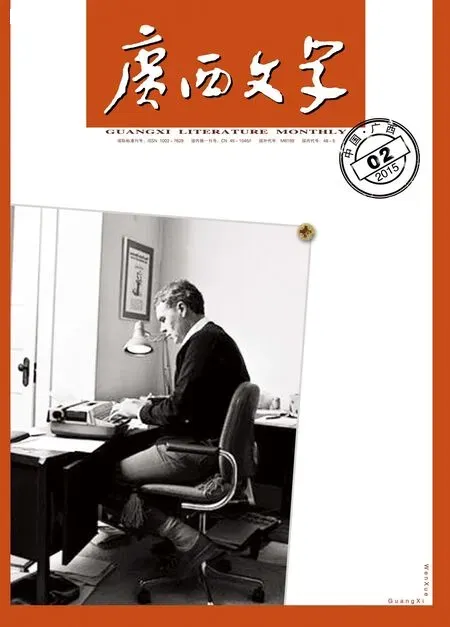村完小
短篇小说·赵先平/著

我们这些老师
我们学校一共有八个教师,校长、副校长、教务主任、总务主任占去了四个,还有四个就是普通的老师。当然学校领导也是上课的,不然这个完全小学校运作不起来呢。我们学校的老师——包括领导在内,年纪都在四十以上,最年轻的是我,已经四十四岁。
我有必要介绍一下我们的学校,我们学校叫安平小学,是一个村的完全小学。在四个普通老师里面,黄老师是个沉默的人,他是近视眼,平时在办公室里批改作业就像只青蛙一样趴在一堆本子上;黄老师身体瘦弱,趴在办公桌上一般也比较安静,只有那吃力的呼吸是有节奏的——那节奏体现在他身体的一起一落上。再就是刘老师,她是个女老师,却是男老师的性格,声音粗大,脾气刚烈,只要她站在讲台上,学生都要安静下来,那是被她的气势压住的。还有一位老师姓苟,比我大两岁的单身中年人,他体格健壮,有着运动员般的胸肌肱肌三角肌,他原本是在县城的高中教物理的,不知什么原因与老婆离了婚,老婆的一位哥是在组织部门工作的,离婚后他就被调到镇中学,教数学;在镇里又与乡镇领导闹出矛盾,据说竟然和镇长打起来,去年刚被发配到我们村完小,他现在教高年级的班,用教中学的办法教小学,效果不怎么好,学生反映到校长那,说听不懂他的课。
我在这个学校里虽是最年轻,但资格却是最老的,因为我一从中师毕业就一直在这个完小教书,教完一届又教一届,其他教师包括学校领导都后我而来,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老师也换来换去,就我不变。
苟老师住在我隔壁,他经常早早起来运动,举哑铃,俯卧撑,在门框上做引体向上等,闹出很大的动静,搞得每个早上我也早早醒来。我的身体不好也不差,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身体练得像运动员一样。我给苟老师提过几次意见,甚至是抗议,但没有效果。他是脑子一根筋的人,每天只按自己的节奏去生活,似乎不怎么考虑别人。有时我忍受不了他的行为,半夜突然开音响——你知道,我是个夜猫子,经常熬夜码文字。或者,我还用棍子敲击墙壁,以此回应他的如雷呼噜声,但收效甚微。白天上班,我对校长、副校长等学校领导发牢骚、发言论,对苟老师大加谴责。虽然我知道领导不能对他产生影响,可是我总是有一种传统的思维,认为只要领导管一管,就能起到作用。我并没有意识到他从一个高中老师到小学老师,已经到尽头了,他从县城中学到村小学,也是已经被贬到最底层了,他对领导已经无惧无畏了。他以自己的方式特立独行地生活着,对周围事物似乎失去了关注的热情。
我忘记介绍苟老师的一个兼职身份了,他是全校老师中唯一兼职教体育的教师。这是最初他到我们村完小任教时自己提出来的。之前学校的体育课是放羊式的,只要是在校园里的,体育课学生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苟老师改变了这种状况,体育课变得正规起来了。学生们喜欢他的体育课,却一点儿不喜欢他的数学课。
这一年刘老师的丈夫出车祸死了。刘老师就是我之前介绍的我们学校唯一的女教师。刘老师的丈夫是个包工头,开一辆村里最好的车,二十多万元的车,却死在车祸上。刘老师悲伤的时间并不长,因为她丈夫生前惹出最多的乡村新闻就是男女关系的绯闻。半年后刘老师和苟老师住到了一起,并且到乡里领了结婚证。刘老师大苟老师三岁。
苟老师结婚,我是最大的受益者。他结婚后搬到刘老师那里去住,早上和晚上我再也不受噪音的干扰了。乡村的空气多么清新,乡村的夜晚多么宁静,我很安静地在乡村的早晚进行写作。我很享受这种白天上课、早晚写作的生活。
刘老师和苟老师结婚后,她似乎变得女性化多了,上课声音柔和,不再动不动就发脾气了。而苟老师,早上的锻炼方式变成了练太极拳。我们那个眼睛近视身体瘦弱的黄老师每天都跟着苟老师练太极,身体竟慢慢变壮起来。
校长李宝剞的公务
我们的校长叫李宝剞,他的弟弟叫李宝剑。李宝剑是我们安平村的村书记,可他常年在广东打工,据说已经在一个工厂里当上了主管。村书记李宝剑不在村里,村里的公章就放在他哥——我们村完小校长李宝剞的手中。这样一来,我们的校长李宝剞公务就很忙了。
李宝剞的繁忙公务,村民黄炳能的体验是最深刻的。在黄炳能看来,校长兼管村支书公章的李宝剞公务是忙得不得了。黄炳能找李宝剞已经不下十次了,黄炳能对李宝剞说,校长,这是第十一次了,如果你再不给我解决,我要上法庭了。黄炳能说这话的时候,李宝剞正背着手在村小学的操场上踱步。正午的太阳照在李宝剞校长“地方支援中央”的秃头上,闪出些许的汗光,就好像他的头上也有无数颗不太亮的小太阳。村小学校的操场只有半个篮球场子,但就是这半个篮球场这两年却是越来越小了。李宝剞说,黄炳能,你帮我解决篮球场变小的事,我就帮你解决老婆的事。
黄炳能肯定不能解决篮球场变小的事,要是能解决,黄炳能就当校长了。上一次,黄炳能找校长的时候,他也是给校长的一句话给打发了。李宝剞校长说,黄炳能,你要是帮我把李老年历的电费收回来,我就帮你解决老婆的事。李老年历是村里的五保户,他不交电费可你还不能停他的电。
篮球场子变小的事,黄炳能不能解决,但可以干涉一下。黄炳能的堂叔黄可安,安平村有名的吝啬鬼和贪婪鬼,屋后有半畦菜地,这半畦菜地紧挨着村小学校的篮球场子,这两年黄可安用了种种法子使半畦菜地逐渐变成一畦。黄炳能对校长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我对老家伙说道理去。”
“呃呃,这道理对牛说去。”李宝剞打算不睬黄炳能了。黄炳能一看校长不睬自己的事,就有些绝望。黄炳能拉着李宝剞的衣服,带着哭腔说道:“校长啊,我都近四十岁了,这张脸往哪搁啊!”
“呃呃,你这人真烦,真烦。”李宝剞不耐烦地说,“都四十了,还离什么婚!”
“这婚我是离定的了,校长,你就给我盖个章吧。”
“我不盖!”李宝剞说。
“结婚自由离婚也自由。”黄炳能委屈地说,“你不能因为害怕影响全村三个文明建设奖就不给我盖章。”
“嘿嘿,一桩离婚事儿会影响安平村的三个文明奖?”李宝剞冷笑道,“好歹咱是同村,我是可怜你啊黄炳能!”
黄炳能犟犟地回答:“我不要你可怜!”
李宝剞指着黄炳能的脸,生气地说:“那好,你可想好了,我给你盖了章千万别后悔!”
黄炳能挺直腰说:“不后悔!”
李宝剞顿了一下,开始用一种公事公办的语气讲话:“黄炳能,你说说,你为什么要和老婆离婚。”
黄炳能愤愤道:“这婊子和别人搞男女关系!”
“和谁?多长时间了?”
“和李合昆,上个月开始,我亲眼见三次。”
李宝剞说:“还亲眼所见,这口气确实难咽下,应该把这婊子给休了。不过我问你黄炳能,离婚后你还想结婚吗?”
黄炳能问:“这和离婚有关系吗?”
李宝剞说:“你别管有没有关系,回答我的问题!”
黄炳能低声说:“想。”
李宝剞问:“想和黄花闺女结还是和上了点年纪的结?”
黄炳能喃喃说道:“我……我都上了这把年纪了,哪还有黄花闺女跟呢?找个上了年纪跟我般配就成。”
“好,好。”李宝剞点头,突然又换另一种语气说话,“和你般配的,那应该是有儿有女了。我问你,不是你生的人叫你爸,你和老婆亲生的叫别人妈,你舒服吗?”
“这……”黄炳能语塞。
李宝剞继续说道:“还有,你老婆只和李合昆搞三次。你离婚要娶的人,别人搞她的,肯定不止三次,你自己算算看,百千次都不止了……你想想,你这离婚了再结婚合不合算?”
黄炳能愣住了。
趁着黄炳能发愣,李宝剞离开村小学的操场回到他的校长办公室。临走时,李宝剞扔下一句生硬的话语:“你想好想通后再与老婆到校长办公室来找我。”
我的一节课
我站在黑板前写了一道算术题,8+8=?是竖式的,那个“+”在左边,两个“8”在右边,下面的长横画得有点斜,偏向右上。我是在黑板的左下方写这道题目的,这样方便学生上来做题,那些一年级的学生都是在一米一到一米三之间。这个小学校是个村完小,学生不多,一个年级就是一个班,一个班有三十人左右,但老师不少,每一学科都有专职教师,我是专门教小学低年级数学的。
一股秋风从门外吹过来,穿过课桌与讲台的空间,然后吹向门对面的窗口,窗已经没有了玻璃,只有窗框,窗框吱吱响了一阵。我叫靠窗边的一个学生站起来,因为他眼睛老盯住吱吱响的窗框。那个学生有些惶恐,站起来的时候把椅子带倒了,但并没有倒到地上,而是“嚓”一声碰到后一排的课桌前缘,椅子卡住了。这个声音引得全班的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我并没有发火,而是微笑地看着他,和颜悦色地问:“可亮,你知道做这道题目吗?”因为全班的学生都看着他,我怕他害羞,便又大声地对全班学生说,“知道做这道题目的同学请举手!”全班的学生把目光转移到黑板上,那个叫可亮的学生感激地望了我一眼,转过身去把椅子扶好。可亮转回身来仍然站着,但他也举手,举起老高,还踮脚跟。“可亮,你上来做。”我说。他兴奋地跑上讲台,我弯下腰给他一截黄色的粉笔,我说:“可亮,你可要写好对齐哦。”这个时候,整个教室就静了下来,风也不吹了,仿佛也在注视着这个叫可亮的学生做题目。
我喜欢这些乡村的小学生。他们淳朴、可爱,他们像一朵朵就要开放的黄葵花,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他们顽皮、捣蛋,他们像一株株带刺的野玫瑰,身上充满着灵动的野性。我站在讲台前,边看着下面的二十几个学生边想:“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外出打工,平时缺少父爱母爱,没人调教,如果我还放任自流,那将是这片故乡故土的罪人啊。”于是我走下讲台,走到他们当中。我在可亮的座位上坐下,看着他在黑板上做题。我看到他穿着一件黑白花格的上衣,半新却有点儿邋遢,裤子是深蓝色的,因为裤管长了点,他两边的裤脚都挽卷起两三圈的模样,显得下面大、中间小。我知道这样的衣裤大多是都市里的地摊货,是他的父母打工之余淘到后寄回来的。班里的二十多个学生,穿着的大多是这种衣裤。
可亮在黑板前紧张而认真地写着题目。其间,粉笔断了,掉到地上两次,那个“1”写好后,“6”字写得有些歪,他擦去两次,重写后依然是歪的,但他好像已经觉得满意了,便在讲桌上放好粉笔。
可亮想回到自己的座位却发现被我占据了,便一下怔住,显出不知所措的样子。我站起来,示意他回来坐。我对全班学生说:“孩子们,可亮同学的演算对不对啊?”
“对!”学生们齐声回答。
“八加八等于多少?”
学生们依然是齐声地响亮地回答:“一十六!”
我赞许地点了点头。我想,八加八,这两个数字真是好呢,一十六,一世六六顺,这个结果也不错。
调研组到我们村完小来检查工作
学校接到通知,这周星期五县教育局、教研室领导要到我们村完小检查指导工作。据说是新任的局长下达了一项下基层调研的任务,要求局领导和教研室人员走遍全县各个村完小以上的教学点。于是一个将近十个人的调研组星期五就要到达我们的学校。据了解,这是一支实力强大的调研队伍,他们老中青结合,都是县里头学校管理、教研工作方面的顶尖人物。
星期五说到就到。调研组带队的是教育局常务副局长黄副局长,他是一个正值年富力强的局领导,理论水平高,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让我们这些基层完小的老师听得云里雾里的。
教研室主任是一个女的,她的年纪看上去已经接近退休的岁数,不过她显得很有亲和力,对我们完小的每一个老师都亲自握手,嘘寒问暖,显出对基层教育工作者的关心和体贴。
语文教研员是个比较年轻的女孩子,她手里捧着个笔记本,一进我们村完小校门就要求听我的课,说久闻我的大名。我们校长一脸尴尬,解释说今天为了迎接领导的检查,全校老师都不上课。女孩子颇感遗憾地对我说,经常在报刊上见你刘老师的作品,真想领教一下教学水平。我想如果我告诉她我并不教语文,而是教数学而且是小学低年级数学,不知她会有什么感想。
数学教研员在调研组里恐怕是年纪最大的,他有一头纯银的头发,话语少却能一语中的。他一进我们的办公室就要求校长把数学老师的教案本收集起来,并且仔细翻阅。
那个高个子的中年人应该是危房办的工作人员,他不说话,眼睛却骨碌碌地转。他看得最多的是学校的房子、窗户什么的,还不时往笔记本里记点什么。
围着常务副局长团团转的人是局里管电教的副主任,他亲自扛着摄像机全方位地拍下领导的每一个动作,胸前还挂着一部照相机。他显然非常熟悉摄像机的拍摄技术,一会儿单腿跪拍,一会儿跑到高处俯拍。看来平时他不仅是拍摄局领导的活动,县领导甚至更高级别的领导他都拍摄过。
有一个人似乎与这个调研组脱节,他显出事不关己的样子。无论是常务副局长的讲话,还是我们校长的汇报工作,他始终都把眼睛盯在手机上,我们不知道他是看短信还是看手机里的新闻或其他的什么内容。间或,他的右手拇指会迅速而灵巧地摁手机键,我们猜想他这个时候肯定是发短信了。他只是在常务副局长介绍他的时候看了一眼我们全体老师,就这一眼让我们看出他是一个严肃的人,他面色冷峻,眼里充满威严。从介绍中我们知道,他是局里的纪检组长。
还有两个人,他们是这个调研组的联络员和司机。联络员不停地接电话、打电话,虽然避开领导们到树荫下面去接听,但他的声音还是在不知不觉间就变大起来,令我们全校老师侧目。司机比较年轻,他双手斜插在裤袋里,走路轻佻,有点吊儿郎当的样子。他大部分的时间不是跟在领导身边,而是跟在语文教研员这个女孩子的身后,时不时跟她轻声地说话、微笑。司机似乎喜欢这个女孩子,但又还不敢过分接近,他对自己似乎不那么自信,言语间流露出些自卑的意味;他肯定对女孩子表示过恋情,但女孩子应该是看不上他,甚至是忽略他。
调研组是下午三点钟到我们村完小的。从领导们的讲话中我们知道他们的行程是这样的:他们早上十点钟从县城出发,驱车两个小时到我们乡里,中午十二点在乡政府饭堂吃饭,吃到两点钟然后就直奔我们村完小。我们从调研组一下车就闻到酒的味道,他们每个人都应该喝了酒,不过都没人喝高。
星期五我们村完小的安排是忙碌而有序的。上午九点我们安排全校师生打扫清洁卫生,清洁卫生不留死角,这用去了我们上午三个小时的时间。中午我们安排低年级学生放学,下午不用来学校,安排高年级学生中午回家吃饭后两点到学校布置会场,在学校操场上摆主席台摆听众席。下午三点半开会,会议主席台坐有调研组全体成员和我们村完小的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和总务主任,我们四个老师坐听众席前排,听众席后排坐着全校高年级学生。这个会议应该是我们村完小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会议开了四十分钟,然后学生放学回家,调研组人员分头调研或检查工作。五点钟调研组人员在一个高年级学生班教室里集中给我们村完小打分,这期间我们全校教职工下厨房帮炒菜师傅打下手。六点钟我们全校教职工和调研组人员一起吃饭,出席晚宴的还有村里头头面面的人物,一共满满两大桌人。为了接待调研组,我们村完小在上午的时候就请人杀了一只羊,除了羊,校长还从自己的亲戚家买了两只鸡、两只鸭,酒是村里人自酿的米酒。我们认为晚宴很丰盛。喝酒喝到晚九点,调研组的人回去了我们还继续喝。
我们估计,调研组从我们村完小回到县城的家,应该是半夜了。
已经调离了的白云霞老师
那年,八岁的白天鸿脑顶上的头发很浓密,他父亲给他理了个奇怪的发型,远看去像头上顶着半个锅盖。白天鸿看着高年级的同学们围着他姐姐白云霞在操场上做击鼓传花的游戏,实在想不出表达不满的办法,就从裤裆里拨弄出他的小鸡鸡,冲着高年级的同学们撒了一泡尿水,说:
“不和我玩,我尿你们!”
远处的高年级同学和他的刚当老师不久的姐姐白云霞当然不知道在一棵龙眼树根下的白天鸿对着他们撒尿。白天鸿不防背后有一个人在看他尿尿,那个人就是校长李宝剞。李宝剞显然非常不满意他的学生在树根下随便尿尿,便威胁白天鸿说,再这么撒尿就不让你姐当老师。当时白云霞还是民办老师,白天鸿听说过不让他姐姐当老师就没有公家饭吃,没有公家饭吃姐姐就没有钱给他买糖果,于是急了,转过身冲着李宝剞喊了一声:“你答应过我姐要让她转成公办老师的!”
李宝剞本来是想把白天鸿揪到办公室的,听白天鸿这么一喊,就愣住了。
白天鸿一边收回他的小鸡鸡,一边指着李宝剞,继续说着:“那天你抱着我姐你就这么说的,我看见了!”
李宝剞确实抱过胸脯丰满的白云霞。
白云霞连续两年高考都考不上,她又不甘心务农,就去找李宝剞,让他帮弄个民办老师的指标。李宝剞本来是不想让白云霞当民办老师的,但经不住她丰满的胸脯一再靠近,就答应了。李宝剞对白云霞说,我是校长,我要保住公职,是不能离婚的。白云霞说,去你的,谁让你离婚?你和我年纪差一大截呢。李宝剞就冲动地抱住白云霞,说:“好,好,我不但让你当民办老师,以后有机会还帮你转成公办教师!”
那些日子,李宝剞一直在白云霞身上辛勤耕作,不是因为他有多大的能耐,而是白云霞的胸脯太迷人了。他忘不了白云霞那对白嫩而高耸的山峰,忘不了和白云霞弄完事以后留在他心里的那种幸福的疲惫感。他想,年轻真好哇。
是人都会有贪欲之心,都会有霸占之念。那年四十八岁的李宝剞真的想一辈子占着白云霞,像过去的地主老财一样,偷偷占着她,做地下的小老婆。可是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呢?这事在村里还是起了风浪,李宝剞的老婆到学校闹了一场。这透风的墙就是从顶着锅盖的白天鸿嘴里说出去的。有一阵子,白天鸿逢人就说,我姐要吃公家饭了,我要有很多糖吃了。不过李宝剞校长是个有办法有能力的人,他很快就阻止了风波的进一步扩散。
后来,李宝剞校长真的把白云霞变成公办教师了。当然这里面也有白云霞自己努力的因素,比如转公办教师的考试,她在全县民办教师的考生中名次还是很靠前的,比如公开课比赛,白云霞在县里拿了第一名等。
事后想起来,李宝剞校长的总结是,白云霞这个女人真厉害。
白云霞和李宝剞校长风波乍起的时候,正是白云霞民办老师转公办的关键时候,乡里的罗宝权书记亲自过问了这件事。
罗宝权书记亲自来安平村调查这场校长与教师搞男女关系的风波。罗书记单独在校长办公室查问了李宝剞。罗宝权书记用手连敲办公桌:
“这是师德与师风的问题,说!你真的和白云霞有关系?”
李宝剞没有编谎,如实向罗宝权书记交代了他和白云霞的关系。罗宝权圆瞪着眼睛,说:“你真搞了?”
李宝剞说:“真搞了。”
在罗宝权听来,李宝剞的坦诚比抵赖更令人不可信,他说:“你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已经泡在你的酒缸里吧?”
罗宝权又说:“白云霞这么个优秀的年轻教师会是你下菜的酒?她会看上你这个有妇之夫而且是年近半百的有妇之夫?”
李宝剞说:“不信你问白云霞去。”
罗宝权找白云霞谈话的时候,白云霞说:
“李校长是我尊重的前辈,就像我尊重您罗书记一样,我怎么会和他发生那种庸俗的关系呢?”
白云霞说这话的时候,那对诱人的胸脯迅速地靠近罗书记。
罗宝权书记觉得问题的严重性,就把白云霞带到乡里。
后来,刚转成公办老师的白云霞迅速改行,当了乡里的团委书记。再后来,罗宝权调到县里,白云霞也调到了团县委。
偶尔会见到白云霞回安平村看望她的父母。知情人说,每次她回来,都会带一包糖果给她的小弟弟白天鸿。
白云霞在县里嫁给一个工人,我们村完小的老师,还有校长李宝剞,都见过白云霞那个当工人的老公。我们对她那个老公很失望,校长李宝剞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回忆一个叫何林的老师
以前,我们村完小所在的村安平村会喝酒的人很少,大家过年过节才喝,喝得很节制。后来会喝酒的人多了,村中常见一两个喝醉喝烂的。
安平村人喝酒的特点,融合北佬的粗犷和老广的精细于一身。入席,主客敬酒,你一杯我一杯地干,豪爽得很。待喝到差不多了,一席人就分帮划拳。划拳又叫猜码。安平村有许多以码为名的绰号:慢码、快码、刁码、鬼码……在安平人看来,划拳是衡量一个人的反应能力的一种手段。酒席上划拳,安平人已超越了原先的罚对方喝酒的意义而成为斗智斗勇的一种方式。于是,在胜利的亢奋中,在失败的懊丧中,人就不知不觉醉了。真的醉了,便划醉码。这时,谁还能够再喝就是胜利者了。但是,醉了,谁又肯轻易认输?就再喝。再喝,就烂醉了。
多年前和我一起中师毕业并一同分配到村完小的老师何林经常喝酒。何老师对这个那个学生说,今晚去你家家访。去了就喝酒,划拳。何老师一喝,就醉,醉了,便借酒疯骂家长不是人,说灌黄尿(指酒)的钱有,孩子买作业本的钱却没有。还骂家长把孩子当奴隶使唤,说猪是孩子能喂的?田里的活是孩子能干的?骂着骂着,有时就一手揪住家长的衣领,一手晃起拳头,厉声说,你要再敢打孩子,我也对你不客气了。何老师长得牛高马大,有人还见过他练功夫,这动作是很吓人的。家长对何老师挺客气的,挨了骂,并不计较,心里都想,他是为咱娃好呢。
孩子们的主要敌人是他们的父亲。考试不及格,父亲把孩子拽过来,木条儿就往屁股上抽。所以孩子们特别喜欢何老师去家访,去家访后,“敌人”的态度往往就温和几天,有时还给几角的零用钱。
何老师常醉,在晚上醉,白天从不醉。虽常醉,他的课却上得极好。他的课,有趣,有条理,加上他常家访,学生们就很爱他。又因为爱他,就都愿学。所以,每学期期末统考,在乡里,安平小学的成绩总拿第一。村人提起何老师,都赞说:好老师,好老师。于是,村中红事白事,或遇上个什么节日,总有家长打发孩子过来,唤何老师去喝酒。
安平人喝酒,还有一个规矩,有客来,不醉不离席。
那天晚上,很奇怪,在酒席上,何老师硬说自己是客人。何老师家在外地,可他在安平已教了十年书,性情直爽、开朗,跟村里的男女老幼都合得来,村里人都把他看作平安人。
那晚是端午节,和他喝酒的,是两位家长。
平常,何老师的码划得很臭,不几下就输,经常是输得没兴趣划。那晚,却出了奇迹,赢多输少。他来劲了,非要把家长整趴不可。
他们一直喝到十二点多。十斤装的塑料酒壶,渐渐见底。站起来,何老师感到脚踩海绵,头顶石头。两位家长,一位在桌边趴了,另一位说要送送何老师,刚晃出门来,便过一边去噢哦噢哦地吐,忘了出门是干什么的了。
安平的夜,静悄悄。何老师一步三晃,往学校走去,走了很长时间,一回神,却发觉自己走出村外,置身在一片空旷的田野里。他想,我怎么来到这里?就往回走。走着走着,又想,我没醉,又转过身来……他在田野上来来回回地走着走着……
第二天早上,孩子们到学校上课。等了半天,不见何老师。有几个学生刚想去他房间看,这时,有位村民来说何老师死了,在田野里。我们几个老师和学生们便跑向田野。
何老师的头栽在泥水里,面部朝下。那个地方,是个浅水洼,泥水都没没过小腿。只要何老师一翻身,仰面,就可以呼吸,就可以不死。可何老师没能转过身来。
两位家长说:“我们不该把他灌得烂醉,不该!”
村人说:“这么好的老师,死了可惜啊!”
有人叹息:“唉,这酒还真是害人不浅啊。”
事后,我们才知道,那天,何老师得了调令,调离安平,到县城里一所重点小学去任教。便有人说,怪不得他这么特别来兴说自己是客人,原来是这样哇。
我们再也见不到何老师的身影了,再也听不到他上课的声音了。每次想起何林,一股悲酸感就涌上我的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