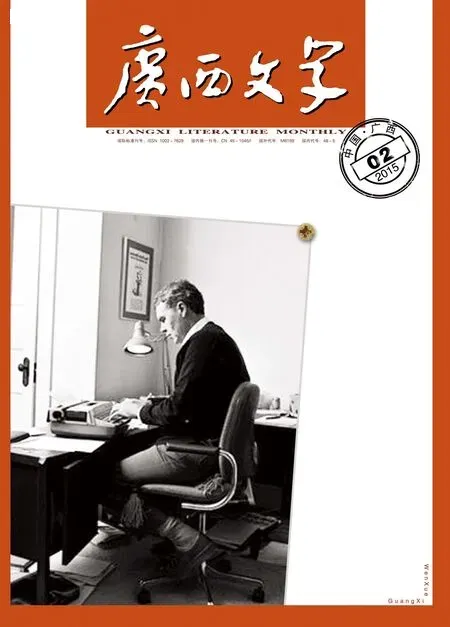飘荡的蒲公英
短篇小说·紫 灵/著

一
陈大富弯着腰推开自家厨房那扇有点松的木门,焖木薯的香味就从里面迫不及待地冲到他的鼻子下。他用力吸了吸,肚子跟着叽里咕噜地响了起来。新挖的木薯整整齐齐地码在墙角的地上,旁边还码着一堆个头粗壮、沉实的地瓜和几个身材浑圆、披着金黄挂着白灰的南瓜。这些都是自己的女人马莆英在地头、地尾那些巴掌大的地上种出来的,她舍不得那些边边角角的地方空着,就想着法子在上面种些耐长的东西。
陈大富进了门,把搭在肩上的扁担往木薯堆旁一放,挂在扁担头上的一卷磨细了的麻绳就跟着晃悠悠地荡起来,放下扁担陈大富转身往门外的天看了看。亮了一天的太阳已经不见了,只剩下一圈微微的白将门前的院井边上正在刷粪桶的影子拉出歪歪扭扭的一条。影子很细、很长,一缕凌乱的发丝在影子的额前毫无顾忌地跟着刀子似的风翻滚。马莆英刚给地上施肥,她将刷好的粪桶往地上磕磕,转头看到陈大富正在看她,眉眼一低,一抹暖阳在她干瘦的脸上悄然绽开。吃饭了!陈大富朝影子粗着嗓子喊了一声。
哎!马莆英走进厨房揭开锅,里面是一盘焖木薯和一碗几乎看不到油花的大白菜。陈大富盛了碗粥就着焖咸的木薯就是一阵猛吸。
慢点吃。看着自家的男人就着这清汤寡水狼吞虎咽的马莆英细小的眼睛里划过一缕说不出的悲郁,低下头,眼角的皱褶似乎又深了一分。陈大富是入赘的,入赘马家那时候他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子,只是脚有点跛。因为马莆英家里除了她自己还有一个瞎了眼的老娘。陈大富在马莆英家住下后很快地就凭着一身力气扛起这个家所有的重担。开荒、种地,里里外外整得井井有条,看着院外一地地茂盛的庄稼马莆英的心也跟着长起来。
他们在一起不久后就有了儿子马宇,可是马莆英放不下家里的老娘。犹豫间陈大富却说他可以上门,还说马家就她们母女俩没了根,让儿子随了当娘的姓好有个延续。这事让马家母女俩的心激动了好一阵。可是接下来有个困惑渐渐笼上母女俩的心头。马莆英发现陈大富从来没有跟她说起他家里人,甚至连他的家在哪里都没有提过。但是为了儿子,为了家里的老娘,甚至可以说为了她自己陈大富不说马莆英也没提。只是在逢年过节看着别人家来来往往走亲戚的时候心里未免会有些失落。
入夜,陈大富把白天还没使完的劲在马莆英身上折腾完后喘着气就沉沉地睡了过去。马莆英却是睡不着,侧着脑袋呆呆地看着身边的男人,心里却像是给什么东西堵住了。这男人到底是从哪来的?
屋外的光透过窗户的裂缝直直地落在陈大富身上,终日在地里风吹日晒没把他吹垮,倒是养出一身结实的肌肉来。陈大富是一个好男人,如果不是跛了条腿就不会上门要自己这样一个女人了吧?马莆英在陈大富面前有点自卑,她的身材很好,四肢也全,可是一块青黑色的胎记狠狠地霸占了她整个右眼以及右脸。因为这张脸她成了弃婴,她是瞎眼老娘在外面乞讨的时候捡回来的。
老娘带着马莆英来到巴崖村的时候已经十六岁了,村支书可怜这母女俩便指了村里一处破砖窑给她们。于是她们便在附近开起荒来。就这样她们就像村头的荒草一样使劲地生长。在这成长的交替中,破砖窑附近的荒地硬生生地给她们种熟了。偶尔,马莆英也跟着村里的人挑着水灵灵的青菜翻过大山到附近的小镇上去卖。可是,镇上的人嫌她丑,不但不跟她买菜,还不时有一群群的年轻人冲上来把她的菜踢翻,说她让镇子都跟着变丑了,还骂她是个没人要的野种。
马莆英回到砖窑跟老娘哭了一夜,老娘就抚着她的头说:妞啊,这砖窑就是咱的根,这样子长成啥样这是天给的。我们不作恶,不欺人,本本分分地过日子,老天会开眼的。
等到老天开眼的时候马莆英已经长到了二十四岁。那一天正好是山里的盘王节,她到镇上给老娘买药,陈大富拖着条折了骨的腿坐在人家的屋檐下,舔着干裂的唇,眼睛尽往人家手上的吃食干巴巴看去。马莆英看不过眼就从背篓里拿了个糍粑和一竹筒子水给他。陈大富接过来三两下就把糍粑塞进肚子。陈大富吃完看着还呆呆站在他面前的马莆英,用手背擦了擦嘴,突然说道:带我走行不?等我腿好了能干活,不会吃白食。
马莆英就这样把陈大富带回了家。她只知道他叫陈大富,据他说是老家遭了灾逃荒出来的,逃难的时候摔了腿。可是马莆英总觉得陈大富说这话的时候眼里分明写着不安和惶恐。但她没有多问,因为她需要一个可以为她遮风挡雨的男人。可这事还是慢慢地在她心里长成一个疙瘩,偶尔也会漏一两句。比如说,你老家都在哪啊?家里还有啥人不?每当这时,陈大富回答她的只有一成不变的沉默。陈大富一沉默马莆英就慌了,于是事情就不了了之。
马莆英伸出手搭在陈大富身上,从背后紧紧地抱住他。这个家有了他才安生,她怕他走。其实她心里还藏着另一件事。白天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听说砖窑的主人要回来了。回来也好,这些年她跟大富省吃俭用地也存下点钱,早就想把这砖窑买下来了。想着这地方很快就真正地属于她,兴奋得都要睡不着了,马莆英就这样在床上辗转反侧,眼看天都要亮了还是无法闭眼。想着眼看就要过年了,还是先准备些过年用的东西吧。于是起床,从墙角的瓦缸里拿出点米用水泡上,泡软了就可以磨些粉做点年糕。
第二天,太阳从马莆英旋转的石磨声中醒过来。马莆英看着像雪花似的粉浆从磨缝里流出来,心也跟着飘了起来。远远地,她看到有个人朝这边走过来。来的是巴崖村的新任村支书赵春光,他说,英子,这个砖窑原来的主人赵大农要回来了。马莆英看着他脸都涨红了,兴奋地说道,哦,这事我早听说了。支书,等他回来我想跟他把这地买下来,你帮我跟他说道说道?听到马莆英这么一说,赵春光却支吾起来,憋了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说道,他们想请你们挪个地。
挪个地?我们挪去哪?
老话都说落叶归根是不?大富离家这么多年是不是该回来看看了?赵春光说这话的时候眼光越过马莆英的肩膀落在一直站她后头边的陈大富身上。陈大富低着头一动不动,就好像没听到赵春光在说话。
赵春光的话让马莆英的头都大了,只觉得脑袋里嗡嗡作响就像是钻进群苍蝇一样。她也不知道赵春光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只看到陈大富失魂落魄的眼神落在院子前那一块块不成形但已经整熟的地上。地上的新土早就翻好了,那是她和大富一锄一锄整出来的。
刚冒出山头的太阳不知怎的忽地就变得像只鸟似的一下子就飞到了天空顶上,明晃晃地照着人的眼睛生痛。从山峭间刮来的风依然像刀子般一拨一拨地割着人。自从入冬后,山里的风每天都在大山底下肆无忌惮地吹刮着地上的每一个人。村里的人早早地就睡下,或是拢在火堆旁,煮着茶,悠然地等着年的到来。
马莆英和陈大富从来不休息,他们趁着这光景努力地往荒地上挖,多开点地就能多种点钱出来。每一寸土地都是他们的希望。她总想着,等攒够了钱就可以把这块地买下来,盖一座新房子。有了新房子他们才算落了地,才算有了根。可现在这唯一可以依靠的土地就要离她而去,它没能等到她的希望实现。陈大富蹲在墙根下抽起了烟,暗红的火光在空气中狠狠地亮一阵就熄了,然后她就看到一大团浓烟从陈大富的嘴里面喷出,接着凌厉的山风把这团烟狠命地搅碎,最后什么也没了。自从赵春光走后陈大富一直蹲在院子里抽烟,从早上到中午,除了像木偶一样地装烟、点火,几乎是一动不动。没有了地,这个男人也要走了吧?
在来到巴崖村前,她跟着老娘从一个地方乞讨到另一个地方再到另一个地方,十四年了,从来没停过。因为她们没有家,没有家就没有根,没根的人就是要飘飘荡荡的。那时候的冬天真冷啊!她和老娘在草棚里住着。寒冷的风把她吹得迷迷糊糊的,只记得老娘抱着她发烫的身子拼命地哭。妞啊,你别死,别扔下老娘!老娘的哭声把路过的村民惊了,给她们从地里挖了块老姜,捡了把柴火在草棚里煮了碗汤给她灌了下去。能不能活看天意了,路过的人说。那人临走,老娘却扯着人家的裤腿说,好心人哪,我这孩子还没名哪,你就给她留一个吧?那人问,老娘你姓啥?老娘说我也不记得我姓啥了,只记得当年我那冤家牵着马把我接进门的。这妞是我捡的,她长得丑,家人就把她丢了,我看她可怜就养着了。那人听着说,要不你们就姓马吧?这孩子跟着你到处飘飘荡荡的,像棵蒲公英似的,就叫马莆英吧?老娘点点头,这孩子就叫马莆英,蒲公英落了地就会长根,长了根就安生了。从此以后,马莆英知道从地里能长出救人命的东西,有了土地人也就安生了。
马莆英突然从木凳上跳起来,急匆匆地往院外走去。蹲在院子里的陈大富吃惊地抬起头,一缕充满了各种复杂情绪的视线跟着马莆英的身影消失在村里泥泞的黄泥路上。
二
马莆英赶到老支书家,远远地就听到一阵拉风箱似的咳嗽,一串接着一串,让人听着都喘不过气来。接下来又是一阵悠长细绵的喘息后紧接着的寂静,死一般的寂静。马莆英站在老支书的院子前,她希望老支书再一次收留他们,正要抬脚,沉闷了许久的屋突地给一声嘶哑的怒吼扯碎了。老支书喑哑的声音如同破铜锣般断断续续地敲进马莆英的耳朵。滚!你这孽障,这就要赶人是不?爹,你也知道这人家的地,再说他也不愿卖,这买地的钱我都帮着凑了,你说这咋办?都说落叶归根,可这陈大富到底是哪人啊?英子姐也真是苦命,跟着瞎眼婆到处讨饭,嫁个人连哪的都不知道。
这两个人的对话让马莆英抬起的脚硬生生地往后退。落叶归根,这四个字变成另一块比石头碾子还要沉的东西往马莆英早已失魂落魄的心上压。我的根在哪呢?马莆英没有再找老支书,而是沿着村旁的一条泥路往前走。
老支书发现有人来,踉踉跄跄冲了出去,却看到马莆英缓缓消失的背影。他的眼睛慢慢地红了,两行浑浊的泪淌过脸上的沟沟渠渠沿着两片干枯的唇滑进嘴巴。瞬间,一股苦涩从舌尖迅速往全身散开,于是,眼更红了。老支书用手背抹了抹眼,似乎看到了自己还是年轻时的模样。
那时候真的好年轻,年轻得不知道什么是忧郁。那个时候,他牵着一匹挂着大红花的老马翻了不知道多少个山山岭岭把长得跟花似的老娘接回家。那时候老娘不叫老娘,叫春子。春子的家在大山里,家里除了老爹老娘还有个哥哥。他们结婚后,老支书为了能多赚点钱给家里,就到外面打工去了。等他回来,看到的却是一张空床。原来,春子被家里人赶出家门,家里人怕他伤心就一直瞒着他。
那一夜他在巴崖山顶上望着一条麻绳似的山路吹了一夜的风,村里的人说那天晚上听到他在山顶上哭断了魂。他想着春子,念着春子,可春子终究是走了的。
再后来,老支书又娶了妻子,还生了个儿子。老支书凭着一股埋头干活的劲给村民们选上当了村支书。干着干着他就从年轻的小伙子变成了中年大叔。这时,村里却来了个瞎了眼、蓬头垢面的女人,手里还牵着个黑了半边脸的孩子。虽然岁月的风霜在这女人的脸上刻下了一道道沟沟壑壑,可老支书看到她那颗早已沉寂的心却像是烧开的水似地剧烈翻滚起来。春子,那个让他魂牵梦萦的人竟以这种方式出现在他面前,她又回来了,只是原来的记忆都没有了,人也变得有点疯癫。老支书给她们母女住进了破砖窑,帮着她们开荒种地,渐渐地看着马莆英长大了。
马莆英终于走远了,远远地消失在老支书的视线尽头。她没有回砖窑,而是走到她用锄头一点一点整出来的地头上去。这里的冬天没有雪,虽然山里的风吹得像刀子般的利,但也吹不走那地面上不停冒尖的菜苗。绿油油的是菠菜,白嫩嫩的是大白菜,还有那长得像花似的大包菜在地里支起一个个圆滚滚的芯。它们就这样肆无忌惮地向人们展示着这片土地的肥沃。
马莆英走到白菜垄里蹲下伸手到白菜根下想拔出两棵,等儿子回来就可以用它来做一个白菜炖肉,这是马宇最喜欢吃的菜。当她的手碰到那湿润、黝黑的土地却像触电似的猛地收了回来,给它再长两天吧,往后再也见不着了。马莆英红着眼进了家门,陈大富不见了。
渐渐地,太阳又沉到了山的那边去了,陈大富还是没有回来。这男人会不会像当初突然出现那样突然地消失了?没有了地,难道连男人也跟着没了吗?
终于,坐累了,夜已黑,黑得连巴崖山都叫人看不见了。马莆英摸索着找到一根还算硬挺的木棍,在地上敲了敲。走吧,既然迟早都是要走,白天和黑夜又有什么区别?她要到山外去找儿子,儿子在两年前就离开家在外头打工了。
马莆英拄着棍子沿着陈大富修建的篱笆墙转了一圈,圈内关着她所有的期盼。这里曾留下了老娘、自己的男人、儿子的影子。这里的水井、石辗子、晒绳,还有角落里她随手扔下却长成一团浓密的山姜,空气中似乎还飘荡着它那辛辣又带着清香的气息,这一切让她着迷,让她心疼。
马莆英转到了院门,长长地叹了口气正要往外走,一道黑影从那白菜地头窜了出来,肩上还挂着两只硕大的箩筐,一深一浅地往这院子边走。大富,马莆英扔下棍子冲上去抱住黑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用力地捶打着眼前的人,你去哪了?你怎么不走?这里什么都没了!
陈大富伸出粗糙的手在马莆英的脸上深深地擦了一把,吞吞吐吐说道,只要你不嫌弃我,我就一直跟着你。只是……只是我家乡的村子都给泥石流埋了,我回不去,真的回不去了……马莆英看着眼前这个一向不说话的男人忽地说了这么一番话,整个人哭得更厉害了。等她哭过了气,扯着陈大富说道,我们回去吧,只要我们能活着,村子就能重新建起来。
马莆英抹了抹眼睛,看了看陈大富,又看了看还搁在灶旁那做了一半的年糕,撸起袖子继续把那散落的粉打成糕。现在我们就把年过了,过了就走。明天我们到镇上让人给他捎话,等我们安生了就接他回来。
天蒙蒙亮,这对夫妻已经挑着一担装满衣物的箩筐爬到巴崖山的半山腰。马莆英跟着陈大富翻过巴崖山,又爬上了另一道山梁。快到了吧?马莆英望着高矗入云的山尖问。陈大富没有回答马莆英的问话,闷闷地往前走了几步停了下来。回过头再看了看马莆英,将肩上的箩筐放到地上,眼里写满了忧虑。马莆英看着他也不好再说什么只是默默跟在他身后沿着山麓走。当他们快要爬到山顶的时候陈大富却领着她转入一条树木浓密的小道。在小道尽头,马莆英眼前突然一亮,举目望去他们竟站在一座繁华的小城边上。
这里四面环山,蓝得滴水的天空下层层叠叠的桑田轻烟笼罩随风而动,宛若雾涛碧海。房屋依山而建一排一排的,中间由一道道青石板连接而成。马莆英怎么也没想到在这大山深处竟隐匿着这样一座世外桃源般的小城。然而,陈大富的眼睛落在东北角的一片地方再也无法移开。
马莆英顺着他的视线望去。只见那一处地方桑田叠幢,树木浓密如海,丝丝缕缕炊烟从树冠间袅袅升起,盘旋,随后融入雾涛碧海久久不去。山下,一道碧绿幽蓝的水依山而绕,沿洞而出,将那碧海桑田拢进了自己的怀里形成一个天然的良湾。这是什么地方?马莆英困惑地看着陈大富。
陈大富转过头看着她,这是……我也不知道。陈大富的回答让马莆英如坠迷雾。我的家就在前面,可是它已经给埋了啊……陈大富说着,又往那山水围绕的村庄看去,脚下却再也不肯移动半步。马莆英困惑地看着眼前这个男人,这些年他害怕的就是这些吗?彷徨间,马莆英看到一条黑色的身影急匆匆地往他们这边赶来。
赵春光?看清来人马莆英的心“咯噔”一下跳了起来。巴崖村的村支书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赵春光看到他们倒像是松了口气似的,绷得紧紧的脸如同头顶上明晃晃的太阳一下子全都绽开了。他三两步冲到这两个人跟前气喘吁吁地说道,哎哟!我说你们这两个好家伙,怎么说走就走?
支书,我们知道你为难。陈大富沉声说道。大富啊,你的事我都清楚了,这些年倒是为难你了。赵春光的话又勾起了马莆英的困惑,她偏过头紧张地看着自己的男人。终于,在赵春光断断续续的讲述中,陈大富刻意隐瞒的故事慢慢地浮出水面。
这一段故事竟然要从马莆英的养母瞎眼老娘春子出嫁前说起。那时候的春子还是一个水汪汪的大姑娘,本是陈大富的小姨,也就是他母亲香梅的妹妹。当时由于家中贫寒,为了给老爹治病他们就把大女儿香梅留下看家,把小女儿春子嫁给了老支书。原本期望着能拿一笔彩礼钱来治病,另一方面还能让春子过上好日子。没想到,春子嫁过去没两年竟然给人撵出了家门。被夫家赶出家门对一个女人来说是终身的耻辱,春子被撵后不敢回家,在外面到处流浪,变得痴痴傻傻。老爹听到这个消息后认为是自己害了春子,没过多久就郁郁而终。老爹死后,娘也跟着走了。两个老人走了以后,春子的姐姐也就是陈大富的娘就带着陈大富离开家乡沿着一座座山、一座座城不停地寻找春子,无论如何她都要把这个苦命的妹子找回来。
几年过去了,渐渐地香梅满头的黑发变得花白,脚步也开始沉重起来,终于,她带着失望领着陈大富回到了良湾村。却发现村子给泥石流埋了,悲郁之下香梅竟跳崖自尽。陈大富为了下山寻找母亲尸骨,从山上滚了下来,把脚摔断了。他挣扎着爬到镇上求医,却因身上没钱而遭到唾弃,在街头饥寒难忍时遇上马莆英。马莆英虽然不好看,但他看得出眼前的人心地善良,他就跟着马莆英回了家,慢慢地他发现老娘竟是自己要找的小姨。可是这时候的春子什么都忘了,唯一能记起的就是巴崖村里的老支书。陈大富心里明白,虽然春子和老支书的情分不长,可她终是记着他的。然而,此时的老支书早已成家,儿女成双他又能说什么?只好陪着她留在巴崖村,留在这片让老娘和马莆英都眷恋无比的土地上。
现在他要带着马莆英回家了,然而,离家多年又让他胆怯,他还能回去吗?站在山头遥遥望着那一片熟悉而又陌生的土地,陈大富的脚步再也无法移动。他没有打断赵春光的讲述,他只是纳闷这里真的是他的良湾村吗?
赵春光只顾自个儿说着,没注意到陈大富的困惑。倒是马莆英听入了神,她怎么也没想到那个把自己拉扯大的老娘和自己的男人背后隐藏了这样一段故事,更没想到眼前这个像画一样的地方会是陈大富出生的地方。
马莆英悄悄地扯了扯陈大富说,大富,我们回家吧?陈大富却站着没动,就好像前面出现的只是一座海市蜃楼。
赵春光抢过他肩上的担子往前头的村庄努了努嘴,我说兄弟,你倒是走啊!走?去哪?陈大富跟着赵春光走了两步又停了下来,我,我还能回去吗?
赵春光走得快,等陈大富把话说完他已经跟这两个人拉开一段距离了。不过,陈大富的话他倒是听清楚了,回过头朝这两个还待在原地的人喊道,大富,那是你家,跟我走就是了!接下来这段路这两个人在赵春光的紧催快促下磨磨蹭蹭地走进良湾村。
站在村头曾经的熟悉与陌生同时涌上陈大富的心头,阔别多年魂牵梦萦的家就在眼前,在掩埋的废墟上一座新建的村子重新出现在他们面前。这里的人还是家乡人吗?陈大富跟在赵春光后头走着走着,这些念想在他头脑里一骨碌地涌了出来,越是接近村子,他脚下的步子越慢。赵春光领着他走到原来房子的废墟上,一道碧绿的篱笆墙围着幢结实的瓦房矗立在院子里,房顶上的瓦新簇簇地在太阳底下泛着炫耀般的光。看到这里,他几乎要立刻掉头就走,这已经不是他的家了。
赵春光进了门发现这两人没有跟上来这才回过头去看,却看到陈大富把他放下的大箩筐又挑起来一晃一晃地往村外走,马莆英紧跟在后面不停地踮着脚。喂,我说你们这两人是怎么回事?快回来!赵春光冲着他们的背影粗着嗓子喊道。他这一喊,倒是从屋里喊出个秃着头的矮胖子。胖子走到赵春光身边瓮声瓮气地问,这咋回事了呢?赵春光朝他撇了下嘴,人跑了呗,不敢回来!兄弟你是不是没把话给人说清楚?胖子拍了拍赵春光倒是笑了。我这不是想着把这里修整好再给他们说,等他们过完年回来舒舒服服住着多好?谁想到他们会走啊?你倒是想得好,把我也坑了,我要不是来这里一遭还不懂咋回事呢,还让我给家里的老头子骂了一通。
我说,赵支书现在就别埋怨了,先把人追回来,等走远了就追不回了。秃胖子朝赵春光的屁股狠狠地拍了一巴掌指着那两人的背影说道。
原来这秃胖子正是赵大农,自从起了回乡的念头后他就悄悄打听着家乡里的事。当他了解到自家的地上住着马莆英一家后他也曾困惑。他要这样回来,这家人就得搬出去。要不回吧,这可是自家的祖地,俗话说落叶归根,他总不能带着一家老小的就在外面飘吧?思来想去,就悄悄回到巴崖村找老旧识把这事说了一下。当他打听到春子和老支书的故事后,就想这陈大富不知道是哪的,但可以到春子的家看看,更没想到春子跟陈大富竟是一家人。原来良湾村当年给泥石流毁了以后,早就由政府出资重建了。建好了,再派人把失散的村民找回来。只是由于陈大富跟着香梅早就离开良湾村,也没了消息。这时候正好赵大农一路打听过来了,就由他出资,村里也出点在陈大富家的原址上修间房子给他。
正当赵大农在良湾村忙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却等来了心急如焚的赵春光。原来,他也打听到了自家老头子的往事,思来想去,就瞒着老支书找到了春子的家乡先看看,这一看遇上了赵大农。他们俩一合计,觉得不能再瞒了,由着赵春光赶回去跟陈大富摊牌。赵春光急走快赶地倒在半道上遇到了陈大富和马莆英这两个惶恐不安的人。
赵春光扯着陈大富抿了抿唇,兄弟,这些年对不住了。老娘,就给她留在巴崖村,这里你就替她看着行不?陈大富在赵春光肩上重重地捏了一把,缓缓地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