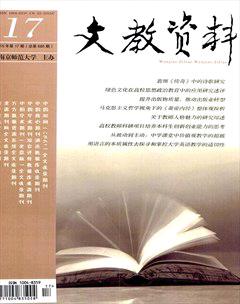学群散文《走向珠穆朗玛》的创作艺术探析
杨荣树
摘 要: 艺术产生的过程不单单是物质在一定技术作用下简单的运行与改变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创造者自身精神灌注、催生出与其内质相一致的物态形成过程。本文通过探析学群创作《走向珠穆朗玛》,表明艺术创作成果的特质与气度与作者的精神能量有密切关系。
关键词: 学群散文 《走向珠穆朗玛》 创作艺术
海德格尔认为,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真(即客观存在着的物质体和精神体的总和)发生与持续的特殊方式,是世界与大地历史性冲突的场所”,“是历史的基础”、“是人生存的历史性本源”,“启示着人生存在世界与大地之间这一根本处境,并为人的历史性生存提供现实的可能性”[1],因此,文学艺术创作当以反映“历史的基础”即“人生存的历史性本源”为己任,在维系和发展健康的性灵中愉悦性灵,在此过程中呵护和塑造美好的心灵。
美好心灵无不体现对人类共同美好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的勾画和追求。随着人类愿望的梯性上升,这种勾画和追求的内质将不断改变,因而它始终是人类不断翻新的理想图景。正因为此,人才会为挣脱旧境、达到理想的新境而不断地苦闷、彷徨、追求、抗争,而有所生灭、有所进步。
艺术往往就创生于这种由感愤、弃离实“真”趋奔于理想的虚“真”的欲念冲动及其触及合适的物象后,串缀和融合主体情思与客体物理,融合造就物我合一的意象意境的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以自觉表象运动为主的“感性”心理和概念运动为主的“理性”心理相伴综合运行[2]及作为形象思维处于高度紧张、凝聚状态的一刹那闪光的“妙悟”升华的心力[3]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历史恰好证明,艺术家们往往在追求真、善、美的前提下和过程中,在经过了充分的感性、理性和妙悟等认知、思想和感情等综合性心理活动合理想性地确定和展开之后,即以旧有传统为自我奠基的基础,以开劈新径为自我丰美的法宝,富有个性而又兼顾受众的欣赏诉求及水平淋漓尽致地畅抒情怀,成就了一件件鲜美的艺术精品。因此,艺术家们的创作才会“性情面目,人人各具”[4],艺术之花才会永不凋败。
学群在《散文》2007年第8期上发表的散文《走向珠穆朗玛》,充分体现了这种独立性和时代价值,是一件独特的艺术品。作者为了能短暂挣脱现实的“真”,走向珠穆朗玛,意外获得了“完成一次自己对自己的超拔”的机会,圣洁这一终极精神元因此得到了刚性膨胀。然后,他喜不自禁地将虚实、天地、物我镕为一炉,筑就了浑然一体、瑰丽独特的艺术世界:自然的大气、物质社会的大气、自我人格品性的大气和反映这种大气的自然、大气的社会和大气的精神的表达方式的大气。
作者描述其精神由俗至雅、由小至大、全方位立体化膨胀以至与宇宙同涯、与天堂同质的骤变过程。先是作者“在这个世界里活过一些时日,对于生命,对于时光便有了许多感受”。“于是就有了做点什么的需要,哪怕是短短的一下,从庸常中走出去”。而此时,恰巧将目光投射到了地图上,“停在中国的西南部,一块棕红色凸起来的地方”,于是瞬间就点燃了热情、振奋了精神,尝试着“把我的目光寄往8000米高处,完成一次自己对自己的超拔”,开始了“走向珠穆朗玛”之行,在行进中感受到由地域之变引起的文化之变尤其是青藏高原上特有的“朝拜”一类的精神之变后,联想起自己“生活的那块地方,一个人的生命中塞进了太多的东西”,而这些“膜拜的藏人匍匐在地面”时,“灵魂里天空是这样接近”,于是心生万千感慨,决意改变“这些年来,一直都在吃,不停地往里面填塞”而使“身上装载得太多,物资挤占了精神的空间,脂肪代替了灵魂”、精神几近枯死的状态,“拉光吐光,把自己的肠肠肚肚都通通清洗一遍”,一直“向前走”,走向珠穆朗玛,展开“一次灵魂的朝圣”。艰辛来到珠穆朗玛脚下,看到白天里雄奇、绚烂、壮美、与天地谐和一体的珠峰和傍晚时奇异、圣洁、娇美、玉立于黑暗之上、连接白天与黑夜、连接灰暗与灿烂的珠峰,在此自由、空灵、幽静、幽深的环境中释放出的圣洁的人类终极精神元纳入心宇,而它又突然以自己为圆心呈喷射状急剧强劲地向宇宙全方位扩张,把自己的躯体和灵魂密切地连接上并且融进了浩渺巨大的宇宙之中,产生了“来自雪山的水,把握和雪山一起盛入天空的蓝色里”,终于自己瞑迷之中“看到”自己“印在天空上的影子”,并且因为“山在地面与天空、湖水与白云之间建立起一种神秘的联系”,“人走在求经的路上”,并由此“通向神灵”,最终完成“自己对自己的超拔”。
在终极精神的这种刚性膨胀中,其表达方式显得大气十足,体现了作者高远大气的思想情怀。本篇以抒情为主、辅以议论、兼及叙事,其基础骨架是叙事。但它又不是按事件的起因、经过与结果叙事,而是以点带面、以点带线、点线结合,展开酣畅淋漓的抒情和议论,使自己一腔圣洁精神得以刚性膨胀和舒展。这样大气地极其简单却明了的叙事,为大气地抒情和议论留下了大量篇幅和笔墨。详略处理是作者的又一大手笔,对这两点一线也不是平均使用力气,前点只用了寥寥数行,简单交代了寻求能“引领你的目光”的“一点”的原因和结果,为全文做好了铺垫。行程一线用墨较多,对行程一语带过,所见、所想、所感却酣畅淋漓大气地写,所见是青藏高原上没有外边“所有的繁华与喧闹”,“这般千年如斯的大美”,“一望之下,让人心怀虔诚”,于是“从地面流过的水,从空中吹过的风,从人身上生出来的崇拜,无一不在诵读”,“写在大地、写在天空”的“经义”,尤其是人,“没有汽车,没有帐篷,甚至没有食物和水”,仍然“一步一个等身”,“地在哪里黑下去,人就在哪里躺下去;天什么时候亮起来,人就在什么时候‘走起来”,不辞“千里万里”,感慨与崇敬之情溢于言表。更突出的是,作者由眼前的景联想到自己之前住的那个物质世界及其给人带来的伤害,情不自禁地发出“我们哪里还有一个完整的自己,何曾有那么一块空间和时间来静静地面对”和“面对他们(匍匐朝拜的人们),面对这里的天空,面对这辽阔的宁静”,“我们缺少可以用来面对的东西”的感叹,失落与渴望之情更加强烈地溢于言表。作者又大气地用三个“向前走”的排比句式,一扫之前阴霾的心气,表明“吐光拉光,把自己的肠肠肚肚通通清洗一遍”、“生命跟着大地一起升华”、完成一次“灵魂的朝圣”的坚定决心。后点即行程的终点是全文的重点和精华,占全文一半以上篇幅。这终点的“点”实则是作者行进艰难而形成费尽力气才走很短的距离——短短的一条线,但是因为在作者的活动区域与高大而平缓上升的珠峰及整个走向珠穆朗玛的行程看,只能算是一个“点”,作者在这里完成了全身心的洗礼和升华,实现了圣洁精神的刚性膨胀,它伸延进了广阔深邃、无边无际、静穆圣洁、自由舒畅的天堂之中。他看到的是“我们这颗星球高高举起,聚在所有人的头顶”的珠穆朗玛“裸露的岩石”那孤高坚硬的华表,其伴侣是恒久不离的轻纱似的洁白“云朵”和亘古晶莹光鲜的“冰雪”及让自己变成“赭红”娇艳、熠熠生辉、美轮美奂的“阳光”,比世界之巅强大许多的“天空”时刻都“张开”着的“巨大而深邃的蓝”,如此大气和大美风光,无疑是“天堂”境界。作者置身于此,有了新的逻辑,认为珠穆朗玛是“大地以站立的方式,站到人只能道法的高度”形成的,是“一个把地连到天上的地方”,“我把目光交给”它,就可以“沿着大地走向天空的脚步一路向上,当土地站立成世界上最高的海拔时,人的目光也就有此升入天堂”,自然,想象中,身心尤其是精神就升入了天堂。太阳落山时的珠峰的旖旎景象是“大地把它最本质的美举在那里”,“如此艳美,如此灿烂”,天下无双,所以,作者由衷地议论和抒情:“在这里过上一刻,就足够全世界活上一天,足够我们活上一生!”天堂的日子不能多,但有天堂的日子是多么幸福的事。大幸往往伴随大苦,大福往往伴随大痛,来到珠峰脚下已是不易了,更加不易的还是来到珠峰脚下的“呼吸和脚步”,而这却是人到这里除了身体和灵魂外所能剩下的两样东西,但都很“艰难”。至此,作者展开奇异的思维,进行联想和议论,讨论人舍易取难、亲疏自然、珠峰冷峻逼视人的灵魂、人行高原的艰辛与生痛、物累过重殚精竭虑之人无力登山的可怜可悲等涉及精神层深刻问题。其后围绕这里的天空、太阳、云朵、雪峰、大堤、海子和“我”之间浑然一体的关系,洋洋洒洒富有哲理地禅悟似的在“喝下一口水,就把天空、云朵和山一起装进了胸间”后,将无限膨胀的伟大的“终极精神”与同样伟大的宇宙实在融为一体,将虚与实、小与大、物与我、天与地的交接和融合起来,敞亮出最真切、透彻的觉悟和升华。因此,作者最后情不自禁、意味悠长地如此议论和抒情道:“辽阔的青藏高原一下把我拓得很宽很宽,珠穆朗玛又把我举得这样高,这样高”,“这是一座真正的山,一座要用一生一世来走的山,一座一生一世也走不完的山,一座一旦走过便决定你一生的山,一座你用生命走过,因此也就走你生命的山”。幸福与快乐之情溢于言表。
精神的这种终极刚性膨胀力量,是人类奋勇前行的伟大壮举的强势展现,是对贪婪者、懦弱者和糊涂者们的启迪与警醒,是引领人类精神世界升华的一座灿烂丰碑,更是催生独特艺术世界的重要元素。
参考文献:
[1]余虹.艺术与精神[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48.
[2][3]金开诚.文艺心理学概论[M].北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9-126.
[4]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