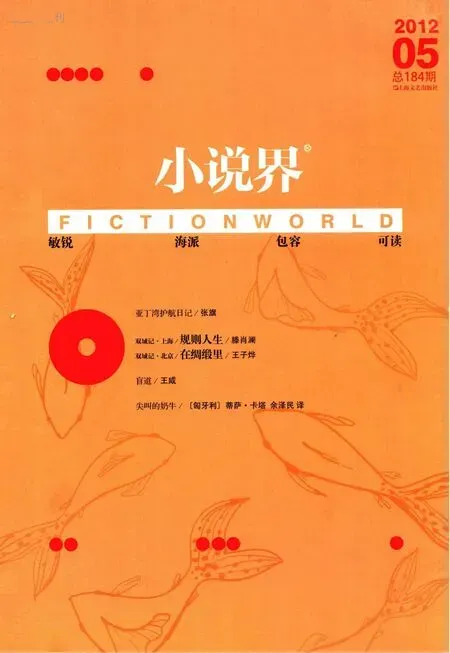黄泥湾风情(三题)
文/江岸
黄泥湾风情(三题)
文/江岸
奶奶的桃树
九十高龄的奶奶年轻的时候有两个绰号,一个是“侉女人”,一个是“国民党婆”。她的老家在豫北安阳,硬腔硬板的口音和黄泥湾当地接近湖北的甜糯口音相差太大,惹人嘲笑,为她赢得第一个绰号。爷爷年轻的时候是一介书生,抗日战争爆发,他毅然投笔从戎,战死沙场,他的遗孀解放以后就此赢得第二个绰号。
不过,那都是阶级斗争时期的事情了,已经有几十年没人再叫奶奶的绰号了。
老迈的奶奶近来真是有点糊涂了。表现之一是她把自己的鞋子洗了。奶奶童年的时候包过脚,还没有包成三寸金莲,就放脚了,但她的脚比普通人的脚还是要小一码。她的这双小脚在她后来的千里之徙中让她吃尽了苦头。她的鞋特别难买,必须靠手工做。年轻的时候,她自己纳鞋底,自己剪鞋面,自己做鞋穿。后来她做不动了,就由我妈帮她做。奶奶穿鞋极爱惜,沾染一点灰尘,就用小手巾擦干净。她还从不洗鞋,说是她老家安阳的规矩,女人的鞋子直到穿烂,也不能洗。她也没有说过不洗鞋的道理,反正就是不洗。我妈发现奶奶晾晒在窗台上的刚刚洗过的一双小鞋,惊讶地叫了一声,把我们所有人都惊动了,跑到了院子里。
奶奶糊涂的第二个表现是突然馋嘴了。院子里有三棵桃树,两棵是五月桃,一棵是八月桃。我们家的桃子和本地土桃完全不一样,不仅个大,而且水分多,咬一口,甜掉牙。很多邻居要么用我们家的桃胡种植,要么用我们家的桃枝嫁接,结出来的都是又苦又涩的毛桃。我们家的桃树是用奶奶从老家安阳带来的桃胡种植的,据奶奶说,那味道和她老家的桃子一模一样。奶奶从豫北安阳,千里迢迢奔赴豫南,带几颗桃胡完全是没有预谋的。那时她不满十八岁,桃胡只不过是好玩的少女随身携带的玩具。五月桃快成熟了,又白又大地挂满枝头。从不贪嘴的奶奶竟然要吃桃子。奶奶咬了几口五月桃,就放下了,要吃八月桃。八月桃还是青涩的,看着奶奶一点点啃八月桃,我们的腮帮子都浸满了酸水。奶奶捧着那个八月桃,隔一会儿就啃一口,啃了一个上午。
奶奶糊涂的第三个表现是她喜欢哼曲儿了。奶奶面朝北方,依偎着桃树,久久凝视北方的天空。层峦叠嶂阻断了奶奶的视线,奶奶能看见的顶多是桃树顶上北方天空的一角。看着看着,奶奶竟然哼起了小曲儿。我们都不懂得奶奶哼唱的是什么。还是我妈细心,听出来奶奶哼唱的是《小放牛》。我妈是大跃进期间从平原逃进山里的,饿晕在路上,被奶奶救活,做了光棍汉我爸的老婆。我妈和奶奶一辈子相处得非常亲密,我爸五十九岁那年去世了,我妈独自奉养着奶奶。年轻的时候,奶奶偷偷唱过《小放牛》给她听,说是河北民歌,安阳人都会唱。我妈说,《小放牛》有三段,你奶奶翻来覆去就唱第三段:什么鸟儿穿青又穿白?什么鸟儿身披着绿豆衫?什么鸟儿催人把田种?什么鸟儿雌雄就不分开那个咿呀咳……
我妈背转身,抹开了眼泪。我妈说,看来,你奶奶的大限到了。停了停,我妈又说,她是想你爷爷了……
我妈跟我们讲过奶奶的故事,都是她们娘儿俩闲聊时,奶奶告诉她的。我们长大的时候,奶奶可能对自己年轻时候的荒唐事儿羞于启齿,从没有对我们提起过。但是,从我妈那里,我们知道了奶奶所有的故事,令人唏嘘。
阳春三月,桃花灿烂的时候,奶奶的村庄开过来一支军队。军队号房子,奶奶家也进驻了不少兵,挤满了偏院。后来,奶奶就认识了很多兵,也认识了我爷爷。不训练的时候,爷爷就邀奶奶去庄子周围看桃花。后来,就偷财主家的桃子给奶奶吃。五月桃罢园了,就偷八月桃。八月桃还很青涩,但是奶奶吃得津津有味,每天让爷爷去偷。爷爷咬过一口八月桃,酸得倒牙,就呸地一口吐了。这个丫头怎么那么喜欢吃青桃呢?爷爷非常狐疑。他毕竟二十多岁了,猛一下就明白了,吓出一身冷汗。吃到八月桃罢园的时候,爷爷的部队接到调令,要开往前线抗击日寇。开拔之前,爷爷找到奶奶,泪流满面,掏出一封写清地址的家信,掏光了身上所有的钱,塞给了奶奶。奶奶的父亲是个私塾先生,极要脸面的,爷爷怕他走了,奶奶的丑事一暴露,她准会被她父亲活埋。奶奶就在爷爷部队开拔的那个晚上,悄悄用烟灰抹脏了脸蛋,背个小包袱,逃出了她的村庄,一路向南而去。
我妈说,你奶奶肯定想念你爷爷了。她在路上奔波了两个多月,等她找到黄泥湾的时候,你爷爷的《抗日烈士证明书》和三百元抚恤金已经由政府送到家好几天了。
弥留之际,奶奶的枕边被我们放满了又白又大又甜的八月桃,我们往奶奶的手心里也塞了两个。奶奶的嘴唇还在轻微地翕动,我妈贴耳去听,听了一会儿,我妈抽泣着说,你奶奶还在哼《小放牛》:喜鹊穿青又穿白,金鹦哥身披着绿豆衫,布谷鸟催人把田种,鸳鸯鸟雌雄就不分开那个咿呀咳……
浮财
整个演播大厅座无虚席,各路收藏界人士济济一堂。五位并肩而坐的国内资深文物鉴定大师和粉面含春的美女主持人已经准备就绪。随着导演的一声令下,享誉国内的省电视台大型综艺文化益智类节目“华豫之门”开始录播了。
嘉宾通道从大厅门口直通大厅正前方宽广的舞台。耀眼的追光灯从门口一直跟随着第一位嘉宾,把他送到舞台上。在主持人的示意下,他把双手捧着的藏品小心翼翼地放在了舞台前部的珍宝展示台上。
这是一位中年人。他穿一身半新的西服,但衣服明显不合身,挂在他身上有些晃荡,看起来,好像是临时借来的。中年人有些木讷,有些腼腆,站在主持人面前,看一眼主持人,又迅速地低下头去。
主持人问,请问您这是一件什么藏品?
中年人说,我这是一件铜香炉,底部有“大明宣德”四个篆字,我想,它应该是大明宣德炉。
您确信它是大明宣德炉吗?
这个,我也说不好。我不太懂文物。
主持人呵呵笑了,继续问道,请问您是怎么得到它的?
中年人踌躇一下,说,其实它不是我的,我是替我父亲来的。
那么说,它是您父亲的。您父亲为什么自己不亲自来呢?
其实它也不是我父亲的,是我爷爷传给我父亲的。我父亲年事已高,来不了。我今天是受父亲委托来到这里的。
哦,是这样。您爷爷传给您父亲,您父亲又委托您带过来参加鉴定,这个铜炉应该是你们家传的了……
不,它不是我们家的。
说真的,先生,您把我绕糊涂了。
中年人挠了一下头,为难地说,说起来有点话长。我能从头说起吗?
主持人迟疑了一下,说,好,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您的故事。
中年人打开了话匣子。他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语言也开始流畅起来:我来自豫南山区黄泥湾。解放前,我们黄泥湾有个地主,叫冯月波,是我们家远亲。我太爷、太奶死得早,我爷爷就是在冯家长大的,后来就给他家当了长工。冯家大少爷冯幼波在汉口读书,后来当兵了。冯幼波有一次回乡探亲,带回来这个铜香炉。冯月波把这个铜香炉放在供桌上,逢年过节时用它烧香。后来就解放了,冯幼波再也没有回来,听说去了台湾。土改前,冯月波专门交代我爷爷,说万一他有个好歹,让我爷爷保管好这个铜香炉,什么时候大少爷回来,就交给他。我爷爷答应了。土改开始不久,冯月波被枪毙了,贫下中农分了他的浮财。很多人家分到了八仙桌、太师椅、四柱床,分到了绫罗绸缎,有的是背回家的,有的是抬回家的,都累得吭哧吭哧的。我爷爷什么都没有要,就要了这个铜香炉。他把铜香炉揣在怀里,回到家,被我奶奶好一顿埋怨。
趁中年人的讲述告一段落,主持人问,这个铜香炉就一直留在你们家了?
中年人点点头,说,是的。我爷爷一直等到死,也没有等回少东家冯幼波。他临终的时候,把这个铜香炉交给了我父亲,让他继续等着冯家人。现在我父亲时间不多了,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个铜香炉。他看到电视上有你们这个节目,就让我赶紧报名,一定让我参加节目。
主持人说,对不起,报名我们这个节目的人太多,可能没有及时让您参加。不过,好在今天,您终于来了。
中年人说,非常感谢电视台给我这个机会。我今天来,不是为了鉴定这个铜香炉的真假,也不是为了知道它到底值多少钱。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这个节目,找到老冯家的后人,让他们知道,他们家的铜香炉,在我们手里。
主持人问,经过鉴定,如果这个铜香炉真的是大明宣德炉,您不愿意自己留下吗?
中年人说,如果想自己留下,今天我就不会出现在这里,我们家三代人就不会替老冯家把这个铜香炉保管到今天。我父亲手上有个大明宣德炉,在我们当地是公开的秘密。文物贩子要买,小偷来偷,还有个乡干部硬要拿走。最吓人的一次,两个家伙冒充警察到我们家抄家,说我父亲违犯国法,私藏文物。我们保管这个铜香炉,实在也不容易。我们很缺钱,但是,我们不能不守信义。
主持人没再说话,啪啪啪地鼓起掌来。整个演播大厅内,顿时掌声如潮。
谢孝
去年国庆节长假,我驱车回到故里黄泥湾,看望母亲。我对母亲说,这个假期我哪里都不去,只在家里陪您。母亲摇摇头,说,你说得好听,到时候还不是手机一响,你就没影儿了。手机勾着你的魂呢。我无言,默默把手机关了,交到母亲手里。
吃过午饭,母亲说,你陪我去逛逛庙会吧,蔡堂子今天逢会。
我满口答应,驾车带母亲去了。一袋烟的工夫,我们就到了。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叹道,我每回赶会,都走好半天,觉得好远,今天怎么就突然近了呢?
我掏出身上所有零钱,塞给母亲。母亲对佛很虔诚,见佛就拜,就往功德箱里投钱。我们孝敬她的钱,一部分被她给亲戚、邻居随礼了,另一部分被她送给了佛祖。
母亲进了庙。我百无聊赖,在一个台阶上坐下来。大学毕业以后,我一直在城市工作,岁月把昔日纤瘦的少年装扮成了一个壮硕的中年,除了本村民组的人,基本上没人认识我了。但是,在台阶上坐了一会儿之后,我突然感觉有双目光在我身上逡巡,我不自在起来,如芒在背。见我发觉,那双目光便知趣地挪开。然而,挪走片刻,便又粘在了我身上。如是反复者三。
这是个什么人呢?为什么如此执著又迟疑呢?认识我,就大大方方过来打个招呼,不认识,犯不着这么偷窥我。
终于,我身上的阳光消失了,有道黑影遮住了我面前的光线。我抬起头来,看见一位须发花白的老汉站在我面前,目不错珠地盯着我。我友善地冲他笑了笑。
请问,你是黄泥湾的姚志高吗?
你是谁?怎么认识我?
刚才如果不是看见你搀扶大婶下车,我也不敢认。我想,能开车送大婶来赶庙会的,肯定不是旁人。我也仔细看了,虽然有三十六年没见面了,你也富态了,但是你的轮廓还在,我就认出你来了。
那么说,我们过去熟悉?
怎么是熟悉?我在大队小学教过几年书,正好教过你们这一届。
我在脑海深处迅速搜寻起来,小学时代的老师一个个跳出来,虽然有些模糊,但还是有一些印象。这个人高,瘦,白净,难道是胡克本老师?
我伸过手去,他也赶紧伸过手来,我握住了他一双粗砺的大手,摇晃几下。我说,您是胡老师啊,多年不见,还挺好吧?
好,好,他连连点着头,说,可是,有一件事儿……
见他迟疑,我连忙说,胡老师,您有话请直说。
他垂下头,低沉地说,你是我的学生里最有出息的一个,我心里头也以你为骄傲。但是,我教了五年书,从没有打过别的学生,唯独打过你。所以,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后悔,想跟你道歉,说声对不起,又没有勇气找你说。就这样在心里憋了三十多年。今天佛祖保佑,终于见到你了。你原谅不原谅,是你的事情,我必须说声对不起。否则,我死不瞑目。
我重新抓紧他的手,说,胡老师,您这是从何说起啊?您过去管教过我,我应该感谢您才对,怎么能让您道歉呢?
他的眼角有闪烁的泪光,问我,你真的这样想?
我缓缓地点了点头。
临走的时候,我从汽车后备箱里翻出两瓶长城干红,递到他手上。我说,胡老师,今天真没有想到在这里遇到您,一点儿小意思,真的拿不出手,请莫见怪。
他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手足无措地推挡。我不由分说,将两瓶酒塞在他怀里,跟他道了再见。开车走出好远,我还在后视镜里看见他呆立的身影。
胡老师怎么不继续教书了?我问母亲。
他哥是大队干部,让他当的老师,他哥不当干部了,他也就不教了。
他说他打过我,您知道吗?我怎么不记得了?
你在学校的事情,我怎么知道?
七天的假期飞逝而去,我和胡老师相遇这一页也很快翻了过去。工作一忙起来,就记不得陈芝麻烂谷子了。
大概隔了两三年时间,有天早晨,我正准备出门上班,手机响了。
请问您是姚志高主任吗?有个陌生的声音问。
我是,请问你是哪位?
我是胡克本的儿子。今天我爹满“五七”,我该向亲朋好友谢孝了。我爹临终前一再叮嘱,第一个谢孝必须对您。我现在在家里给您跪下了。谢谢您宽宏大量,让我爹开心快活过了几年。
怎么,胡老师不在了?得的什么病?
胡老师的儿子不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您送我爹的两瓶酒,我爹开了一瓶,逢年过节拿出来,喝一口。他还到处跟别人说,他的学生给他送酒了。剩下的那瓶,他舍不得打开,让我放他怀里,陪葬了。
我正不知道如何回答,忽然听见手机里传来“砰砰砰”的三声响,胡老师的儿子说,姚主任,我替我爹,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