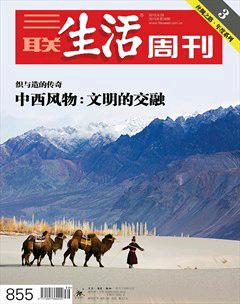丝绸之路的植物
邱杨+付雪航+吕慧
苜蓿
苜蓿是世界上分布最广,栽培历史最古老的牧草,有着“牧草之王”的美誉。每到夏初时节,根系发达、茎高尺余的苜蓿草,便在光滑细致的茎梢处,悄悄开出紫色的簇状小花,结出如螺旋般的果实和似肾形的种子。这种最早被人类驯化的饲料作物,起源于古代波斯。直到公元前500年波斯入侵希腊,士兵们用苜蓿喂战马和骆驼,才把苜蓿种子传入希腊。公元前200年,苜蓿种子传入意大利和北非。随后,随着“丝绸之路”上骆驼队旷日持久的长途跋涉,苜蓿种子也在向东方传播。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在乌弋、安息、大月氏、大宛等地(今中亚地区包括中亚五国、克什米尔、伊朗、阿富汗等地),见到大片种植的苜蓿。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从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带回大宛马和苜蓿种子。据《史记·大宛传》记载:“大宛国左右……马嗜苜蓿。汉使张骞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葡萄。”当时将天子所乘之马称之为“天马”,常嘴嚼着苜蓿茎花而进出皇城内外,故有“天马常衔苜蓿花”之说。
苜蓿的传播及驯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自汉朝引入后,苜蓿先在京城长安的皇家苑囿内试种。由于关中地区与西域皆位于北半球中纬地带,气候和水文条件相似,苜蓿很快便适应了这里,并逐渐向陇东、陕北甚至西北地区传播开来。唐代颜师古为《汉书·西域传》作注:“今北道诸州,旧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苜蓿者,皆汉时所种也。”
自汉朝之后,关于苜蓿的种植便屡有文字记载。《齐民要术》是北魏时期主要记载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生产的综合性农书,作者贾思勰在其中详细记载了苜蓿的栽培方法和利用价值:“土宜良熟。七月种之。畦种,水浇,如韭法。”这说明,最晚在北魏时期,苜蓿种植已推广到黄河中下游流域。
到了唐朝,苜蓿的栽培更加普遍。《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凡驿马,给地四顷,莳以苜蓿。”也就是说,当时驿站用的官马,都有规定数量的苜蓿地或苜蓿园作为饲料基地。唐代《薛令之传》中还提到了苜蓿能充当人类的食粮,而南朝《述异记》则记录“张骞苜蓿园在今洛中”,并明确指出“苜蓿本胡中菜,骞始于西国得之”。北宋《本草衍义》说苜蓿盛产于陕西,用以饲马牛,人亦有食之者,但不宜多吃。而元朝为了防饥荒,甚至下达了种植苜蓿的法令。《元史·食货志》中记载:“至元七年颁农桑之制,令各社布种苜蓿以防饥年。”

苜蓿
到明清时期,苜蓿在华北地区己普遍种植,呈现出王象晋在《群芳谱》中所描述的“三晋为盛,秦齐鲁次之,燕赵又次之”的局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苜蓿“处处田野有之”,连遥远偏僻的地区都有。淮河流域地区也有了一定范围的栽种,但此时的苜蓿大概还没有扩种至江南地区,所以才有“江南人不识也”的记载。而据乾隆时河南《汲县志》记载,“苜蓿每家种二三亩”,反映出华北、西北地区几乎每户农家都有种植。清朝农学著作《农蚕经》、《民囿便览》等均对苜蓿的食用方法、饲用价值、栽培技术等做了较全面的论述。
除了种植范围的扩张,古人对苜蓿的利用方式也在丰富。苜蓿含水量较高,草质柔嫩,适口性好,是饲用价值最高的牧草。在畜禽生长发育所需要的13种维生素中,苜蓿就含有10种,又被称为“维生素饲料”。更独特的是,苜蓿所含的粗纤维,在反刍动物瘤胃内的消化速度很快,容易使家畜产生空腹感,从而刺激食欲,增加采草量。另外,苜蓿的植株生长点位于枝条顶部,刈割后再生能力强,可利用期长。而这个特点在苜蓿传入之初就已经被古人发现,据《齐民要术》记载:“(苜蓿)长生,种者一劳永逸。都邑负郭,所宜种之。”
除了充当饲料,苜蓿还是保持水土、防风固沙和改良土壤的理想植被。清代《增订教稼书》记载,盐碱地上“宜先种苜蓿,岁夷其苗食之,四年后犁去其根,改种五谷蔬菜,无不发矣”。清朝道光时期河南《扶沟县志》也记载:“唯种苜蓿之法最好,苜蓿能暖地,不怕碱。”事实上,这类记载在北方的地方志中比比皆是。而从今天的研究来看,苜蓿属于深根系植物,根系入土深度通常为2~6米,最深可达39米,强大的根系及其分泌物能为土壤提供大量的有机物质,改善土壤的理化性状。
苜蓿还常常与粮食作物轮作或混作。《群芳谱》指出:苜蓿地“若垦后次年种谷,必倍收,为数年积叶坏烂,垦地复深,故今三晋人刈草三年即垦作田,亟欲肥地种谷也”。明代《养余月令》、《群芳谱》和清代《农圃便览》、《农桑经》等都记载苜蓿与荞麦混作是历史上的普遍经验:“夏月取子和荞麦种,刈荞时,苜蓿生根,明年自生。”这说明古代农民已经利用苜蓿根系的固氮能力使谷物丰收。恰如北方流行的一则农谚所说:“一年苜蓿三年田,再种三年劲不完。”
除了用作饲草外,苜蓿还可供人做菜食用。在《四民月令》中,就有苜蓿作为蔬菜来栽培的记载,《齐民要术》也称“春初既中生啖,为羹甚香”。但在太平年月,一般很少有人拿它当饭菜,只有在粮食缺乏时,才被当作“救荒之奇菜”,以至于苜蓿甚至成了生活清贫的象征。唐朝薛令之在《自悼》中写道:“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宋朝陆游在《书怀》之四中亦称:“苜蓿堆盘莫笑贫,家园瓜刳渐轮囷。”除此之外,苜蓿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作为一种域外引进植物,苜蓿能在中华大地上传播开来,除了其固有的自然生态因素,也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在古代,马是重要的农用动力和交通工具,战马更是战争的神经中枢,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军事作战能力,因此历代王朝都很重视苜蓿这一重要饲料的种植和推广。唐玄宗时,官员王毛仲“初监马二十四万,后乃至四十三万,牛羊皆数倍”,要保证数量如此庞大的牲畜群体的生存绝非易事,所以“莳茼麦、苜蓿千九百顷以御冬”。明朝嘉靖年间,军队在九门之外种植大量苜蓿,用于喂养皇家御马。为了保证饲草的充足供应,国家还专门设置官员掌管苜蓿的种植和管理。正因如此,“植之秦中,后渐生东土”的苜蓿,历经2000余年而繁衍不息。
石榴
深秋时节,霜林尽染,红艳艳的石榴也悄悄绽开果皮,露出一颗颗晶莹剔透的榴子。当人们细细地吸吮着清甜的榴汁,任琼浆玉露般的汁水沁入心脾,是否会想起遥远的丝路上关于石榴的传说?“石榴酒,葡萄浆,兰桂芳,茱萸香。”从长安到罗马的漫漫丝路上,一路传唱着这样的唐人歌声。
石榴原产于古波斯到印度西北部的喜马拉雅一带,即现在的伊朗、阿富汗等中亚地区。古波斯人称石榴为“太阳的圣树”,是多子丰饶的象征。大约公元前2000年,航海的腓尼基人将石榴种带往地中海沿岸。在西亚,古以色列的所罗门王就爱饮用石榴汁榨的香酒,据说连他的王冠也用石榴纹装饰。在希腊神话中,石榴被称为“忘忧果”,人们相信它的魔力会令人忘怀过去。
在遥远的东方,榴花与天马,则成了汉朝天威远播流沙的标志。一般认为,石榴是在汉武帝时期,与葡萄、苜蓿等同时经由西域传入中国内地。西晋张华的《博物志》记载:“汉张骞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安国”即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而“石国”则是塔什干,故当时石榴大多被称为“安石榴”。虽然缺乏西汉时期对石榴传播史的直接文献记载,但已有文献中对石榴在汉代已由西域传入中国内地的描述则是确凿无疑。
石榴引入之初,汉武帝就下令遍植长安城。“汉家天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城郊。”据史书记载,当时石榴作为珍树奇果,被栽植在首都长安御花园的上林苑和离宫骊山温泉宫,专为帝王享用。东汉魏晋时期,石榴的种植以河南最盛,而都城洛阳是石榴种植的中心。这一时期,石榴由皇家宫苑开始进入士人阶层乃至普通民众的生活,并开始形成本土化的优良品种。
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记载:“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浮屠前荼林、葡萄异于余处,枝叶繁衍,子实甚大,荼林实重七斤,蒲陶实伟于枣,味并殊美,冠于中京。帝至熟时,常诣取之,或复赐宫人,宫人得之转饷亲戚,以为奇味。京师语云:白马甜榴,一实直牛。”文中“荼林”即石榴,可见在汉明帝时期(公元58~75年)洛阳已有石榴栽培,尤以白马寺品种最为优异。
东晋南北朝时期,石榴以河南为中心,向北、向南继续传播。从《齐民要术》对石榴繁殖、栽种技术和加工利用有详细记载,表明北方石榴的种植更加普遍,栽培技术已臻成熟。而南方石榴也开始见诸文献,蜀地和长江中下游等地开始出现地方名优品种。《乐府诗集》收录的《孟珠》诗云:“扬州石榴花,摘插双襟中。葳蕤当忆我,莫持艳他侬。”
隋唐时期,石榴的栽培得到快速扩展。《封氏闻见记》卷七记载:“汉代张骞自西域得石榴、苜蓿之种,今海内遍有之。”隋大业元年于洛阳故王城营建东宫时,以樱桃、石榴作为行道树。唐时华清宫有七圣殿,绕殿长满石榴,据称是杨贵妃亲手栽种。《酉阳杂俎》中记载:南朝梁大同年间,东州后堂的石榴都是结成双子;南诏的石榴果实饱满、皮薄如藤纸,味道更胜于洛中石榴。可见在唐代,人们对各地石榴的不同特点也都了如指掌。

石榴
宋元时期,石榴的栽培、采收、储藏和加工技术日趋精细,并得到全面推广。宋代石榴品种明显增多,仅《洛阳花木记》就记载了九个不同的品种:千叶石榴、粉红石榴、黄石榴、青皮石榴、水晶浆榴、朱皮石榴、重台石榴、水晶甜榴、银含棱石榴。人们对石榴利用价值的认识也加深了:“多食其实则损仁肺。东行根并壳,入杀虫及染须发口齿等药。其花百叶者。主心热吐血及衄血等。干之作末。吹鼻中立差。”
明代是石榴种植业发展的高峰,这与明代士风不无关系。明中叶以后,私家园林进入全盛期,时人谓:“凡家累千金,恒屋稍治,必欲营治一园。”同时,士子编撰类书、谱录成一时风气,必多方搜求园艺作物尤其是新奇种类。从文献记载来看,尽管南方普遍有石榴种植,但明清石榴的分布仍以北方为重,尤其是品质优良的佳种多出自北方。
石榴在我国悠久的栽培历史中,形成了众多别名,如若榴、安石榴、榭榴、海榴、丹若、海石榴、金庞、金罂、天浆等。如此丰富的词汇,既说明古人对石榴的熟悉与重视,也表明古人对石榴的广泛用途逐渐掌握。
石榴初春新叶红嫩,入夏繁花似锦,仲秋硕果高挂,深冬铁干虬枝,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庭院树种。古诗有云:“春花落尽海榴开,阶前栏外遍植栽。红风满枝染夜月,晚风轻送暗香来。”石榴种植在皇家园林中尤为盛行。李唐时期,因女皇武则天的极力推崇,曾出现“榴花遍近郊”的盛况。在明朝人的插花“主客”理论中,榴花总是列为花主之一,称为花盟主,可见古人对石榴的推崇。
石榴籽实多汁,酸甜可口,营养丰富,自古被视为珍贵果品。除鲜食外,用石榴酿酒在古代较为普遍。梁元帝萧绎有诗句云:“西域移根至,南方酿酒来”;“樽中石榴酒,机上葡萄纹”。石榴还被加工成石榴汁饮用,“北人以榴子作汁,加蜜为饮浆,以代杯茗”。石榴还有醒酒之功,潘岳在赞美石榴时说它有“御饥疗渴,解酲止醉”的作用,清代陈扶摇在《花镜》中也有“其实可御饥渴、酿酒浆、解酲、疗病”的记载。
除观赏、食用外,石榴还被用作药物、染料、胭脂等。在唐代医学家孟诜的《食疗本草》里记载,石榴可以治疗肠肚绞痛、持久泻痢等病,还说到把石榴花阴干碾碎呈末状,混合着铁丹服用一年,即可白发转黑、气色红润。这意味着早在此时,石榴的美容功效已被人们所认识。石榴还是制作胭脂的原料,《北户录》云:“石榴花堪作烟支。”此外,石榴的根皮、树皮及果皮富含鞣质,可作为黑色染料,给玉器描黑、染墨、染发等。
石榴和中国的服饰文化也有着紧密联系。古代女子爱戴石榴花,到南北朝时还很风行,南朝梁简帝肖纲就有“鬓边插石榴”之句。古代妇女着裙,多喜欢石榴红色,而当时裙子染色的染料便是从石榴花中提取,古人由此把红裙子称为“石榴裙”。久而久之,“石榴裙”就成了古代年轻美貌女子的代称,而“拜倒在石榴裙下”则成了求爱的代名词。
石榴身上寄托了古人太多美好的愿望和无尽的遐想,从而使石榴文化在华夏大地影响深远。农历五月,是石榴花开最艳的季节,五月因此又雅称“榴月”。在石榴花盛开的五月,瘟疫流行,人们常会请来钟馗像镇守,而民间所绘的钟馗像耳边常戴着一朵石榴花,有“榴花攘瘟剪五毒”之说。在我国民间,还有以石榴图案祝子孙繁盛的习俗。人们常用“连着枝叶、切开一角、露出累累果实的石榴”图案,象征多子多孙,谓之“榴开百子”,是新婚时窗花、幔帐、枕头等新房陈设中常见的图案。
黄瓜
原产于印度热带潮湿森林地区的黄瓜,距今已有4000年的种植历史。早在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苜蓿和葡萄,接着通过“丝绸之路”引进红花、石榴、核桃、胡麻、黄瓜、葱、蒜等经济植物。黄瓜通过丝路传入我国后,便在此安家落户2000多年,成为家喻户晓的瓜类作物。
黄瓜传入之初,原名胡瓜。因古代称聚居于西北的民族为“胡人”,黄瓜原为“胡人”所种,故有胡瓜之名。而更名为黄瓜,则缘于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纷纷进入中原,建立自己的政权。319年,羯族人石勒建立后赵王朝,立都于襄国(今河北邢台)。他对自己国家的人称呼羯族人为胡人大为恼火,便制定了一条法令:无论说话写文章,一律严禁出现“胡”字,违者问斩勿赦。
有一天,石勒在单于庭召见地方官员,当他看到襄国郡守樊坦穿着打了补丁的破衣服来见他时,很不满意。他劈头就问:“樊坦,你为何衣冠不整就来朝见?”樊坦慌乱之中不知如何回答是好,随口答道:“这都怪胡人没道义,把衣物都抢掠去了,害得我只好褴褛来朝。”他刚说完,就意识到自己犯了禁,急忙叩头请罪,石勒见他知罪,也就不再指责。
等到召见后例行“御赐午膳”时,石勒又指着一盘胡瓜问樊坦:“卿知此物何名?”樊坦看出这是石勒故意在考问他,便恭恭敬敬地回答道:“紫案佳肴,银杯绿茶,金樽甘露,玉盘黄瓜。”石勒听后,满意地笑了。自此以后,胡瓜就被称作黄瓜,在朝野之中传开了。
不过,这个典故疑似是后人附会的。实际上,胡瓜改称黄瓜的确切年代应该在隋代。隋炀帝杨广的母亲独孤氏是鲜卑人,因此隋炀帝有一半胡人血统,但他本人十分崇尚华夏,蔑视胡夷。根据唐代吴兢《贞观政要》中的《慎所好》记载:“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筑长城以避胡。”另有唐代杜宝的《大业杂记》记载:“(大业四年)九月,(炀帝)自幕北还至东都,改胡床为交床,胡瓜为白露黄瓜,改茄子为昆仑紫瓜。”

黄瓜
可在现代人看来,我们平时食用的黄瓜明明是碧绿清脆,为何不叫绿瓜反而叫黄瓜呢?事实上,现在我们吃的都是还未真正成熟的黄瓜。绿皮黄瓜在它老熟之时,才会露出“本色”:皮色由绿变黄,肉质变老变酸,种子硬挺。据《齐民要术》记载,北魏时,黄瓜要等色黄后才采摘。但后人发现,黄瓜未成熟时吃着更脆、更香,慢慢地便在黄瓜尚绿之时摘下食用。
引种黄瓜早期,所见文字记载很少,及至南北朝时才有了相关论述,到了唐朝,黄瓜已成为南北常见的蔬菜。唐代《本草拾遗》和宋代《嘉祐补注本草》皆著录了黄瓜。南宋诗人陆游更有七言绝句赞美黄瓜:“白苣黄瓜上市稀,盘中顿觉有光辉。时清闾里俱安业,殊胜周人咏采薇。”
到了明清时期,黄瓜的栽培技术获得很大的发展。《本草纲目》中记载:“胡瓜处处有之,正二月下种,三月生苗引蔓,叶如冬瓜叶,亦有毛,四五月开黄花。结瓜围二三寸,长者至尺许,青色,至老则黄赤色,其子与菜瓜子同。一种五月种者,霜时结瓜,白色而短,并生熟可食,兼蔬蓏之用,糟酱不及菜瓜也。”
王象晋的《群芳谱》对黄瓜的形态特征描述得更为详尽:黄瓜“蔓生,叶如木芙蓉叶,五尖而涩,有细白刺如针芒,茎五稜亦有细白刺,开黄花,结实青白二色,质脆嫩多汁,有长数寸者,有长一二尺者,遍体生刺如小粟粒。多‘谎花,其结瓜者即随花并出。味清凉,解烦止渴,可生食”。黄瓜为雌雄异花植物,此处的“谎花”是指不能结实的雄花,数量多于雌花达10倍以上。尽管当时的学者不知花有雌雄之别,但两者之差异能被观察和记载确是难能可贵。
对于黄瓜种植技术的研究,也有久远的历史。《齐民要术》卷二种瓜篇中记载:“种越瓜、胡瓜法:四月中种之。胡瓜宜竖柴木,令引蔓缘之。收越瓜,欲饱霜,霜不饱收烂。收胡瓜,候色黄则摘。若待色赤,则皮存而肉消也。”此处已论述黄瓜的播种采收时期和基本种植法。事实上,黄瓜种法有地黄瓜和架黄瓜之分:地黄瓜适于少雨地区,不搭支架,任瓜蔓于田间伏地生长,栽培管理较粗放;架黄瓜则适于温暖多雨地区,在瓜蔓伸长以前,用竹木搭成人字架,使瓜蔓攀缘其上,栽培管理则较精细。
在浩如烟海的唐诗中,不难发现诸如“暖房”、“温室”等字眼,这说明唐代除花木之外,已掌握了黄瓜的温室栽培技术。唐代诗人王建在《宫前早春》诗中云:“酒幔高楼一百家,宫前杨柳寺前花。内园分得温汤水,二月中旬已进瓜。”明代王世懋在《学圃杂蔬》中提道:“王瓜出燕京者最佳,其地入种之火室中,逼生花叶,二月即结小实。”
经过长期实践,古人逐渐认识了黄瓜既喜温又怕酷暑的特性,设法满足它对温度的要求,使其早上市、多次上市,甚至周年供应。根据记载可以窥见,当时的主要农业措施是根据各地的气候特点,错开播种日期,进行露地栽培或温室栽培,提前或适当推迟采收,以延长上市日期。当时就已经有春黄瓜、夏黄瓜、秋黄瓜和冬黄瓜之别。
黄瓜适应性强,易种易活,瓜可鲜食,亦可腌渍、晒干贮藏。尤其在灾荒年间,瓜干可代食粮度过荒年,这恐怕也是黄瓜受古人欢迎的原因之一。
菠菜
“北方苦寒今未已,雪底菠薐如铁甲。岂如吾蜀富冬蔬,霜叶露芽寒更茁。”宋代诗人苏东坡在这首七言散联中所指的“菠薐”,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菠菜。这宛如“铁甲”的美味佳蔬,又名波斯菜、菠斯草、赤根菜、鹦鹉草、角菜等,是藜科菠菜属的一二年生草本绿叶类蔬菜,以嫩茎叶及根供食用。
菠菜原产于亚洲西部的伊朗高原,唐初经尼泊尔传入我国。据《新唐书》的西域传记载,唐太宗时曾派遣官级为从六品的卫尉承李义表出使天竺国(今印度),途经泥婆罗国(今尼泊尔)时通过访问活动,加强了两国的友好联系。到贞观廿一年(647),泥婆罗国国王特地派使节来到长安,贡献波棱等蔬菜,“叶类红蓝,实如蒺藜,火熟之能益食味”。其后散见于诸书所著录的菠薐、波稜、颇陵、颇菜和波菜都是引入地尼泊尔语菠菜(palinga)的汉字记音。
其实早在隋代,菠菜从其原产地经民间渠道就已引入中国。唐代韦绚在《刘宾客嘉话录》中曾说过:“菠薐种出自西国,有僧将其子来。”西国当指原产地伊朗,因其古称波斯,故菠菜又有波斯草和菠斯等别称。直到现在,福建福州、泉州等地区仍将菠菜称之为菠伦。泉州有这样一句俗语:“要食着食菠伦,要穿着穿绸裙。”意思是,吃菜菠菜最好,穿衣绸裙最中意。
菠菜传入中国后不久,便引起了唐代研究草药的医学家孟诜的注意,在他所著的世界现存最早的食疗专著《食疗本草》中,论述了菠菜的药性。其“菠薐”条曰:“冷,微毒。利五脏,通肠胃热,解酒毒。服丹石人,食之佳。北人食肉面,即平。南人食鱼鳖水米,即冷。不可多食,冷大小肠。久食令人脚弱不能行,发腰痛。不与蛆鱼同食,发霍乱吐泻。”这是菠菜见于我国典籍的最早记载。
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约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至二十一年(803~805)。郭橐驼在书中说:“菠薐菜过月朔乃生,今月初二、三间种与二十七、八间种者,皆过来月初一乃生。验之,信然。盖颇棱国菜。”这意味着,到8世纪末,菠菜的栽培己推广至长安西部的农村,郭橐驼不是道听途说,而是自己有种菠菜的实践,才能知道菠菜的生长习性。

菠菜
自郭氏而后,唐代典籍中就没有关于菠菜的记录了,爱写诗的唐人也没有提到过这种新奇的蔬菜。杜甫困顿时常食菜蔬,连山野间的杂草苦荬都写进诗里了,却从未提过菠菜。由此可见,菠菜在唐代栽培并不广,且因并非富贵菜,常食还有“令人脚弱不能行”的副作用,唐代的文人墨客并未注意到它,只有一些本草学家、炼丹术士和因经济匮乏而种来聊以添菜的农民对它感兴趣。
到了宋代,菠菜在典籍中的记载就多了起来。这一方面是由于宋人喜著述,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菠菜的广泛栽培。大约在南宋孝宗淳熙(1174~1189)以后,著录菠菜的地方志数量便急速增长,这意味着菠菜的广布应在南宋以后。而《中国外来植物》的“菠菜”条目也称:“至宋元方广为种植,成为冬春季节常见蔬菜。”
这也与菠菜在文学中的地位变化相吻合。宋孝宗时期的诗人员兴宗在《菜食》中写道:“员子一寒世无有,爱簇生盘如爱酒。菠薐铁甲几戟唇,老苋绯裳公染口。骈头攒玉春试笋,掐指探金暮翻韭。达官堂馔化沟坑,我诵菜君人解否。”员兴宗在诗前小序中将菠薐等蔬菜与竹君并提,赋予了蔬菜人文的内涵,在精神层面上推动了菠菜“中国化”的进程。
《全宋诗》中写到菠菜的诗共计8首。有些诗中提到了菠菜的一些吃法,比如菠菜粥和菠菜饼,还有些诗中提到菠菜在僧侣中很受欢迎,出家人似乎是菠菜的主要消费者。
菠菜是一种味道很有争议的蔬菜。经霜经雪的菠菜发甜,口感好,而其他季节的菠菜比较涩口。正因为菠菜有甜涩两种口感,所以,爱吃的人极喜,而不爱吃的人视若凡品。宋代陶谷在《清异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五代时期做过南唐户部侍郎的钟谟,特别爱吃菠菜,他把菠菜视为天上降下来的“雨花”,并把菠菜、蒌蒿和萝卜看作是无可比拟的佳肴而称之为“三无比”。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时,镇江有一农妇为他做了“菠菜烧豆腐”,还美其名曰:“金镶白玉版,红嘴绿鹦哥。”乾隆吃后,觉得味道很好,且清淡素雅,便封农妇为村姑,菠菜为村姑菜,并经常叫御厨做这道菜给他尝鲜。而明代王世懋在笔记《蔬疏》中则说:“菠菜,北名‘赤根。菜之凡品,然可与豆腐并烹,故园中不废。”可见他并不推崇菠菜。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在一首专写菠菜的诗篇题解中道出了菠菜的来历及其食疗功效:“波棱乃自波陵国来,盖西域蔬也。甚能解面毒,予颇嗜之,因考本草,为作此篇。”所谓“面毒”,古时候小麦多用石磨磨成面粉食用,因而石头中的一些粉末也进入到面里,当时的保存技术又不过关,放置久了便有些泛灰的毒素,人吃了就会发热毒。古人很早就知道菠菜宜与面同食,消解“面毒”,利于五脏,效果颇佳。
除此之外,《本草纲目》在“菠薐”条下云:“凡人久病,大便涩滞不通,及痔漏之人,宜常食菠薐、葵菜之类,滑以养窍,自然通利。”《滇南本草》称菠菜:“味甘微辛,性温。入脾、肺二经。祛风明目,开通关窍,伤利肠胃,解酒,通血。”《食疗本草》说菠菜:“利五脏,通肠胃热,解酒毒。服丹石人食之佳。”
豌豆与蚕豆
历史上,曾有两种从西域传来的豆科植物被称为“胡豆”,一种是我们现在说的豌豆,另一种则是蚕豆。豌豆的传入时间较早,《管子》里面即有“山戎出荏菽,布之天下”之语,根据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的记载,“戎菽”与胡豆同义,即是豌豆,因为“种出胡戎”而被称为胡豆。
豌豆之名则最早见于三国时期张揖所撰的《广雅》,得名是因为“其苗柔弱宛宛”。原产于中亚地区的豌豆向东传入中国后,由于对生长环境没有过高要求,得以在中国大面积种植,加之其性耐寒、耐干燥,在北方地区分布尤多,目前,我国是仅次于加拿大的世界第二大豌豆生产国。豌豆很早就走上了人们的饭桌,《本草纲目》中称其“煮、炒皆佳”;由于磨粉细腻洁白,豌豆被用于制作古时洗漱沐浴用的澡豆。同时,豌豆也是战马的主要饲料之一。
被称为胡豆的豌豆早早就在中国的百谷之中占有了一席之地,然而到了明朝,普及较晚的蚕豆却后来居上,占据了胡豆之名。蚕豆起源于地中海沿岸和中东地区,关于意指蚕豆的“胡豆”较早的记载来自成书于宋朝的《太平御览》——“张骞使外国,得胡豆种归”,指明蚕豆是张骞通西域时带回的物产。但直到宋朝,蚕豆种植一直未能大范围普及开来,北宋宋祁描写蚕豆的《佛豆赞》中写道,蚕豆“农夫不甚种,唯圃中莳以为利”,说明它此时并非大规模生产的粮食作物,而是只种在农人自家的菜圃中。苏轼曾有一次读到“豆荚圆而小,槐叶细而丰”之句,不知其所指,询问一位四川来的友人后方才知道诗中所写的是蚕豆。由于早年种植范围主要在云南、巴蜀一代,人们借云南的“佛国”之称,称蚕豆为佛豆。

蚕豆
“蚕豆”的名称则最早见于杨万里的七言诗,这首诗写于一次杨万里与友人小酌之时,友人指着佐酒的蚕豆说:“未有赋者。”杨万里于是当场戏作《蚕豆》一首,诗中赞叹:“翠荚中排浅碧珠,甘欺崖蜜软欺酥。”这一名称是其在长江流域大量种植后在当地产生的,因为它豆荚如老蚕,而又“蚕时始熟”。至于蚕豆取代豌豆的胡豆之名,也是其种植范围逐渐从四川向外扩散之后的事。《本草纲目》中记载:“盖古昔呼豌豆为胡豆,今则蜀人专呼蚕豆为胡豆,而豌豆名胡豆,人不知矣。”即因为四川人惯于将蚕豆唤作胡豆,使其他地区的人也渐渐受到影响,叫蚕豆的多、叫豌豆的少,进而人们便忘了豌豆也是胡豆。
在古代农耕社会,农家每年最困窘的便是旧粮已尽、新粮未下的青黄不接之时,而蚕豆因为成熟期在初夏,恰好能在这个阶段充作主食,帮助农人顶过最为难过的季节,《农书》称其为“百谷之先,最为先登,蒸煮皆可便食,是用接新,代饭充饱”;历朝所作《救荒书》也对其多有提及。因为量多而便宜,蚕豆在平日也被一些地区当作主要的粮食,《天工开物》就记载在湖北,蚕豆充饥果腹的价值不逊于当时普遍的主食黄米和小米。曾经重庆街头的“棒棒军”就常吃蚕豆,一方面是因为它是一种难得的便宜耐吃的下酒菜,另一方面是因为它充饥效果很好,能维持重体力劳动所需的体能和耐力。
在从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众多物产中,蚕豆并不引人注目,然而它的价值却不容忽视。清人叶申梦的咏蚕豆诗是对这种植物最好的写照:“蚕豆花开映女桑,方茎碧叶吐芳芬。田间野粉无人爱,不逐东风杂众香。”直到现在,蚕豆在四川等地还保留着“胡豆”的古称,宣示着它从丝绸之路上千里而来的西域血统。
睡莲
“浮香绕曲岸,圆影覆华池。常恐秋风早,飘零君不知。”初看或许会以为这是一首题咏荷花的诗,其实这却是唐人卢照邻所作的《睡莲》。古今的人们往往将荷花与睡莲这两种同属于睡莲科的水生花卉一概通称为“莲”,但比起荷花借《爱莲说》得封“花中君子”的声名赫赫,睡莲却显得不那么引人注目。荷花生长于中国本土,周朝时便已有“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之句,而睡莲一般被认为是自佛教从印度传入后才在中国普及开来。
李时珍曾引撰写《本草拾遗》的唐人陈藏器所言,写道:“红莲花、白莲花,生西国,胡人将来也。”据学者考证,绘制于北魏时期的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存在花瓣密集细长的莲花图样,而类似的形式在中国两汉以前从未出现过,反而能在公元前1世纪的印度石窟中找到参照,可见这一图像并非传统的荷花,而是印度传来的睡莲图样。

睡莲
睡莲得名于其朝开暮合的习性,因其“日沉夜浮,必鸡鸣采之始得”,故又名子午莲。关于睡莲的描述曾见于唐代段成式著《酉阳杂俎》,“南海有睡莲,夜则花低入水”;明代王圻著《三才图会》,“晓起朝日,夜低入水”;清朝吴其浚著《植物名实图考》,“内舒千层百花,如西番菊,黄心。亦作千瓣,大似寒菊”,等等。据《岭南杂记》、《大观录》等书记载,睡莲可采而食,“叶类慈菇,根如藕条”,“清香爽脆,消暑解酲”,然而食之令人思睡。当时广州有谚语称:毋佩睡莲,使人好眠。此外,睡莲入药可治小儿急慢惊风,据《本草纲目拾遗》记载:“杭城张子元扇店,施此救人多年矣。”
叠山理水是我国园林造景的基本手法,而作为一种常见的水生观赏植物,睡莲在园林的理水造景中也有着重要的运用。据说,早在汉代,霍光的私家园林中就有一片五色睡莲池,而后来的各类皇家和私家园林中也多栽有睡莲,颐和园的谐趣园中、圆明园的鉴碧亭下都能看到大片睡莲,配以一池静水、一座小亭,营造宁静安详的氛围。
莲花是佛教中极具象征意义的重要形象,其花萎而根不死、来年又得重发的特征符合佛教轮回生灭的观念,而其清净超脱的形象也与佛法要求的清净无碍的境界相合。佛教典籍本身并不区分荷花与睡莲,但在佛教起源的印度,睡莲的存在远比荷花更为普遍,所谓的“七宝莲花”,其中五种属睡莲,剩余两种才是荷花。因此,睡莲从一开始就作为宗教象征符号出现在艺术品中,寓意着圣洁、吉祥,典型例证便是敦煌石窟的壁画,北魏时期壁画中的莲花图样大多是睡莲的形象。此后随着佛教影响力的扩大,睡莲纹样也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出现,到明清时,“子午莲”、“缠枝子午莲”纹样已经成为瓷器、丝织品上常见的纹饰,其含义也脱离了宗教的范畴,被附加上生生不息、清正廉洁等更多意味。
开心果
开心果为阿月浑子属漆树科(Anacardiaceae)黄连木属(Pistacia)植物,约有20个种,分为中亚类群和地中海类群两类,其中50%左右是坚果,其仁可食用。
俗名开心果。一般认为这是古时的国人对这种坚果的古波斯语名称的音译。这一译名充满诗情画意,现已鲜为人知。现代波斯语称其为“pista”,英文拼写为“pistachio”,而在古波斯语中则称“agoza”。在我国的古籍中,这种坚果被称为“胡榛子”或“无名子”。人们知道的只是“开心果”这一俗称。这一俗称的缘由:一是这种坚果的形似人的心脏,成熟后上端自然爆开,因称“开心之果”;二是有一则来自伊朗的民间故事说,一对年轻情侣在这种果树下谈情说爱,正谈得热烈之时,树上成熟的果实叭一声裂开口,展露出里面微红的果仁,情人们认为这是吉兆,彼此以身相许。因此,树梢头倒挂的果实被称为“开心果”。
阿月浑子(Pistacia vera)原产中亚细亚和西亚的干旱山坡和半荒漠地区,经伊朗逐渐传入地中海地区,后经地中海地区传至中东、南亚、罗马、英国、美国等。开心果的野生种见于叙利亚、土耳其、伊朗、阿富汗以及苏联西南部的半沙漠地带,是中亚最古老的树种之一。在4000万年前第三纪时期,开心果是亚热带旱生森林干燥带中的一个树种。开心果人工栽培的历史,在西亚约有3500余年,在中亚约有2000余年,在地中海沿岸约有1500余年。

开心果
这种坚果何时传到中国,说法不一。一般认为,唐朝时期,中国同波斯和其他西亚国家交往频繁,这种坚果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唐代陈藏器在开元年间(713~ 742)撰写的《本草拾遗》中提道:“阿月浑子生西国诸番,与胡榛同树,一岁胡榛子,二岁阿月浑子也。”唐代段成式在大约860年所著《酉阳杂俎》中也有类似说法。两相印证,阿月浑子大概是在唐朝中期传入中国。可是,也有人认为,阿月浑子传入中国远在唐朝之前。唐朝的李珣在八世纪后半期所著《海药本草》中说:“按徐表《南洲记》云:无名木生岭南山谷,其实状若榛子,号无名子,波斯家呼为阿月浑子也。”《南洲记》成书于何时不详,但是,6世纪三四十年代,南北朝时期北魏的贾思勰在其所撰《齐民要术》中引用过此书。由此推断,阿月浑子可能在6世纪前后已传入中国。
红蓝花
关于红蓝花(胭脂)起于何时,后唐马缟的《中华古今注》中有记载:“燕脂盖起自纣,以红蓝花汁凝做燕脂。以燕国所生,故曰燕脂。”说的是从商纣王时期,胭脂就已经出现了。但这本书在另一处说:“燕支,西方土人以染红,中国人谓之红蓝,以染妇人面色。名燕支粉,亦作焉支。”于是后人多以为胭脂确是一种植物,即红蓝。但是用它做化妆品起源于商纣时期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先秦文献中没有关于胭脂的记录,甚至胭脂的那些异名在先秦古籍中也未曾出现。
有据可查的胭脂的异名最早出现在西汉。《史记·匈奴列传》里写作“焉支”、《汉书·司马相如传》里写作“撚支”、“烟肢”等,而“胭脂”一词,则迟至唐代才出现。据文献记载,先秦妇女的化妆品只有脂、粉、泽、黛等。这里所谓的“脂”,说的只是动物体内或者植物种子内的油脂,不是红色的胭脂。先秦时期的面部装饰以粉(白)和黛(黑)为主要色彩,即用白粉敷面,用青墨颜料画眉,不盛行脸上抹红。
中原人开始使用胭脂一般认为是从汉代初年开始的,最初这种化妆品和化妆方法是由匈奴传入中原地区的。在公元前139年,汉武帝为了加强汉朝与西域各国的联系派张骞出使西域。胭脂的引进,也在这个时候。成书于宋代的《续博物志》中说:“出于阏氏。”汉代民歌《匈奴歌》中也唱道:“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殖。失我阏氏山,使我妇女无颜色。”阏氏山在今甘肃省永昌县西,绵延于祁连山和龙首山之间,胭脂与阏氏读音相似,它是因为出于此地而得名。大约阏氏山上盛产这种被当地人叫作“阏氏”,而中原人叫作“红蓝”的植物,这种植物的花朵可以涂于面部增加桃红润泽之色,所以受到了当地妇女的喜爱,其后又逐渐传到中原,并迅速由北向南推广开来。

红蓝花
红蓝花的花瓣中含有红、黄两种色素,花开之后被整朵摘下,然后放在石钵中反复杵槌,淘去黄汁后即成鲜艳的红色颜料。之后人们又发现了紫茉莉也可制作胭脂,因此这种花又叫作胭脂花。紫茉莉夏季开花,有红、白、紫、黄等多种颜色,其中红色的可以制成胭脂。再后来,人们也用杜鹃花粉或杜鹃花汁制成胭脂。唐代王建《宫词》中写:“收得山丹红蕊粉,镜前洗却麝香黄。”山丹,即杜鹃花,唐人通常称其为山石榴花或山榴花,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也说:“胭脂,古造法以紫茆染棉者为上,红花汁及山榴花汁者次之。”
胭脂不但制作原料多样,而且制作工艺也比较复杂,一般要经过采摘、杀花、揉花、晾晒等数道工序。以红蓝花为例,每年在它开花的季节,要在一天中最凉爽的时候去采摘,然后“杵碓水淘,绞取黄汁,更捣以清酸粟浆淘之,绞如初,即收取染红,然后更捣而暴之,以染红色,极鲜明”。这是宋代的《尔雅翼》中记载的杀花程序。杀花之后就可以制作胭脂了,先要取落藜和蒿等草灰,“以汤淋取清汁”,用以揉花,此过程要反复十几次。最后,再用布袋绞取淳汁晾晒即成。
胭脂在使用时通常先晕于手掌,再匀于脸颊。唐代宇文氏《妆台记》中说:“美人妆,面即傅粉,复以胭脂调匀掌中,施之两颊。浓者为酒晕妆,浅者为桃花妆。薄薄施朱,以粉罩之,为飞霞妆。”《红楼梦》在第四十四回中写宝玉和平儿谈胭脂的用法,与此大致相同:“(平儿)看见胭脂,也不是一张,却是一个小小的白玉盒子,里面盛着一盒如玫瑰膏子一样。宝玉笑道:‘铺子里卖的胭脂不干净,颜色也薄。这是上好的胭脂拧出汁子来,淘澄净了,配上花露蒸成的。只要细簪子挑一点儿,抹在唇上,足够了;用一点水化开,抹在手心里就够拍脸的。平儿依言妆饰,果然鲜艳异常,且又甜香满颊。”这样的方法不仅涂抹均匀,而且简便易行,所以流行了很长时间。
猞猁,别称“猞猁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