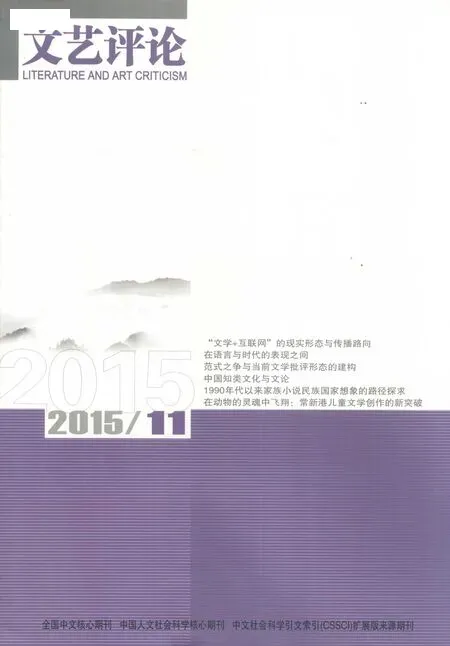“国家”、农民经验与农村幸福生活的构想——重释《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贾鲁华 乔焕江
主导性文化氛围加固了人们对苦痛的体验,继而使其获得了公共性的认同,但同时也使我们对文学文本及其所处时代的解读产生了一种结构性盲视。1978年文学作品所处的尴尬处境由此或可得到解释:一方面,对“文革”与“四人帮”的揭露和批判使人们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下文简称《许茂》)等文本产生了强烈的心理认同,使其社会学意义得到了放大,继而在后世的阐释中仍然把他们看做是新时期文学的重要作品;但另一方面,因其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展示,被人们看做是简单的政策性图解而在缺乏“文学性”、“艺术性”的意义上得到质疑。因此,在我们重新探讨《许茂》的过程中,也就不得不重新还原文本中各种权力关系的相互博弈,重新发现文本中对农村生活秩序调整的生成性力量。这样的重新解读,在嵌入当下不同意识形态的同时,也事实性地会参与当下农村文化的建构,为当下农村的文化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潜在资源。
由此我认为,在当代文学中,小说《许茂》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其独特性不仅仅体现在它短时间内迅速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对“文革”与农村题材进行了文学式的处理并有所突破,①也不仅仅体现在它从发表伊始就被影视制作者关注并改编成了多部影视作品,更体现在因上述两个因素而成的诸多不同版本(文本)连同小说内部在处理主题时构成了一个多种力量并存并相互博弈的问题域,恰是这个复杂的问题场域容含了对于农村幸福生活构想与寻觅的多重可能性。
一、1978年与农村幸福观念的不同面向
在《许茂》②中,多处提到了“幸福”和对“幸福”的讨论。但何为幸福?这确为一个难解的问题。毋庸置疑的是,幸福观念作为一种主观或心理体验的外化性话语表述,因其背后诸多力量的参与建构而具有着不同的维度,其中涉及到时代环境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个人体验和主导文化的形塑等多种力量,因而具有了个人性、社会性、历史性等不同的幸福面向。具体到农村幸福生活的构想,亦有着时间与空间维度上的复杂结构和漫长农村历史文化延展过程中的逻辑缠绕。即是说,农村幸福观念的构想是一个斑驳繁杂的乱团,其复杂构成并非是仅仅靠理论述说即可把握。因此,我们只能返回特定时代和具体文本中加以解析。而《许茂》中对“幸福”的讨论给我们提供了阐释契机。
小说展示的是那个世人似乎已有定论但也存在着诸多阐释可能性的1978年,对此作者周克芹说:“十年动乱,民不聊生,穷乡僻壤也难于幸免,真是‘社不成社,家不像家’。”③对“文革”和“四人帮”的批判、对农村民生凋敝现状的哀叹显于笔端,沿着这条思路,我们或可断定小说中所讲的故事(1975年冬)势必会有着揭露、批判、控诉等类似于“伤痕文学”④或政策宣传式作品的模式化痕迹,但事实上绝不尽然。周克芹首先是一个农民、一个农村基层干部,其次才是一名作家。他有着深厚的农村生活基础和经验,对农村、对农民、对土地有着浓厚的感情,这应该是他的文学创作所必需的情感基调和所要处理的主要题材。这使得周克芹超越了“诉苦”式的“伤痕文学”,也使其没有仅仅在描述农村风俗、民情、街坊邻里之间的鸡毛蒜皮上止步不前,当然也更不会自恋或自怜地抒发自己的小性情,而是“感觉”到了农村的“生机蓬勃”:“纵眼望去,葫芦坝是满目疮痍;然而,置身于其中,却感觉到葫芦坝生机蓬勃。”这是一种融入骨髓的、隐忍而又乐观的农村生活信念,而绝非关注个人化伤感与控诉的“伤痕文学”所能及。同时,这种乐观的生活信念也源于其创作时国家的政策调整。小说创作于1978年、修改于1979年,正值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拨乱反正”、转移工作重心的起始时期,周克芹势必会受到中国整体氛围的影响,使作品充满了胜利、欢快的希望,从而使其创作满足了不同群体的不同诉求: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需要政策宣传、中国人民需要看到希望,作家周克芹满溢的感慨和情怀也趁此得以尽情抒发和阐释。恰如孟繁华在评述1978年的文学时所言:“就意识形态来说,动员民众参与实现现代化的期待,并藉此完成社会发展形态的转型,在新的目标设定中使民族心理重新获得自振并建立自身的权威性和社会信任感,是它重要的时段性任务;就作家的内心需要来说,挣脱长久以来的‘一体化’的精神统治,争取精神自由,表达他们对社会公共事物的参与欲望,并以此体现知识分子的英雄情怀,使他们大有恰逢其时之感,他们的倾诉欲望终于有了机会得以满足。”⑤由此而言,《许茂》参与了1978年“激情岁月”的建构,既契合了国家拨乱反正的整体氛围,又使同时作为农民和作家的周克芹对农村生活的体验与对农村幸福生活的想象得以抒发和述说。但是,幸福一直与个人及其所在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联,个体的幸福观念也孕育于时代丰富、复杂的文化内蕴。《许茂》构建的话语场域中,人物形象对幸福的想象通过具有1978年特色的土地、劳动、物质、爱情、政治意识等观念呈现了出来,而他们对幸福的理解与构想则又展现了1978年世事的波诡云谲。
土地是乡土中国生死存亡的根本、是农民生存的根本,土地寄寓着农民对生活的渴盼和希望,即是说,土地是农村幸福生活构想的一个基本元素。但是,中国近代社会起始的1840年至1921年,“占全国人口不到10%的地主、官僚、贵族占有全国绝大部分的土地;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农民,则没有或只有很少的土地。”当时,“穷苦农民被迫借高利贷,春借一石,秋还二石,陷入了饥寒交迫的困境。”⑥在土地上劳动的农民们没有土地,不劳动者却成为了土地的所有者。在粮食与物质等基本生活条件得不到保障的情势下,农民潜在的革命性通过各种方式在以后的斗争中逐步被挖掘出来。经过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以及国民党不同时期的土地制度,一直到1921年中共成立及其后的革命探索,农民的主体地位得以逐步确立。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有过这样的分析:中国的农民问题,主要是半自耕农和贫民的问题;“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受到革命的宣传。”⑦自此,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到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中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土地,继而拥有了为自己劳动的权力,物质生活也得到了一定改善。可以说,土地改革,乃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一直洋溢着幸福的情绪,这在《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艳阳天》等作品中都有体现。《许茂》中的许茂老汉即为这一时期享受到幸福的典型形象,每年女儿们为他祝生的“那几天正是老汉最高兴的日子:他不仅破例地要喝一些酒,而且酒后还要和女婿们谈谈庄稼经;远地归来的女儿们听着他幸福地回忆起合作化、高级社年代担任作业组长那阵,如何费心费力地经营集体的农副业生产,都不由得十分感动……老头忙着集体的事情,整天脸上泛着红光。那年头,是许家最为昌盛发达的年代,也是许茂一生中最为光辉灿烂的年代啊!”虽然在文本叙事中,“十年浩劫”破坏了他的幸福生活,致使其自私、甚至狡诈的一面凸显出来。但是,土地、劳动和粮食的获得是其记忆中最为幸福的时刻。当记忆在适当的时候得以阐释与发掘,其力量会随着记忆主体的行为而嵌入社会变革的机体之中,其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顺利推行”或可在此找到了传统乡土文化基础。
爱情是文学中最为恒久的主题之一,爱情及其延展形式——婚姻——的获得是男女人物形象获取幸福感的最常见形式。然而,爱情与婚姻中的复杂纠葛却让幸福有着难以言说的意味。从鲁迅的《伤逝》,我们看到了爱情与物质的纠葛;在蒋光慈的《野祭》和《菊芬》中,我们看到了爱情与革命的纠葛;在展示社会主义实践的文学中,我们看到了爱情与阶级的纠葛;《许茂》中四姑娘的爱情则让我们看到了爱情与婚姻、与时代的纠葛。离婚竟然使得四姑娘重燃生活的希望,这种隐喻式的叙述,既是对郑百如造成的个人性苦痛的痛斥,也是对“文革”造成的人民苦难的控诉。因此,饱经风霜的四姑娘脱离苦海之后的希望就具有了双重性,一是对金冬水的爱情以及重获幸福家庭有了希望,二是希望雾霭笼罩的中国迎来春天。事实上,四姑娘对金冬水的爱情、九姑娘对吴昌全的爱情、吴昌全对七姑娘的爱情,都已经显露出超越革命、阶级对爱情的规约,有了个人性感情追求的趋向。但是,1978年的社会氛围仍然使个人性的爱情追求受着诸多因素的制约。比如,“对于质朴的农村姑娘(九姑娘)来说,恋爱是不需要‘谈’的”,只是用自己所见所闻在心中细细斟酌即可确定自己的心中人,“她需要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同他一块儿并肩作战,去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国家级”理想同个人性的爱情相融合,恰是1978年文学主题的独特呈现。然而,这种结合并未使九姑娘的感情有一丝虚假、做作,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九姑娘对未来的幸福生活才充满了更为充分的激情与希望。
工作组组长颜少春的幸福想象则以其政治意识为基础,必然的与国家命运相关联。事实上,《许茂》中的各人物形象都有着1978年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数十年的“一体化”意识形态对农村生活的渗透,十年来“文革”式的政治性话语和行为方式深深嵌入了人们的意识与行动之中,主导意识形态中当然容含着人们对农村幸福生活构想的因子,由此而受到影响的农民也有着因“翻身当家做主人”的身份转换而成就的幸福想象。
1978年是一个容含着苦痛和希望的时期,其中国家政权及其衍生品所显示的力量和农村的内生性力量是此时代氛围构成的显明性动力。也正是基于此,在农民幸福生活的想象结构中,有着时代因素造成的共识,亦有着个人具体生活体验与个人性情造就的个体化面向。
二、1978年的“国家”与农村幸福生活的想象
1978年的风起云涌使其具有了象征意味,“谈论起它就意味着体验共同的解放、拥抱共同的复活节,它仿佛传达了这个民族共同的情感与幻想,共同的精神向往与内心需要,它是人们激情奔涌的新的源头,往日的心灵创痛因它的荡涤抚慰而休止并且康复”⑤。《许茂》中的农民们正是在这样的“激情岁月”中拥抱着激情与希望奔向明天,探求着想象中终将来临的幸福生活。
四姑娘徐秀云在与工作组组长颜少春的谈话中有这样一个疑问:“今天晚上大家讨论修电站,点电灯,改河造田多打粮食,这些计划全都是很好的,实现了,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可是,我就想啦,将来什么都实现了,不愁吃,不愁穿,住砖瓦房,装上电灯,那样就算‘幸福生活’么?‘幸福’两个字的意思就只是吃喝穿戴么?……唉呀,我说不清楚。”面对善良、坚强的四姑娘的问题,颜少春似乎并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是她确认“‘幸福’二字当然不是指的吃喝穿戴”,并且接着说了一句颇有意味的话:“你会得到真正的幸福的!——所有的好人,哪怕受了多少磨难,终归会幸福。共产党干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你和所有的劳动人民谋求幸福!要有信心,那样的日子总要到来的”。千百年来,中国农民对于“好日子”的想象无非就是获得自己的土地、“不愁吃、不愁穿”,中国共产党及其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通过土地改革使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又通过农村合作化运动使“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理想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满足,建立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承诺也满足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想象。这种“共同幸福”的社会构造通过不同的方式渗入农村生活,甚至对农民为美好生活的实现而“鼓足干劲”的气象提供了政治性的基础。但是,政治性的社会想象和话语在进入农村生活却也要经历一个复杂的程序。从不同方式的宣传到直接的权力渗入,国家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想象一直都是农村社会发生变革的最强推动力量之一。
许家八妹是一名军人,是许家一个颇有“学识”或者说应该接受了正规党政教育的人物形象,她在小说中并未直接出场,但是她给家里的一封信却成为了一个把农村社会与国家命运勾连的启示:“国家”安宁是个人幸福的保障。并且断言:“四姐是一个好人,总有一天她会得到幸福的。”“今年全国的形势比去年好。那样的日子正在到来”。1975年冬,这的确是一个令国民看到些许希望的时期。小说在描述金冬水这一人物形象时,给出了“好形势”的直接描述:“这一年春天里‘四届人大’吹起的春风,夏天里,传来党中央关于整顿各条战线的喜讯,特别是深秋时节,华国锋同志、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了那个农业会议之后,出现了辽阔农村的热浪,鼓动着葫芦坝上这位受贬谪的共产党员的心扉,敲击着千家万户庄稼人的门窗。”这样显明的政策性宣传通过小说传达出来,其意味是颇值得寻思的:一方面,这种宣传是周克芹向读者的宣传,另一方面,这是共产党员金冬水的内心体验。这是主导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宣传策略,亦显示了国家政策介入农村后对农民与基层干部心理结构的成功形塑。即是说,国家政策作为农村社会变革的力量,既述说了国家对农村幸福生活的构想,也通过各种方式嵌入农村生活,从而使农民的心理结构和对幸福生活的想象与国家主导性机制相融合。
以颜少春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连云场(之后去了葫芦坝),则意味着以政权直接介入乡村的形式为乡村变革注入力量。他们到底为民众带来什么?她是人们盼望已久的“清官”,还是像“文革”时期别的工作组那样,“不抓生产,不抓群众生活,大家都断顿了,可他们还硬叫学唱样板戏”?颜少春为组长的工作组进入农村时受到了诸多的猜疑甚至排斥,这自然是国家政权介入农村时不同力量之间的博弈,亦是农民自身经验或者内生性力量对外来力量的抗拒和排斥。但代表国家和中国共产党的颜少春的到来的确为村民带来了别样的话语:“农民为什么跟共产党走呀?——还不是因为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给农民带来好处……可是,后来这只船像搁在浅滩上,走不了啦!贫困像鬼魂似的跟着他们。特别是这些年来,党的政策总是落不到实处……想想嘛,在这种情况下,像许茂大爷这样的农民,他能不怀疑吗?能不想想自己的前程吗?”这段话语确可以视为20世纪80年代国家政权对稳定农村生产秩序的宣言,也契合了农民对“好日子”的想象;当然,这同时也是对“四人帮”与“十年浩劫”破坏农村生产秩序的控诉。正如颜少春所言,农民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一方面源于无土地的贫困生活与其造就的农民的革命性力量,另一方面在于共产党让农民过上“好日子”的承诺。如若不考虑小说文本对国家政策太过显明的描述,这样的政策性解读对于农村生活秩序的恢复确是正当的、极具合理性的。颜少春的个人生活经历也为她践行“正确路线”的政治宣言提供了融入农村社会的可能性:她对农事的了解,对农民行为和思想的理解,都为国家和党的政策进入农村获得了经验性的支持。但在文本中,颜少春的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遇到了来自各方面利益团体的阻挠。事实上,颜少春遇到的困难与无奈,象征性地体现了国家政权介入农村生活、面对百废待兴时的无奈,也显示了农村空间中各种力量的权衡与博弈。
三、农民经验与“幸福”构想
不可否认,国家的土地改革政策和惠农政策为农村、农民的幸福生活带来的诸多希望和实际影响,但我们不能忽视乡村内部主要由农民生活经验构成的内生性力量。农村生活有其自身的逻辑延展,虽然构成这一逻辑的诸多因素在争取自我利益诉求的过程中也呈现出了斑驳繁杂的态势,农民个体不同的经验也造就了一幅异常复杂的图景,但是农民的行为和思想在其中也亦能找到合理的解释;虽然大多时候农民个体所经验的现实和赋予它的意义是片面的,但已然构成的经验和意义也为他们理解事物和行为提供了基础。并且,“只有把握了此类丰富的经验,我们才能对一个特定的经济体系如何影响了构成它、维持它或取代它的事物进行有意义的分析。”⑧恰如小说《许茂》中所言:“人们大凡都是从自己直接的、具体的生活感受出发来进行思考的。”
事实上,在农村幸福生活的构想过程中,不仅仅得益于新中国与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方式的引导乃至于改造,农民来自于生理性需求与传统文化的对“好日子”的热切期盼也是一个重要的力量。细心的而又有学识的颜少春分明看到了存在于农村、农民自身的一种热情和希望:“来到葫芦坝时,她既看到一种劫后的荒凉景象,也看到了人们对于美好未来的热烈追求和向往……在颜少春看来,无不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表现出那种‘对于美好前途的追求和向往’。”
葫芦坝村民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对土地的坚守、对家庭的构想、对旧社会的痛恨、对土地改革和合作社的信任以及对“十年动乱”的复杂体验沉淀在了自己的心中,铸造了一个难以条分缕析的复杂心理体验结构。恰是农民与时代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此心理结构,为我们合理地解释村民的行为提供了基础。同时,也为我们阐释小说《许茂》提供的一种潜藏于文本内部而又不同于惯常的对“文革”的阐释视野,为我们寻找农村进步的生活秩序和构想农村的幸福生活提供一种农村的内生性力量。就吴昌全这个在小说中并不突出的人物形象而言,作者把他塑造成了一个坚守土地、热爱农村的年轻人,他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国家“农业现代化”的倡导,同时又是一种自觉的行为:“他对乡土的眷恋,对以提高产量为目的的科学研究倾注满腔的热情,既不是为了完成谁交给他的任务,也不是出于好奇的心理,更不是为了去领赏,完全是一种强烈的热爱人民的情感,使他对农村家乡的贫困感到切肤之痛……他天真而又诚挚地相信:靠集体的力量,用新的科学办法生产,就一定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然而,这种高度道德化的人物形象在我们看来的确又与普遍性的农民形象⑨多少有些游离。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吴昌全母子、金冬水等人物形象看作是国家与党的政策与构想在农村产生作用的完美体现,但又并非仅仅由此单一力量在形塑着他们的心理结构:农村千百年的生活逻辑以极强的稳固性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逻辑延展,潜在地影响着农民的行为和对历史变迁的看法,甚而形塑着他们对“好日子”的构想。其间,如上所述的对土地、爱情等的观念体现了不同面向的幸福想象,而推动其生成的内生性力量确部分源自传统乡土中国文化的沉淀。⑩
小说对许茂有这样的描述:“遇事都有主见、按着自己的方式思考问题和决定‘政策’的许茂老汉。”这种“主见”与“自己的方式”是一种什么力量,能够促使许茂老汉按照自己的方式理解国家“政策”?小说呈现出的许茂是一个“孤僻、自私、固执、奸诈、冷酷”⑪而又不乏善良、温情、内涵丰富、具有普遍性的农民形象。这么丰富的形象意蕴就怪不得周克芹把自己多年对农民问题、农村问题的思考都寄托在了许茂身上。应该说,许茂身上有着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想的影响,有着基层干部在践行国家决策过程中渗入的诸多利益争夺对其性格的扭曲,还受到自己特殊家庭结构的深深困扰,亦有着农村生活千百年的积淀在其身上的延续……
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辩驳的共识。千百年来的农民对土地的热爱和坚守受到过太多的热情歌颂和描述,旧社会农民爱土地而无土地的尴尬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在形式上已经化为泡影,极大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热切期盼。许茂“是一个被土地牢牢束缚着的农民”,小说对其爱土地、爱劳动亦有着形象的描述:“青青的麦苗,肥大的莲花白,嫩生生的豌豆苗,雪白的圆萝卜,墨绿的小葱,散发着芳香味儿的芹菜……一畦畦,一垅垅,恰好配成一幅美丽的图画……许茂这块颇具规模的自留地,不是一块地,简直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这是他的心血和骄傲。”农业合作化使土地成为了集体财产,但是自留地仍然极大满足了许茂老汉对土地的热爱、对劳动的尊重与渴望,这并非仅仅是“吃饱饭”所能解释的,而是千百年农村社会的固有逻辑才使得许茂这样“伺候”着自己仅有的一点“自留地”。
被人视为“自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许茂并非一直是这样的形象,他对国家与党的想象也并非一直如此。与其说许茂以自己身上固有的农民思维思考着农村问题,不如说“文革”时期扭曲了国家决策的工作组的行为与农民思维相互作用与融合才致使小说中许茂形象的产生。在这样的视野中,以颜少春为组长的工作组进入葫芦坝时,许茂的不欢迎态度才可得到合理的阐释,既不舍得自己的房子让别人住、心疼自己的灯油和粮食,又由于先前工作组对农村生产秩序的破坏而形成了抵触心理。
许茂在土改与合作化时期,一直以一个积极参与者的形象出现,那也是自己一直引以为豪的时期,靠着国家的正确决策和自己的辛苦努力,盖起了一座“与众不同的气派、宽敞、明亮”的“带石头院墙的三合头草房大院”,并获得了“爱社如家”的殊荣。然而,当“浩劫”来临、“工作组”进入农村后,许茂并没有像郑百如那样趁此挺进、“咒骂共产党”的同时却获得了党的信任,没有像吴昌全那样潜心于自己的农业科技实验,也没有像三姑娘等大多村民那样随波逐流……这个曾经获得荣誉的农民老汉隐藏起自己的“革命”热情,同时,“当许多人高喊着革命的口号进行着政治战争,几乎忘掉了土地的时候,许茂却为着自己的利益,运用他惊人的智慧,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拼命聚集着财富”。“浩劫”阻断了他对“好日子”的想象、剥夺了他劳动的权力,他的行为是九个孩子要抚养而妻子早亡的特殊家庭的无奈之举,更是一个真正的农民要在土地里劳作的内在信念所致。他以自己的方式在“动乱”的气氛中生存着,“在‘空隙’里生活着和发展着”,一个要土地而无土地、想劳动而让“排样板戏”的岁月里,许茂老汉却坚守着自己心中“好日子”的构想与信念,在国家政权与农村社会的夹缝中辛苦地践行着“农民”的生活。
因此,如若对许茂老汉仅仅做道德化的谴责,并不能合理地对小说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进行有效的认识与解读,更会造成对小说呈现的时代有着结构性的盲视。国家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构想和对农村幸福生活的承诺,在乡土社会的践行中往往会遇到异己的力量,这其中最强有力的就是诸如许茂身上存在的农村社会的内生性力量。
小结
从周克芹的小说《许茂》到各种次生文本,虽然在批判“文革”与“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倡扬农村经济的现代化发展乃至于新农村建设构想方面做出了文学性的处理、且取得了不能不承认的成功,但是如若深究,我们却分明可以看到在农村幸福生活的想象上存在着诸多的裂隙和诸多力量的博弈。
从1956年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到2014年中央“1号文件”对农村社会的设想与承诺,中国乡土社会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之深、之广,从农村的巨大历史变迁和农民生活的变化可见一斑;但是同时出现的“三农”、农村环境污染、农村空心化、特别是农村民众的精神危机等问题,却是仅仅凭借国家的正确决策很难有效解决。⑫目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小城镇建设已经成为了解决农村问题的主流性话语,但在构想和践行农村幸福生活的过程中,我们还不得不依靠和顺势引导存在于农村的诸多力量、特别是乡土社会的内生性力量。我想,国家决策只有同农民对“好日子”的理解与想象相融合,“缝合”起话语、想象中的诸多裂隙,中国农村的幸福生活才可以得到合理的构想,农村才可以使各种力量相谐而存在,构筑起有“中国特色”的“乡土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