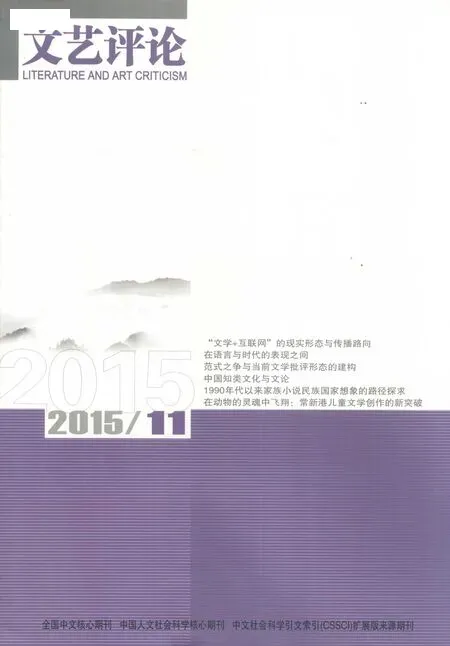智性叙事中的精神剖析——评秦巴子长篇小说《身体课》
○王春林
虽然早在阅读《身体课》(载《花城》2010年第4期)这部长篇小说之前,我所知道秦巴子是陕西一位很有影响的优秀诗人。此番真正吸引我阅读注意力的,其实还是小说那迥异于寻常的标题。之所以如此,一方面的原因在于,当代中国文学曾经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把本来与文学密切相关的“身体”全然放逐在了文学的领域之外。事实上,这样一种肉身的被抽离,相当严重地影响着那一时期中国文学更高成就的取得。既然曾经放逐过身体,甚至于把身体当做了文学书写的某种禁忌,那么,秦巴子如此堂而皇之地标举身体的行为,当然也就引起了我的高度注意。但在另一方面,或许也正是出于对以上情形一种本能反弹的缘故,到了晚近一个时期,伴随着物欲的极度泛滥,实际上只是标举着欲望的所谓“身体”写作,却又在中国文坛弥漫一时。置身于如此一种现实文化语境之中的秦巴子,居然把自己的长篇小说径直命名为“身体课”,难道说优秀的诗人也要迎合大众市场的物欲需要,也要在小说领域“秀”一把“下半身”写作的风潮么?这样的一种强烈疑问,自然也是促使我高度关注秦巴子这部长篇小说的一个根本原因所在。
然而,只有在真正地深入到秦巴子《身体课》的文本内部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此前对于作品的两种想象,与文本实际仍然存在着较为遥远的距离。就后者而言,秦巴子的小说虽然径直命名为身体,但这身体却与时下那种只是意味着物欲泛滥的身体无关。尽管说,小说中肯定少不了关于欲望的描写与展示,但严格地说起来,秦巴子之本意却并非只是到欲望的表现为止,而是更胜一筹地把欲望也当做了自己的审视反思对象。就前者而言,秦巴子固然堂而皇之地把包括肉身在内的身体纳入了自己的诗学表现范畴,而且这身体的出场显然已经构成了对既往禁欲主义氛围的强烈挑战,但我们却必须注意到,秦巴子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并没有简单地矫枉过正似的把身体肉身化。在充分强调身体肉身化特征的同时,把身体作为肉身之外的复杂精神特征也呈示出来,正是秦巴子这部长篇小说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
我们总在强调文学是人学,但却往往忽略了人的存在乃是以身体的形式而现身的。离开了身体,人实际上也就不复存在了。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文学与身体之间,事实上存在着异常密切的关系。“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同在,虽然我们总是难以确切说明如何同在。按照各种各样的概念和隐喻,可以说我们是在我们的身体里,或者是我们拥有一个身体,再者就是我们与身体一致或者疏离于身体。作为爱恨情仇各种情感的对象,身体既是我们自己,也可以说是他者。对于精神分析学来说,它是主要的自恋对象。而对于虔诚的禁欲主义者来说,它是阻碍精神圆满的危险的敌人。在多数情况下,身体在诸如此类各个极端之间处于一个摇摆不定的位置,它既是快乐的主体和对象,又是无法控制的痛苦的化身,对理性的反抗,以及终有一死的载体。”“在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品中,身体总是幻想的对象,它同时是指意活动——作为心灵和意志对于世界所发挥的作用,这种活动采取一个外在于物质性的立场——独特的他者,在某种意义上又是这种指意活动的媒介(比如这只正在书写的活生生的手),甚或是它进行刻录的地方。关于文学中的身体的问题特别让人感兴趣,这是由于文学和身体两者之间明显的距离和紧张,一种与两者互相依赖的感觉并存的、‘自然’和‘文化’之间无法消减的紧张。长久以来,让身体进入写作是文学最为关注的问题。反之,让写作指向身体则意味着试图将物质的身体变成指意的身体。”①在这里,彼得·布鲁克斯对于人的存在与身体以及与文学这三者之间的内在紧密联系进行了足称深刻的分析阐释。尽管我无法确证写作《身体课》之前的秦巴子是否意识到了彼得·布鲁克斯《身体活》的存在,但这部小说之暗合于《身体活》中的某些相关论述,却是毋庸置疑的一件事情。直截了当地说,也只有通过秦巴子的写作行为,才使得他笔下那些人物形象“物质的身体”变成了内涵丰富的“指意的身体”。
《身体课》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报纸上一个偶然的关于出土白瓷女裸体塑像的报道,促使女主人公康美丽回忆起了自己青年时期的一段人生情感遭际,回忆起了“文革”期间特定情形之下与雕塑家陶纯(虽然,那时候的康美丽并不知道雕塑家的名字叫做陶纯)的一次猝然相遇。正是那次猝然相遇,使得康美丽形成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身体高潮。让人难以预料的是,如此一种青春记忆的唤醒,居然使康美丽经历了一次史无前例的精神危机。这次精神危机的形成,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康美丽自己的心理状态,而且还自然而然地波及影响到了身为私企老总的丈夫林解放与身为报社记者的女儿林茵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尤其是在确证了雕塑家陶纯居然是林解放的生父之后,康美丽再也无法延续自己和林解放的婚姻生活,无法忍受林解放的身体存在,最终以离异的方式结束了他们长达三十多年看起来还算平静的婚姻生活。故事的主线之外,小说还穿插叙述了林解放与林茵的若干与身体紧密相关的情感遭遇。从常理而言,如此一种相对简单的故事情节,可以说绝对无法满足一部长篇小说的篇幅要求。一般而言,传统长篇小说所表现的应该是一个相对长时段的,既具有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又具有可谓是跌宕起伏命运遭际的客体对象。用这样的价值标准来衡量秦巴子的这一部《身体课》的具体表现对象,则无论如何都是不合适的。
然而,秦巴子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具有某种点铁成金的天才,他居然能够把这样一个看起来相对简单的故事演绎成了一部真正具有思想艺术原创性的优秀长篇小说。实际上,也正是依凭着这一点,秦巴子的《身体课》才告别了传统,才成为了一部“现代”意味特别强烈的长篇小说。我们之所以强调《身体课》已经不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就是因为作家的叙事重心已经彻底地远离了传统长篇小说中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命运,取而代之的,乃是叙述者对于笔端人物形象所进行的那些堪称精彩的心理精神分析。就我自己有限的阅读体验而言,在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的写作历史上,如同秦巴子的《身体课》这样彻底地放逐了传统的故事情节,完全把对人物的心理精神分析作为文本核心构成的长篇小说,绝对是第一部。我们都知道,在一般的意义上,只有严谨的学术著作才会采用逻辑层次分明的理性分析式的写作方法,而小说创作尤其是长达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只是应该采用具有强烈动作性的感性叙述手段,方才有可能吸引更多大众读者的阅读注意力。与此同时,秦巴子的这种写作方式,还必须得直接面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巨大挑战。此处所谓中国文化传统就是指,虽然我们也有所谓的哲学存在,但严格地说起来,中国文化传统中所严重缺失的,正是一种带有突出思辨性的逻辑分析能力。因此,在现代社会与现代思想形成之前,分析方法的严重缺失,的确可以被看作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根本特征所在。与中国文化传统形成鲜明对照的,自然就是西方的文化传统。虽然很难说西方的文化就不重视综合的认识方式,但相比较而言,西方文化自文艺复兴以来,便特别注重于事物细部的内在分析,却又绝对是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正因为中国文化向来缺乏分析的传统,所以,秦巴子以一种分析的方式为主体来写作一部长篇小说,自然就意味着对于中国文化传统一种强有力的挑战。进一步说,挑战中国文化传统倒在其次,关键的问题更在于,秦巴子的如此一种长篇小说写作方式,体现出的是一种强烈的艺术实验精神。别的且不说,单就《身体课》所凸显出的这样一种鲜明的艺术原创意味,它就应该在中国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格局中占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
要想更准确地为秦巴子的《身体课》作出恰当的定位,我们就必须首先对新世纪以来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总体状况有所了解。“与形式层面上的实验探索特别活跃,小说文体创新意识相当突出的20世纪90年代相比,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确实从整体上呈现出了一种格外沉寂的发展态势。虽然小说文体创新意识的匮乏,并不意味着就缺少能够称得上优秀的小说作品,但中国的长篇小说创作在新世纪明显地失去了对于所谓先锋叙事的尝试运用热情,却又的确是一种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从文学创作的基本发展演变规律来看,这或许是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蓬勃异常的先锋叙事创造期之后,一个自然的创作调整期的出现。一个十分明显的迹象就是,这个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了一种相当普遍的回归传统现实主义叙事模式的艺术倾向。许多作家重新回到五四文学、回到古典文学中去汲取有益的精神养料,力求在既往长篇小说艺术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探寻带有某种鲜明本土化特征的小说文体形式。”②正是因为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作家在小说创作方面普遍地失去了具有强烈实验色彩的思想艺术层面上的探索热情,所以,那些依然有勇气坚持在小说的艺术层面上进行实验探索的作家,就显得格外难能可贵,就理应得到我们的充分尊重。
然而,秦巴子在《身体课》中所一力坚持的如此一种理性分析式的叙事方式,较之于一般意义上的先锋叙事而言,无疑有着更为鲜明的艺术原创性色彩。如果说其他一些作家的先锋叙事,尚且有迹可寻有具体来历可言的话,如同秦巴子《身体课》这样的一种先锋叙事方式,就如神龙见首不见尾似的根本就没有多少来历可供探寻。惟其无迹可寻,秦巴子此作艺术层面上的原创意味就更其突出了。我们曾经注意到,在谈到阿根廷杰出作家博尔赫斯的时候,人们最喜欢的一种说法,就是把他说成是“作家中的作家”。人们以这样一种特别的言辞表达方式,来充分肯定博尔赫斯在现代小说艺术层面上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在这里,我也想仿照这样一种说法,把秦巴子《身体课》在先锋叙事层面上所做出的努力,称之为“先锋叙事中的先锋叙事”,以此来充分肯定这部长篇小说艺术层面上所取得的不容忽视的原创性成就。
如果说我们平常所习见的那种长篇小说叙事方式具有突出的感性特质的话,那么,如同秦巴子这样一种心理精神分析式的小说叙事方式所表现出的,自然也就是一种鲜明的理性特质。大约也正因为如此,我更愿意把秦巴子在《身体课》中所具体采用的这种分析式叙事方式干脆命名为智性叙事。以如此一种智性叙事的手段,内在地切入到现代人的身体构成当中,对于现代人欲望与情感相冲突的心理精神世界做一种真切的描写与表现,因而深入地洞察发现现代人的某些精神奥秘,恐怕正是秦巴子写作这部长篇小说的根本动机所在。在我的理解中,秦巴子之所以要把自己的这部长篇小说命名为《身体课》,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对于笔端人物身体的分析性描写,事实上占据着文本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但在另一方面却也是因为身体上的若干重要部位,乃依序成为对于长篇小说创作而言极为重要的基本结构。熟悉当代新诗的人都知道,作为优秀诗人的秦巴子,其最有影响力的诗歌作品之一就是《雕塑家》。到了长篇小说《身体课》中,作为前言出现的果然是这首名为《雕塑家》的诗歌名作。另一方面,小说中严重地影响着故事情节走向的一个人物形象,其身份也正是雕塑家。把这几个因素综合到一起,就不难判定,秦巴子的这部名为“身体课”的长篇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恐怕正是作家充分地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从诗歌《雕塑家》出发进一步演绎完成的。能够从一首相当抽象概括的诗歌出发,演绎出一部长达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来,充分证明秦巴子拥有着超乎于寻常的艺术创造智慧。
具体来说,秦巴子乃是依循着人体上的眼睛、鼻子、嘴巴、耳朵、乳房、手、阴部以及脚这样一个基本上自上而下的方式来渐次展开他的分析性小说叙事的。其中,出现于第一章“眼睛,观看与窥视”中的一部分内容,我以为带有强烈的元叙事意味,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这部长篇小说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实际上,窥视是人类最热烈也最难以满足的欲望之一,是人性中的一种古老本能。人人都曾经历过成长过程中对神秘的异性的好奇,而那大胆者窥视异性的‘罪恶行径’,会遭到同伴的嘲笑甚至诅咒,然而,那嘲笑与诅咒却常常带着一种邪恶的快意,其实,这快意与被嘲笑被诅咒对象的窥视行径有着同谋的意味。在某种意义上,人人都是窥视者。窥视的本能源于人类好奇的天性。好奇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内驱力——然而,这种好奇之心并不必然指向认识的有用性,很多时候,仅仅是好奇心的满足,就可以令人欢天喜地。”秦巴子在小说中,写到了一位既是诗人,也是情不自禁的窥视者的知识分子形象冯六六。出于对林茵近乎于疯狂的迷恋,他专门在林茵家对面的高楼上租了一间房子,经常以窥视的方式既观察着恋慕对象林茵的日常生活,同时也了解着林茵一家的基本生活状况。在对冯六六带有一定变态意味的窥视行为进行了一番描写分析之后,秦巴子写下了如上一段关于窥视行为的分析性文字。
在这段文字中,作家由冯六六在公众层面上肯定为人所不齿的窥视行为,进一步谈到了实际上“人人都是窥视者”这样一个不无惊人意味的观点。只要联系现实生活仔细地想一想,就不难发现,作家的这种说法,其实是很有一些道理的。由此再联想开去,进一步联想到小说的写作行为,就可以发现,人群中最符合窥视者特征的,实际上正是小说家自己。所谓的小说家,不正是在以小说创作的名义近乎堂而皇之地窥视了解并表现着他者的生活状态么?在这个意义上,则秦巴子自己首先就是一位出色的窥视者,他把自己所窥视到的关于康美丽、林解放、林茵以及冯六六他们的生活与精神状况,以小说艺术的名义展示在了广大读者的面前。与此同时,作为读者的我们,也在借助于秦巴子的分析式叙事观察了解着康美丽他们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这些读者的阅读行为,也同样带有鲜明的窥视意味。或者也可以说,我们是以作家同谋者的身份,以一种共谋的方式,与作家一起合作完成着一种冠冕堂皇的窥视仪式。那么,强调作家的写作与读者的阅读行为均带有突出的窥视色彩,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意味呢?我想,对于窥视色彩的强调,其实是在强化着现代小说对于人的内在世界隐秘性的洞察与表现。既然是窥视行为,那当然就是被窥者所无法察觉的。既然被窥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一举一动早已经进入了别人的视野之中,那么,他也就不可能自觉地进行自我遮蔽。这样一来,被窥者就会把自己最本真的生存状态充分地展示出来。作家和读者,也正可以凭此而相当透辟地抵达人物形象内心世界的深处,然后淋漓尽致地把现代人精神世界的真实呈示出来。
同样值得引起我们高度注意的,是第一章中的另外一段叙事话语:“当然这只是作者我的视角,我的观看,我的想法。也许,康美丽当时并不是这样想的,她只是不经意地躺成了《裸体的玛哈》那样的姿势,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躺成了马德里斯画中那些有着‘神秘的性感’的女人的姿势,她并没有刻意地要诱惑谁(林解放,或者读者,或者作者)。那所谓的诱惑的意味,只不过是林解放、读者(经作者的诱导)和作者本人以各自不同的观看角度看出来的罢了。”这一段叙事话语的元叙事意味,同样是非常突出的。在这里,秦巴子清醒地意识到了写作主体的有限性。应该注意到,作者作出此番分析的前提,是他已经借助于叙述者的口吻对于康美丽的言行和心理状态进行了一种确定无疑的分析描述。就在读者的艺术想象力差不多已经完全沉浸入故事情境中的时候,秦巴子又以这种方式把读者一下子从故事情境中抽离出来。然后,他不无狡黠地告诉读者,也许“这只是作者我的视角,我的观看,我的想法”而已。既然出现在“我”的想象视野中的康美丽是如此一种情形,那么,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如果置换一个观看主体,他所想象描述出来的康美丽,恐怕就会全然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景致了。就我的感觉而言,秦巴子的这种元叙事,一方面充分地表达了作家对于笔端人物的尊重,人物自身可以有自己的别一种意志,叙述者所说出的,只是人物意志的可能性之一种而已。另一方面,依凭着如此一种艺术处理方式,秦巴子也向所有的阅读者打开了自己的小说文本,并使《身体课》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种现代意义上具有强烈召唤性的开放性文本。与此同时,秦巴子的这段元叙事,还在有意无意之间揭示出了一种小说写作的奥秘。那就是,作为小说的作者,他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要对读者起到一定的诱导作用。他一定得设法让自己的小说语言具有某种神奇的魔力,只有这样,才能够很好地完成此种诱导作用。而且,越是阅读经验丰富的人,就越是能够体会到,凡是优秀的小说作品,作者的这种诱导作用就越是发挥得酣畅淋漓。我们平时谈到小说创作时,总是强调好的小说一定得具备充分的艺术说服力。其实,秦巴子在这里所强调的诱导作用,也可以被看作是艺术说服力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如果我们把秦巴子这里的元叙事,与他在小说结尾处的另外一段元叙事结合起来,就更能够体会到作者诱导力的重要性了。“我之所以不厌其详地写出陶纯塑造他心中美神的过程,是为了让读到这些文字的人相信,这一切其实都是出自我的想象,我并不是陶纯工作现场的一个旁观者。但是小说作者凭什么获得这种全知全能的视角并且让人们相信他所说的都是事实他的人物确实存在呢?理由其实很简单,因为人们有阅读需要、并且愿意相信。这其中的关键之处在于小说作者与他的人物能否达成一种共谋,也就是说它们之间应该具有一种看上去不是那么愚蠢的逻辑性,只要魔术师的把戏不能被轻易地拆穿,魔术就可以不断地上演。当这逻辑性与生活暗合,那就会创造出真实,而当这逻辑性与生活背离,其结果就是传奇。但无论是真实还是传奇,都是写作者与他的人物以及阅读者生活经验和心灵愿望共谋的结果。”当秦巴子反复强调小说写作其实是“写作者与他的人物以及阅读者生活经验和心灵愿望共谋的结果”的时候,一种元叙事的味道就表现得十分明显了。
在某种意义上,秦巴子的这种说法,是暗合于艾布拉姆斯“文学四元素”理论的。美国著名文艺理论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③中提出了“文学活动四要素”的著名观点:“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素,几乎所有力求周密的理论总会在大体上对这四个要素加以区辨,使人一目了然。第一个要素是作品,即艺术产品本身。由于作品是人为的产品,所以第二个共同要素便是生产者,即艺术家。第三,一般认为作品总得有一个直接或间接地导源于现实事物的主题——总会涉及、表现、反映某种客观状态或者与此有关的东西。这第三个要素便可以认为是由人物和行动、思想和情感、物质和事件或者超越感觉的本质所构成,常常用‘自然’这个通用词来表示,我们却不妨换用一个含义更广的中性词——世界。最后一个要素是欣赏者,即听众、观众、读者。作品为他们而写,或至少会引起他们的关注。”秦巴子的说法,很显然与艾布拉姆斯四要素中除第三个文学要素之外的其他要素存在着密切关系。
元叙事手段的充分运用,再一次说明着秦巴子《身体课》具有强烈的“现代”意味。作为一个原创性色彩鲜明的“现代”小说文本,《身体课》一大突出的特征,就是紧紧地抓住身体,通过对于人物身体感觉的细致分析,进而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相当具有说服力地揭示了人物形象的内在精神奥秘。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康美丽与林茵这两位不同时代的女性身上。
先来看康美丽。在某种意义上说,康美丽确实是生活在当下时代里的一个幸福女人。从生活看,拥有一个和谐幸福的三口之家,既有身为企业家、时代成功人士的丈夫林解放(虽然林解放在外边有两个情人,但很显然,康美丽自己并不特别在意这一点),也有身为报社记者的女儿林茵。从工作看,她自己虽然也曾经一度被迫下岗,但由于有丈夫林解放的努力,衣食无忧的她又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一名图书管理员。照常理说,既然有如此一个也还称得上是和和美美的家庭,有着自己满意的工作,更何况,与丈夫之间也并没有发生什么过不去的尖锐冲突,甚至于,他们之间都没有红脸吵架,那么,康美丽就无论如何都不应该主动提出要和丈夫林解放离婚。我想,一般人们对于康美丽离婚行为的无法理解,多少类似于许多年之前,中国的普通观众无法理解电视剧版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的离婚举动。世俗的人们根本无法理解,既然日常家庭生活已经这么幸福了,安娜为什么还非得要离开自己的丈夫呢?在他们看来,安娜很傻,安娜是自己在往火坑里跳。他们根本就不可能理解安娜对于精神世界的高度追求。康美丽的情况同样如此。既然家庭生活与日常工作都不存在问题,那么,这康美丽离的究竟是哪门子婚哪?!
按照小说里的交待,康美丽的离婚行为,其实和她的身体感觉,存在着相当直接的关系。在康美丽的一生中,她的身体只达到过两次性高潮。第一次是“文革”期间,是在康美丽的青年时期。“康美丽整个一生的苏醒,都源于他的一瞥中的一丝笑意。那仿佛是嘲弄的笑意,强化了她身体当时的冲动,朦朦胧胧的混乱之中,她有一种被照亮,被开启,被唤醒的快感。那快感,不仅是心理的,更是一种生理的快感。几十年之后,当她终止了和男人的性亲近,回味起来,她觉得比她一生中任何一次做爱时的性高潮都要来得强烈。在那一瞥之下的快感的泛起中,她有点晕眩,她感到身体绵软,缓缓地像一块巨大的山体坍塌着,但那是一种快乐的坍塌,她的眼前一片桃花,香气灿烂。后来,她的一生中,都在试图重寻这种感觉,她想在丈夫身上把那种快感找回来,但她一生都没有再达到过那种美妙的高潮。”大约真的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虽然康美丽与雕塑家陶纯只是萍水相逢,虽然他们之间一个是批斗者另一个是被批斗者,但令人备感神奇的却是,只是陶纯的一个眼神,就能够使少女康美丽达到了其平生的第一次性高潮。然后,就是康美丽与丈夫林解放长达三十多年的婚姻。奇怪的是,在这漫长的婚姻过程中,康美丽居然再也没有形成过那样的性高潮。她第二次性高潮的出现,居然还是与雕塑家陶纯有关,只不过,这一次,康美丽面对着的是陶纯以康美丽自己为原型创作出来的一个人体雕塑作品。“康美丽看到那雕像的时候,有一瞬间的晕眩……她定定地站在那里,看着自己的雕像,她想象着一个男人的手是如何塑造面前的这个身体的。她的身体,在那个男人的手里,从一堆泥经过他的反复拿捏渐渐地变化成型,她甚至能感觉到那只手从她的身体上经过,他摸过了她身体的每一个地方,包括乳房和私处。这样想的时候,她的身体像真的被那男人摸着似的已经有感觉,心里痒痒地起了变化,她觉得乳房在胀大,下身隐隐地在抽动,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在冲撞着自己,她下意识地收缩身体,但是抑制不住的久违的快感还是在身体里泛滥起来……”
可以说,康美丽的身体所经历的这两次奇特的性高潮,对于她的人生选择产生着根本性的影响。如果说,在女儿林茵的报纸上看到自我雕像的照片,最早促使康美丽的心态发生某种微妙的倾斜变化,使她情不自禁地回想起“文革”中青年时期一种独特的身体性高潮经验的话,那么,发现丈夫林解放居然是雕塑家陶纯的亲生儿子这一事实,就使得康美丽再也无法容忍与丈夫之间的夫妻关系了。假若从一种象征的意义上说,我更愿意把康美丽的这种异常行为,看作是一种对于本真自我的寻找和回归。而这,事实上也就意味着虽然康美丽与丈夫林解放看似美满幸福地生活了三十多年,但严格地说起来,康美丽的这三十多年,其实是失去了自我、长期被异化着的三十多年。然而,令人称奇的是,康美丽的这种精神觉醒,居然是由她的身体感觉来加以唤醒的。一般意义上,我们总是把身体与精神理解为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但秦巴子的小说叙事实践却告诉我们,这样的一种观念或许是有问题的。就《身体课》这部长篇小说所具体描述的情况而言,人的精神世界和人的肉身世界,实际上往往是以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方式互相紧密地缠绕在一起的。秦巴子之所以要把小说命名为“身体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或许正在于此。就比如康美丽,她的离婚行为,当然应该被看作是一种精神觉醒行为,但这种精神觉醒行为的缘起,却又分明与康美丽身体感觉上的性高潮存在着直接的关系。然而,如果你只是把康美丽的行为看作是一种身体行为,却也明显是不合适的,因为其中的精神意味实在是不容忽视的。从这个层面看来,断言秦巴子的这一部《身体课》通过身体感觉的分析而内在地切入到了人物精神世界的微妙之处,当然就是一种无法被否认的存在事实。
同样来自于身体深处的困惑,自然也突出地表现在林茵这位女性形象身上。虽然说与母亲康美丽相比,林茵无论是就思想观念而言,还是就行为方式来说,都堪称新时代的女性,但她却一样面临着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困境。当然,林茵的困境,主要体现在她和诗人冯六六之间的复杂纠葛上。虽然说已经成婚的诗人冯六六不肯为了林茵而离婚,但只有在冯六六那里才能够得到身体的激情高峰体验的林茵,却一直无法自持地疯狂迷恋着冯六六的身体。“林茵曾经在这声音里挣扎过多次,她问自己:‘爱他吗?’然后自己回答:‘已经不爱了。’那为什么要跟他走?为什么还要和他做爱呢?她回答不了,于是又反问,爱又是什么呢?在他的召唤声中不能自持地想要把身体交给他,是不是爱?或者只是性?她是喜欢陈青的,但她极少有和他做爱的想法;她有时候很讨厌冯六六,但却愿意在他的怀抱里快活地呻吟……林茵的挣扎没有结果,当冯六六说‘我想你了’的时候,总是乖乖地就跟着他走了。”为此,林茵甚至于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性解放者。然而,发生在海南岛上那次失败的一夜情,却明确地告诉林茵,让她迷恋不已的实际上只有冯六六一人的身体而已。那么,这样的一种感觉与行为是道德的么?林茵在内心深处常常这样扪心自问:“她相信自己的身体不会欺骗自己,和冯六六做爱时的美好是其他人所无法比拟的。尽管她曾经怀疑自己是不是过于贪恋肉欲,但她很快就否定了,她为自己找到了另外的理由,那就是她的内心里仍然存留着对冯六六的爱情,在海南岛那次非常糟糕的一夜情,就是一种反证,仅仅只有英俊的男性身体并不足以唤起并获得性的美妙。而她和陈青的关系则是另一种反证,没有爱的激情的平平淡淡的所谓日子,同样也不会获得性的美妙。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林茵以自己的身体感受做了验证。于是,蔑视既有的虚伪而又漏洞百出的道德规范,而只以爱与人性为最真实坚定的理由,就成了林茵内心里的性道德尺度。在她这里。没有所谓不伦,只有不爱。只要有爱存在,那就是最道德的性关系。”实际上,正因为既有过海南岛那位一夜情的男士,也有过实在产生不了什么感觉的陈青,来作为林茵进行情感、人生选择的重要参照系,所以,她最后发出的希望冯六六离婚与自己结合的要求,就是顺理成章的。林茵如此一种重要的情感与人生选择,很显然,既是一种身体强烈召唤的结果,也带有着突出的精神觉醒意味。
需要指出的是,《身体课》中的康美丽母女,虽然在身体感觉的强烈召唤之下,都做出了自己明显迥异于常人的情感与人生选择,但真正的问题还在于,人物这样的选择究竟是否正确?这样的选择带给人物的果真就是一种幸福的生活么?秦巴子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并没有轻易地给出一种必然的承诺。比如康美丽,虽然她执意离婚,执意离开了丈夫林解放,但当她真的如愿以偿地和自己的雕像共处一室的时候,心里产生的居然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孤独与恐惧的感觉。作家的这种描写,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对于她坚定不移的离异行为的一种解构反讽效果。到了小说的结尾处,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站在了她的门口。虽然按照小说的暗示,这位老人似乎就是雕塑家陶纯,但来者果然是陶纯么?如果是陶纯的话,他的出现能够给康美丽带来什么呢?会是一种人生幸福的感觉么?康美丽会遭逢其人生中的第三次性高潮么?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未知数,秦巴子并没有给出哪怕是一点暗示性的交代。再比如林茵,在经历了父母的离异,经历了家庭的剧烈变故之后,突然意识到了家庭港湾的重要性,所以,出人意外地向诗人冯六六提出了自己需要一个家庭的要求:“‘你会娶我吗?你愿意为了我而离婚吗?’她偎在他的怀里,几年前的问话,像是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而冯六六感觉如同电击,他扳过她的脸表情复杂地看着他:‘我没听错吧?你说什么?’‘我说你愿意离了婚娶我吗?’冯六六可能是觉得太突然了,也许是以为她在开玩笑。他直视着她的眼睛:‘如果你是认真的,那需要给我一些时间。’这一次,他还会像几年前那样边打边退然后再次逃跑吗?”确实,面对着林茵提出的婚姻要求,冯六六到底有没有勇气满足她呢?他真的会再一次逃跑吗?对于这一点,秦巴子同样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其实,并不是秦巴子不愿意给出明确的答案,关键的问题在于生活本身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无解的。以如此一种方式有力地表现出康美丽与林茵两代女性身体和精神的迷惘、茫然状态,所充分体现出的,恐怕正是作家秦巴子的思想艺术智慧。很显然,从小说艺术手法的层面上说,秦巴子所采用的就是一种开放性的小说结尾方式。而这种开放性的结尾方式,往往也正是现代小说一向所惯用的。
实际上,并不仅仅是康美丽母女,在《身体课》中,作家对于诸如冯六六、林解放等几位人物形象,也都进行过相应精彩的关于身体与精神的分析性描写,只不过由于篇幅所限,我们无法一一加以展开罢了。但有一点必须提及的却是,即使是在如此一部实验性色彩非常鲜明的“现代”意味特别强烈的长篇小说中,秦巴子也难能可贵地做到了对于笼罩于人物之上的某种神秘命运感的传达。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如下一段叙事话语中。“但是生活就是这样,一些秘密和一连串的偶然,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当其中的某一块因为某种偶然被推倒,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建筑工地上的发现是一个偶然,而对那个发现的报道由报社四个文化记者之一的林茵去做也是一种偶然,报纸带回家被康美丽偶然间看到,触发了多年前的一个偶然,康美丽随高年级学生去乡下找陶纯是一个偶然,而陶纯发现康美丽的惊人之美也是一个偶然,但当这些偶然首尾相连地构成一个生活链条,就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必然结果:康美丽和林解放离婚了。这个离婚的事情被林茵偶然发现,则成了下一个偶然序列的一个起点。”事实上,作家对于命运感的参悟,不仅表现在这一段叙事话语之中,而且更是点点滴滴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在了整个小说文本的字里行间。人的生命历程中,可以说处处都存在着偶然,而所谓的命运,其实往往就是生命中的一连串偶然连接在一起之后所形成的一种逻辑必然。在我看来,大凡优秀的长篇小说作家,便都应该是人类某种神秘命运的领悟与参透者。只有通过故事的叙述,成功地把这种命运感传达给读者的长篇小说作家,方才算得上写出了真正杰出的长篇小说文本。依照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秦巴子的这部长篇小说,则《身体课》自然是当之无愧的。
更进一步地说,作为长篇小说的《身体课》固然离不开人物和故事,但是,相比较而言,对于如此一部原创性色彩特别鲜明的作品来说,小说真正的主人公,或许既不是康美丽,也不是林茵、林解放,而是身体,是小说中所有出场人物的身体。读完全书,掩卷沉思,便不难体会到,真正占据了小说文本中心地位的,实际上正是人的“身体”。即使仅仅从这一点上来说,秦巴子《身体课》的原创性,也已经是十分显豁了。我想,除了“身体课”之外,作家大约再也无法找到比这更合适恰当的小说命名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