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老屋
二 元
永远的老屋
二 元
这将是我最后一次看到老屋,所以我必须赶回故乡。
从记事起,家里并不富裕,但是在勤劳的父母经营下,日子倒也过得有滋有味。童年的我从不觉得自己的家有什么不好之处,相反总是觉得自己的屋是村里面最好的。相比宽敞的大房子,屋子的空间是有些狭小,但是屋里墙上装裱着我喜欢的各种宣传画和报纸,我的灵魂经常在那些图画和文字里游弋,所以我并没有感觉到空间上的压抑;相比安装着玻璃的明亮窗子,我们那糊着麻纸的窗户显然有些落后,但是我更喜欢自家窗户上的精美花纹和鲜艳的红窗花;屋里虽然没有从城里买回来的时兴家具,但是还有什么能比那热炕头更加让人留恋呢?父亲总是把窑面拾掇得平整光洁,让人不忍心涂抹。我习惯仰望着方正的连砖上那些瓦片发呆,寻思着乘父亲哪天不在家的时候爬到那高高的屋顶上去!
我努力使自己专心开车,可是眼前还是浮现出了记忆中的那些画面。
上次像往常一样,经过长途劳顿才回到久别的故乡。穿过熟悉的小巷,映入眼帘的却不是温馨十足的梦中家园,让我颇为震惊的是不知何时窑面的泥坯脱落掉一大块,电线也被砸断了。老屋就在眼前,可是迈进庭院的脚却无法走进屋门。一家人沉默不语,赶紧找来铁锨和扫把,马上投入到清理这突入袭来之物的忙碌当中。若不是亲眼所见,我绝不会相信老屋已经如此破败不堪。在我的印象中,老屋总是坚固而又华美,就像心目中的父亲总是那样矫健精神,哪知蓦然回首,已是白发苍苍、举步维艰。好在天真活泼的儿子在小院里欢快得跑来跑去,才使周围的空气没有接近凝结。
从那一刻起,家人一致认为老屋不行了,但究竟是翻新还是重建仍是个问题。
当天晚上,父亲讲起爷爷当年修建老屋的往事。在那年月,天气异常干旱,村里严重缺水,但是更为可怜的是取水的工具只有那笨重的木桶。从远处挑一担水回来压得肩膀生疼,而水漏得只剩半桶了,所以老屋的地基根本没有做实。从这个角度讲,长远看来,似乎没有翻修的必要了。
汽车在黑色的高原上飞驰,风雨无阻。在孩子几次睡着又醒来后,我们终于再次回到了故乡。
夜色苍茫,老屋依旧守护着院落。
第二天早上我还在梦中,就被屋外叽叽喳喳的鸟儿吵醒,原来太阳已经老高了,父母早已起来开始做饭。睁开眼,发现窑洞的背墙已经裂缝,而且略有错位的样子。披衣走进院子,眼前的老屋愈加沧桑。窑面的裂纹和褶皱比之前更多了;窑檐上的连砖早已经没有了棱角;两只猫头鹰安详地住在屋檐下,正奇怪地打量着来客,仿佛它们才是真正的主人;瓦片被风化得掉渣,风起欲落;屋顶上的小草再次探出了脑袋,几朵野花开得正艳。唉,这就是我可爱的老屋呵,怎么不是我记忆中的模样啦?!
就是眼前的这几间老屋里,住过爷爷奶奶那一辈人,住过父亲母亲这一辈人,也住过我们这一辈人,还有儿子他们这一辈人——经常不时回来小住几天。修建得并不坚固的老屋能够经挺立到今天,实在是一个奇迹!
记得有一年,家里依靠卖烟叶获得一笔钱,母亲建议给屋子箍一层砖面子,既好看或许还坚实呢,我们也觉得母亲的主意有些道理,不料却被父亲拒绝了。父亲说屋子结实不结实,决定于修建时候的施工情况,并不在于有那一层好看的“鸡蛋壳”,只要平时注意及时看护,屋顶不漏水,地基不湿水,再过二十年也不成问题,把钱用到娃娃们念书上才是正事。
从那以后,我才注意到,每次天阴下雨前后,父亲总是在屋子前后忙来忙去,或者除掉杂草疏通水渠,或者检查有无老鼠洞穴以防钻水,或者看看屋子背墙有没有意外淋湿。即便是后来帮我们照看小孩的日子里,每过一段时间,父亲总是不忘记回故乡看看。事实证明,我们可爱的老屋足足挺过了三十年,即便村里某些拥有美丽“鸡蛋壳”的屋子后来都已坍塌,可是我们可爱的老屋仍然安然无恙!现在想来,那是多亏了父亲默默地坚守和操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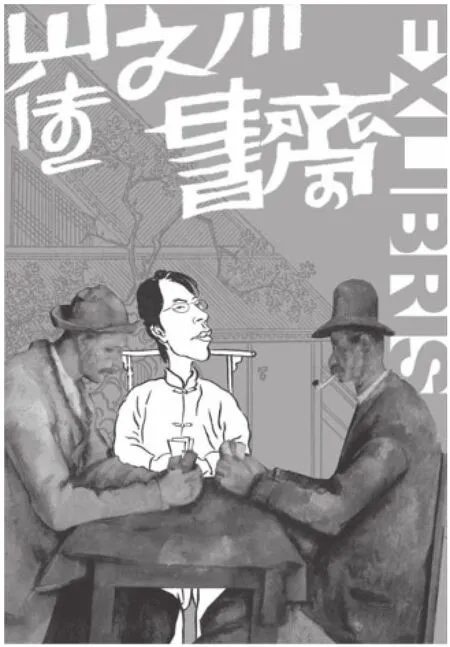
崔文川 藏书票
老屋的生命即将走向终结,于是我们决定在原址上新建几间房子。听到这个消息后,好心的乡亲们多次劝说我们。他们认为社会发展了,人们都往城里赶,村里住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再说我们都生活在城里,实在没有必要花钱在村里修地方。父亲仍然坚持着自己的态度:城里的生活不属于自己,只有在村里的日子才是最舒坦的。我的想法与父亲不尽相同,但是态度一致。恰逢五一劳动节放假,于是我们匆忙回到故乡,做些准备工作。
父母和我腾开了老房子,然后开始将老屋里的东西搬进房子。
已经习惯了或者坐在办公室里电脑前、或者蜗在水泥格子楼房里、或者卷在人来人往的大街小巷里,突然有一天在自家的老院里抱起那些尘封已久的坛坛罐罐走出走里,难免有些兴奋,大有穿越时光之感。父亲说那张陈旧的八仙桌虽不起眼,可就是家里祖辈用来看书学习的;打开油漆花色精美的柜子,竟然还有母亲为我们做的很多双布鞋没有穿;不时碰到我儿时玩过的东西,轻轻触摸一下,仿佛任何的遥远就在昨天。
看见我们忙忙碌碌地搬着东西,儿子也跟着帮忙拿一些小的物件,乐在其中。儿子今年才六岁,但是每逢假日,必然粘着爷爷回到老家。虽然不是生在此地,也不长在此地,但就是喜欢躺在老屋里的热炕上,喜欢庭院里的架子车,喜欢村庄里的那棵老槐树。
看着老屋被逐渐掏空,我甚至想象着老屋被拆倒的那一瞬间,这是我多么地不愿看到,但是又无法阻挡。毕竟拆掉腐朽,才能建起大厦。
正在忙碌间,突然有客人来院子探望,原来是从河南远道而来的叔叔们专程看望他们的第二故乡。五十多年前,他们跟随父辈逃荒来到这个陌生的村庄,是我善良的祖辈接纳了这些衣衫褴褛的外乡人。听父亲说,他们当时选择落脚于我们家户后,生活中聪明又能干,后来和他年龄相仿的兄弟几个都考取了学堂。如今个个事业有成,有的已是某学院院长,有的是某公司主管。是故穷不遗传,更不扎根,一个人也许出身并不华贵,但是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同样可以活得有尊严,活得更为精彩。
在故乡的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假期已完,我不得不告别了故乡,彻底告别了我的老屋,踏上返程。我深信,不久老屋将被更加坚固的平房所取代,而那些陈旧的物什,将毫无疑问的被再次搬进新房,继续传承着老屋的记忆和精神。
◎二元,本名崔元成,自号莫湾居士,80年代生于陕北延长,先后在各级报刊发表作品数十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