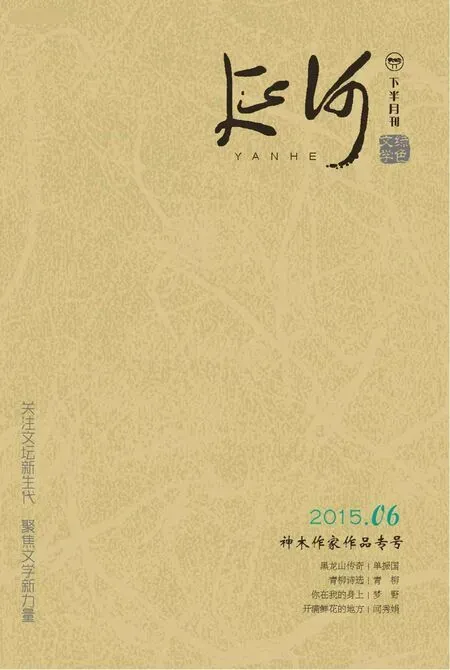我和大羊
凯 拓
我和大羊
凯 拓
那年深秋收获完地里的庄稼,我赶着大青骡去城西沟的一家煤矿盘煤。我的身体一直不好,又教过几年书,矿长就安排我在井下拉块炭。大炭拉完以后为了及时清理掌子面,不耽误再次掘进,矿长就给我派了个耙块炭的。这个耙块炭的不是别人,正是我后来的好朋友大羊。
大羊是煤矿东边柳树峁人。三十多岁的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许多。个子不算高但壮实,厚厚的嘴唇小而无神的眼睛,长得像我们村的灰三汉荣喜一样憨里憨气。他第一次给我的印象就是个老实人,出门在外能和这种人一起干活肯定吃不了亏。
耙块炭和拉块炭一样,是一种极没出息的营生。比起拉大炭的,拉块炭的工资也相应的比较低一些。耙一吨块炭才挣六毛钱,拉一吨也不过才五块钱。如果我每天能拉十吨块炭,那大羊每天只能挣六块钱。如果我每天拉不了十吨,他连六块钱也挣不下。因为挣钱少,所以他早晚在家里吃饭。晌午他就从那个黄色的挂包里掏出玉米面窝头,就着伙房里的开水咽下去。我从没见他抽纸烟,而是躲在一边抽水烟。他对煤矿上干活的人无不钦佩,尤其敬佩的是我们这些赶车拿大钱的人。
自从大羊在井下耙块炭以后,有人时不时地给他抽纸烟,有人亲切地喊他大羊哥。晌午看见他啃涩酸干硬的窝头,就给他塞半块白馍吃。而对他好的这个人不是别人,而是拉他把块炭耙成堆的我。
在骡车队里,我算是低能儿,低能儿才去拉块炭的。你别小看我这个拉块炭的,拉块炭也有拉块炭的好处。一来不用去抱二三百斤重的大炭,二来也免得被大炭碰破手脚。假如没有拉块炭这个营生而我还想下井的话,那也只能和大羊哥一样扛着耙子下井耙块炭了。

神木剪纸 刘凤棠《三羊开泰》
起初的几天我的精力和大青骡一样充沛,一小时准往外能拉一趟。还没等大羊哥把块炭耙成堆我就直入巷道,长长地喊一声:“大羊哥——你在哪里——”
“我在这呢——”
听见是我的声音,大羊哥在那边巷道拉长声音回应。而这时的大青骡已经知道大羊哥的具体位置了,就打着喷嚏扬着头不多时就走在大羊哥身边了。大羊哥呢,他摸摸大青骡的头亲昵地说:“哎呀,这真是一头好骡子呀!”
我不为骄傲地说:“就是嘛,我的骡子能不好吗?”
在盘煤的十几个骡子里,大青骡个儿最大膘也最好跑得也最欢,我自然为自己拥有这么一头好骡子而自豪。可是后来随着日复一日地下井盘煤,我的体力随着饭量的减少一天天地下降。黑夜腰酸腿疼难以入睡,第二天起来总是无精打采的。下井前背着矿灯拉着大青骡到了黑洞洞的井口,有一种仿佛就要进地狱的感觉。到了井下装块炭时拿着大锨觉得那么沉,而看见那并没多高的车箱简直比货车或火车皮还能盛货——那些日子我确实是早鸡了,我的好脾气也不知不觉变坏了。可是性急的大青骡越发地骠肥体壮精神气十足,还没等我装满车箱它就急着要走了。为此它受了我不少的辱骂和虐待:“你这个不识好歹的畜生,我让你少跑几回还不行,你现在是扑死去呢?”
看见我没好气地用缰绳刷打大青骡的脑袋,大羊哥出来替大青骡打抱不平了。他生气地瞪着我说:“你看你这人也是的,到底是骡子有过(错)呢还是赶车的人有过呢?”
看见我理屈词穷不说话了,大羊哥又缓和了口气说:“唉,可惜了这么一头好骡子让你使唤,我要是有这么一头好骡子一天准能拉十几吨块炭。”
我揩着额头的汗,气恼地对他说:“你嫌我铲得慢,那你就不能替我铲一会儿了?这些天每天下井,我确实是累的管够呛了。”
“我知道你从来没盘过炭,这几天肯定是干草鸡了。你让我替你铲,那我就铲一会儿吧,有啥大不了的!”
只见大羊哥从我手里夺过大锨,然后唰唰唰地铲起来。没过多久,那车箱里的煤块就高高地冒了起来。我欣喜地说:“大羊哥,你这么能干干脆就买头骡子也赶车吧。”
大羊哥说:“唉,袖筒里伸不出脚,没钱买呀。别说了,你赶紧走吧,快点走看今天儿能不能拉十吨。”
挨了打的大青骡看着我不知该不该走,我高兴地喊一声“得儿球”,大青骡听见我的喊声像听到命令一样撒开四蹄就上路了。矿灯将前面狭窄的巷道照亮,左拐、右拐、再左拐、再右拐,又爬一道缓坡就出了井口。出了井口,再走不远就到了炭场。然后过磅、卸炭、再掉头,大青骡一溜烟进了井口下了那道缓坡,西拐、北拐、再西拐、再北拐。这时不知道大羊哥正在哪个掌子面耙着呢,我又长长地喊一声:“大羊哥——你在哪里——”
大羊哥在另外一个掌子面应道:“我在这呢——”
听见大羊哥熟悉的声音,大青骡就直直地走过去。那天拉最后一车的时候,我出了井口过了磅才知道拉了十吨还多呢。由于疲劳我笑不出来,但心里还是高兴的。心想,大羊哥天天能这么帮那我才好呢。
第二天我看见,大羊哥果然从家里拿来一张小锨。和这么憨厚的人一起干活吃不了亏的,但我除内心高兴什么也没说。可是每次装车不用我说,大羊哥总拿大锨让我拿小锨。两个人很快将车装满了,大青骡很懂事似的扬着尾巴撒开四蹄越走越精神。
在长期的共同劳动中,我知道大羊哥遭遇不好,人又善良,在煤矿无论干什么活他总受人排挤。我多么想让他买一头骡子赶辆车盘煤,美美地挣上一笔钱,再娶个媳妇成个家,那样矿上的人就不敢小瞧他了。可是当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大羊哥时,大羊哥叹息着说:“唉,我爸刚没了还不到半年,给我弟弟娶媳妇欠下的债还没还清,熬一年下来也只能还上贷款的利息。”
我听了无奈地叹息一声,对他的遭遇表示深深地同情。
好不容易盼到月底,大羊哥仅仅领了不到三百块钱。可是他握着钱高兴地说:“又能还贷款利息了,还了贷款利息这个月还有二十多块钱零花呢。”
一个月二十块钱能买什么,听了这话我就偷偷地给他兜里塞了一百块钱。我以为有这一百块钱,他就可以买纸烟什么的了。可是第二天在井下,他又将钱塞到我兜里。他说:“我是夜黑回家才发现的。我以为是会计多给我数了一张呢,后来才想到是你给我塞进来的。哎呀,我家里不缺吃不缺穿的,即使没一分钱也能过个两三个月的,所以这钱我坚决不能要。”
我诚恳地说:“大羊哥,那你得抽烟你得零花吧?大羊哥,要不是你帮我这个月我也领不到这么多钱。就这么熬下去,说不定我坚持不下来回了家呢。大羊哥,这点钱你别嫌少,快拿着吧。”
我把钱又塞进大羊哥的衣兜里去,可大羊哥把钱掏出来硬塞给我,有点生气地说:“你出门在外揽工受苦是为了养家糊口,我守家在地怎么好意思花你的钱呢?况且这个月和你一起干,我比往常领的钱还多好多呢。”
几次三番说服不了大羊哥,我只好将钱收起。收工以后我买了袋面粉送到他家,顺便给他五十多的老母亲买了两盒糕点。因为自己的儿子结交了我这么个好朋友,老人高兴得合不拢嘴。她咀嚼着糕点说:“这东西才软绵顺口呢!”
我说:“大娘,软绵顺口你就多吃些,吃完以后我再给你买!”
大羊哥看着我,嗨嗨嗨笑着说不来什么。
腊月中旬煤矿放假,我并没有急着回家。应大羊哥的邀请,我在他家留了一夜,弟兄俩喝了个四脚朝天方才休息。第二天大羊哥将我送出村口,他指着村口狭窄的砭路说:“我们村也有煤呢,只是路不通。等这条路修通了我们村也开煤矿,到时候……”
我说:“到时候你们就是煤矿的主人,你就不愁没钱花也不愁娶不过媳妇了。”
大羊哥嗨嗨嗨笑着说:“到时候我就买头骡子,也赶车盘煤。”
我说:“要买就买像我这样的,能吃能跑还力气大。”
羊哥嗨嗨嗨笑着说:“到时候一定买你这样的。”
我走出好远好远他还向我挥着手说:“明年地里没开始干营生,你再来这里盘煤。正月二十煤矿开始干活,我还给你耙块炭。”
我也挥着手向他说:“大羊哥,我一定来!”
来年的正月二十,我又去那家煤矿盘煤。大青骡似乎也想念我的大羊哥了,不用吆喝不用赶它在平坦的柏油路上撒开四蹄跑着。
但是山梁上多了一座黄土坟茔,人世间却独独少了我的大羊哥。大羊哥的母亲像一个白痴,她坐在院子里的石头上泣不成声地告诉我:“正月里修路的时候,你大羊哥是被山上滚下来的石头砸伤的。在医院的时候,他还一个劲地念叨着你的名字,可惜当时村里人不知道你家住哪里。”
人生无常,一个美丽的设想就这么结束了。我陪老人掉泪时大青骡也站在一边,一副十分伤心的样子。太阳落山了,它不停地蹭着我的腿和臂,两只泪眼盯着我好像在说:“天黑了,咱明儿再来吧。”
我走过去摸摸大青骡的头,对它说:“咱明儿再走,今儿就在住这里吧。”
那天夜里我梦见大羊哥了,他买了骡子要赶车呢。他拉着骡子走在我面前,嗨嗨嗨笑着说:“你看,我的骡子像你的大青骡一样,也是这样的皮毛,也是一样的好饲养。最主要的是它和大青骡一样有力气,一样的能干活!”
看着大羊哥的大青骡我欣喜地不知说什么好。
◎凯拓,又名贺中学,1962年出生,神木县栏杆堡镇人。1979年高中毕业,1982年当兵,1884年复员,后在农村学校任教。在部队就开始文学创作,出版长篇小说《八月红》《红尘》《永远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