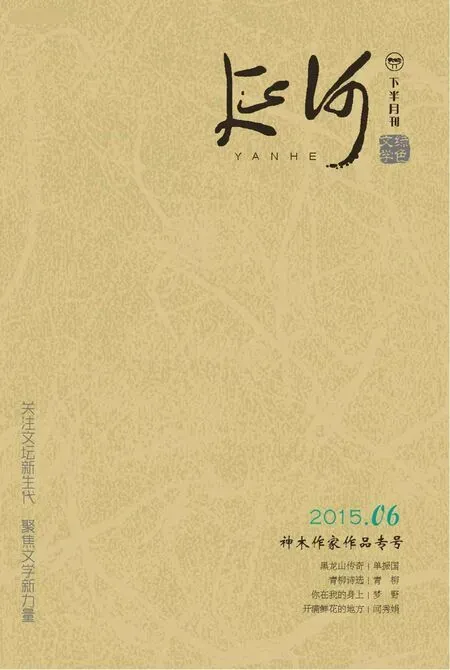我家的后园子(外一篇)
黄 浩
我家的后园子(外一篇)
黄 浩
我又溜回了老家的后园子。起风了,我听到金秋深处,花果敲打大地的声音。
老家的大院是典型的四合院,院子北面有一个后门连着园子,长着许多花果树。有桃树、梨树、桑树、核桃树,大人们叫它后园子,孩子们更喜欢叫它花果园。园子呈长方形,北依城墙,南靠大院的正房,东西两边砌了很高的墙,墙两边种着两排白杨树,俨然一个封闭的园子。像亚当、夏娃的那个伊甸园,总有人准备偷吃禁果。这是一个低于地面的园子,靠城墙有一个暗洞,把水引了进来,只要有土地、有水,有辛勤劳作的人,园子里就什么都可以长出来。
在我的记忆中,老家园子里的花果树已经有年岁了,他们茂盛宽大的枝叶将园子隐藏在浓荫之中。大院里的几个本家都在园子里分有一块蔬菜地,种着各种蔬菜。在那个饥饿的年代,园子里的蔬菜和花果成了我们整个家族的一种依靠和希望。因为这个园子,我们的大院在小镇很有名气,家族的每个人都为后园子而感到骄傲。那时候,常听爷爷讲后园子的故事。老爷将大院买来的时候就带着后园子。但只买大院主家不卖,老爷忍痛割爱又多给了8块大洋,才将园子盘下来。后来老爷带着三个儿子在后园子栽满了花果树,并将后园子的管理权交给了三爷爷和三奶奶。老爷给了我们这个家族遮风挡雨的房子,大院里共有房子24间,他的子孙平静地在这个大院里生活,更重要的是他给了子孙们这个后园子,给了我们四季飘香的果园,给了我们几代人快乐的童年。
当燕子衔着春泥飞来的时候,园子里就闻到花香了。不经意间,那棵高大的杏树挺立在蓝天里,淡粉色的花朵凸起在干枝间,一朵挨着一朵,一排排灿烂成一片,怒放在蓝天里。看杏花你得仰望,当园子里的花香渐渐变浓,桃花展开了笑脸,花期一期接着一期,次第开放,梨花、苹果花、枣花,争相卖弄风情。其实孩子们是最爱花,最懂花的人。地下看花是一种情趣,空中看花又是一种情趣。爬树是孩子们的强项,两手上倒,两脚上挪,身子往上跳跃,一会儿就爬在树上了。人钻花丛,脸耀花海,风吹花瓣,随风扑簌簌的起舞。开的最鲜艳的花,朵儿最大的花,长得最好看的,都逃不过小小采花人的眼睛。树上摘花枝时,就有花瓣迎着阳光飘下来,落在孩子们的身上、地上,就成了园子里的花毯。后来,孩子们手里就都拿着花枝,跑着、跳着、追着、笑着,于是简朴的家中,就看到插在瓶子里的杏花了。每每推开门,淡雅的杏花就扑面而来,像一盏盏点亮的灯,温暖着困难的日子。本家的几个孩子进园子,三奶奶从不过问,但邻居家的孩子那是不允许进后园子的,偷偷跑进园子的,小手就要遭罪了,所以巷里的孩子们提起三奶奶,没有一个不害怕的。
不知不觉炎热的夏天就走进园子。放学后,本家的几个孩子把书包一扔,钻进了后园子里不肯出来。母亲总是在饭熟后,一遍一遍喊着儿女们的名字,这熟悉的声音常常在园子里回响。每隔几天,三爷爷就会放水浇园子,那是我最喜欢看的一件事。清清的水流,碰到阳光一眨一眨的闪人的眼。我爷爷总是站在城墙上照水,生怕别人把水抢了去,嘴上嘟哝着什么,有时向园子里喊:“老三,浇完了没有?”于是园子里就传来:“还得一会儿。”的回声。水流就这样缓缓地流进园子里的蔬菜地,流进每一棵花果树里。微风送爽,斑驳的树叶总是翻翻身子,让你在瞬间看到,从树叶缝隙透进来的阳光。孩子们是园子里的主人,他们是最杰出的观察者。杏子这几天多大了,桃树结了多少颗桃子,桑葚啥时能吃,梨子今年大还是去年大,苹果树是不是长虫了,今年的枣子结得咋样,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夏天的下午,是园子里人最多的时刻,爷爷和三爷爷早就在园子里摆好了战场,楚河、汉界的拼杀,让两人经常面红耳赤。父亲和二叔、四叔闲聊着什么,妯娌们手里拿着针线活,轻声说着家长里短,孩子们围绕着大人们跑来跑去,园子里到处飘荡着欢乐的笑声。夜不知不觉地潜入园子,月影从山的背后升起来,恬静的月光钻进了枝叶间,落在地上形成交错的光影。此时,杏、梨、苹果、红枣正躺在树枝上吸收月光和水分的营养,个头渐长。夜深了,花果们拉着悄悄话,伴着蝉鸣和蝈蝈的叫声入眠。困了,困了,一个花果睡了,十个花果睡了,一排排地睡了,一棵树的花果们睡了,我仿佛听到花果们的打鼾声传来,此起彼伏。
农历五月是杏子黄熟的季节,高高的杏树上挂着无数颗黄灿灿的金子,孩子们总是仰望杏树,张开嘴看能不能掉下来。这时候,三奶奶就忙碌起来了。只要我们进园子她就跟了进来,生怕我们偷吃杏子。于是我们总是晚上溜进园子,拿一块小石头向杏树上一扔,就能落下许多黄橙橙的杏子,放进嘴里,一股新鲜的味涌来,像水里泡着白糖舌根带一点酸的味道。总是在吃饱后,再捡满两衣袋,悄悄地跑回家。第二天的早上,后园子里就能听到三奶奶的骂声了,她看到杏树下吃剩的杏骨了。杏子黄了,树上挂着一个个笑脸,随风在树叶间摇曳,墙外的邻居也馋了,总是有人拿起石头向杏树一扔,地下就落下一些杏子,于是三奶奶的骂声传来,飘过园子的上空。遇到星期天,三奶奶也有上街的时候,我们瞅准机会,一头钻进后园子手脚利索地爬上杏树,挑最黄、最熟的杏子吃,然后把杏骨装进衣袋里,而三奶奶回来没发现杏骨,向树上看了又看,总感觉杏子又少了,自己唠叨着不知是什么原因。
园子里花果的个头一天天变大,颜色渐渐变深,挂满了果实的枝条向下垂了下来,终于等到秋天换着各种花衣迈进了园子。红脸的苹果端庄地站在枝条上,仰望岁月之母,红彤彤的枣子上,趴着晶莹的露珠,在阳光下一闪一闪,那珠子上站着几千个太阳。黄橙橙的梨儿,饱满肥壮地挂在黄叶上,像一个个骄傲的公主。我依然记得紫格彩彩的桑葚,青格灿灿的桃子,绿格茵茵的核桃,红格艳艳的柿子,脆格生生的青黄瓜,它们都是孩子们的宝贝和理想。这个季节趁三奶奶不注意,孩子们就溜进园子,快速地爬上各种花果树尝鲜,三奶奶悄悄地就走进园子来了,我们宁神闭气趴在树干上隐蔽起来,这次三奶奶因为树叶阻挡没有发现我们。十月的花果树上,就能闻到一股甜甜的果香,各种香味都不一样,弥散在园子里。站在苹果树的枝条上,四周的苹果把我围了起来,红红的苹果摇曳着,我像一个果王,每一颗苹果都是一个红衣女子,有的唱着歌,有的跳着舞,有的拉着悄悄话,谈着恋爱。选择哪一颗摘,它们都红扑扑的露出笑脸,水灵灵的成为你的奴仆。苹果、红枣、梨儿、核桃刚刚向岁月举行了成年礼,春华秋实,它们即将成熟,完成一年一次的辉煌交替。从冬天孕育花蕾到春天花开,不是每一朵花都能成为果实,每朵花都要经风授粉。而在结果之前,陕北的沙尘爆就来了,吹走了许多花瓣,地上满满地落了一片,这些花就成不了果实。躲过了风,夜雨就开始敲打花了,于是又有一部分花落了下来,授过粉的花就结出了果实。这时候你要注意花果上的虫子了,只有躲过虫害,花果才能圆满成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自然界的生存法则,而我们人类又该遵循什么法则呢?

神木剪纸 武晓梅《团花》
又一次回到老家。站在老家的大院,一切都是陌生的。四合院的大门,所有的房子已经破烂不堪,本家的所有人都搬到城里,没有一个人肯留下来,照看祖上留下的产业,过一种宁静、平和的生活。分到四叔名下的房子卖了,二叔的也卖了,那么大的院子只有我们的一小部分,租房的都是陌生人。我沮丧地看着眼前的老家,那个带给我们家族快乐的后园子,虽然没卖出去,但园子里堆满了垃圾,由于无人照看,园子里的花果树全部枯死了,光秃秃的样子让人心疼。我知道那个园子,在我的生活中永远消失了。
我们走出了那个园子,那个幸福的园子。
一棵树
油松是自然界的长寿树种,属针叶常绿乔木,身材高大挺直,简约明快,气宇轩昂。它的树冠成塔形或卵圆形,如大地上种植的一把把绿伞。风儿摇动树冠,那高高的绿塔,仍然保持着向上飞翔的姿态。
广袤的黄土高原是油松生长的沃土。在陕北的野生油松种群中,有一棵旱源油松之王,树龄高达2500年,它真是一个长着,鹤发童颜,一个又一个长命百岁的轮回,让它成为圣者、智者。自然界授予它王位,那顶绿色的王冠,已经戴了好多年。一棵树,能活几千年,立在黄土里,特别醒目。在蓝与黄里,顶着一个庞大的伞盖,承载者几千年的身体,巍巍如大山,垂垂如高原的巨人,绿叶缤纷,松针盈盈,擎举在黄土沟壑间,遮天蔽日。一棵树,孑然一身,孤独挺拔,守候在旱源。方圆几百里,都是细软的黄土,相伴无松,贫瘠干旱,山峁梁涧,担当了悠悠的岁月。
古松高二十米,树宽需七、八个人才能抱住。主干通直,浑圆正壮,笔挺垂足,丰盈大地。皴裂的树皮,如青筋突起,呈褐色,结结巴巴,一高一低。在树沟间,一大片一大片凸起、凹下,如长在树杆上的千层鱼鳞。厚实的树杆,常有开割的裂口,流出粘稠的溶液,真是松脂如泪、油洒四方。白色溶液是古松的眼泪,红黄色的溶液是古松的血。而朴素的树纹,丝丝缕缕,成规则地布满树干,像古宅木雕的花纹,。若将古松树干横切成面,就可以看到一幅圆形地图。布满了树心、年轮、血管、筋脉,密密麻麻地构成一个延续生命的大系统。
一棵老松,日日与阳光相遇,吸金收银,满眼凝望都是跌碎的阳光,铺满了苍翠的王冠。起风了,畅通无阻的风,从四面八方劈向老松,庞大的树冠左右摇晃着,枝与叶紧紧地抱成一团,它们有强大的定力,在主干的支撑中,保持着一种平衡。一棵树响起松涛声,从一片叶子传到另一片叶子,从一根松针传到另一根松针,于是声音被无数根松针敲打着,如海面擂响的百面大鼓,面对狂风,老松毫无惧色。凉风习习,老松顶着巨大的压力,风雨雷电轮番上阵,都败下阵来,它是高原战斗的旗帜。一棵树,就是一尊神。二千多年守望着岁月,掀起满树挂着的红丝带,飘舞在高原,如歌如泣。敬畏千年古松,就是敬畏生命、敬畏自然。这颗巨大的绿伞,由长长的岁月撑起,几十根主干立在阳光下,壮硕地成长,蓝天是那样遥远,老枝与嫩枝,新枝与旧枝,枝桠交错,它们都是日日拔节,吐着新枝,缩短着天地间的距离。
老松庞大的树冠上,长满了青翠的叶子。叶子在旁枝、侧枝、新枝上长出。新枝是松树最柔软的枝条,有规则地长着一簇簇松叶随风摇曳,它是最年轻充满活力的一蔟。松树的叶子,总是以一簇簇的形式出现,每一簇有168条青色的针,沿着枝条一层一层布局,到枝顶有26层松针排列,一层一层守护着蓓蕾,指着阳光温暖的方向。每条松针都是都是10厘米,支出的二条嫩嫩的松针,都是9厘米,出奇的一样,像母亲生得双胞胎,无论个子、颜色、粗细、形态、神情都一模一样。松树是耐旱的树种叶子似针状,有利于储存水分,较少水分的蒸发。松树的叶子是松针,在冬日里,就有不少松针枯黄,成棕红色夹在绿叶间。坐在棕色绒毯的古松下,松针悄悄地滑落,像扑簌簌的松雨,不时松球就落了下来。树下铺满了棕色的松针,夹杂着数不清的球果,软绵绵的,足足有1米多深。
每年冬天,新枝的顶端,总能顶出几个蓓蕾,尖尖的、棕红的、带着毛毛的芒刺。如果打开花苞,就看到有一圈花瓣样的底座,绿绿的,这就是松花。挂在新枝上的蓓蕾,不是都能长成球果,只有经风授粉后,才能结出果。当年长成的球果颜色是棕红色,像一个圆球状的莲花,有11层花片,78个花瓣。每一个花瓣上都藏有两颗种子。当松球成熟开裂,借助风,球果的种子,就像一个个降落伞,从花瓣里钻出,随风飘到高原的各个角落。旧的球果是黑色的,老松的枝叶间,密密麻麻挂着数不清的球果,黑黑的一大片,如没有点亮的灯笼。无法说清二千多年的古松,能结多少球果,几百年、几千年的球果早已变成了黄土,也许几十年的球果还挂着。新生的枝叶间,总能看到棕红色的新球果,灿烂在松针间,与黑色的球果相对,格外醒目。
2500多年的一棵古松,可以想象它有多么发达的根系。它在厚软的黄土层里,360度方向自由地拓疆扩土。几亿条根,就有几亿条的路径,它在温暖的黄土里,游走、探路、伸展。在这漫长的征程中,自己也不知道走了多远,它只是日日延伸,上下左右,远近高低,年年掘进。这是一个庞大的家族,纵横交错的根系,串联起一个宏大的网,又稠又密,有的长达几十公里。它们在丰盈的土层里,不断寻找新的目标和方向。当长长的根遇到了含水层,它就如一根导管,将水分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古松的各个枝叶上,它们吸收着岩层的矿物质,吸收着土地的元素,滋养着这棵千年古松。
陕北的旱源起风了,形成一个巨大黄色的漩涡,它不断地在黄土上移动着,带着尘土和沙砾,扑向古松。一声巨响,钻天的古松倒下了,沉沉地倒在黄土里,断成了几十截,2000多年不屈的尊严,在倒下的那一刻,终被黄土掩埋。一个人活不过一棵树,一棵树活不过一把黄土。
◎黄浩,陕西省神木县人,现供职于神木县电视台。9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有近百篇(首)诗歌、散文在《散文选刊》《草原》《西部》等刊物发表,获2007年度《草原》文学奖,2007年度中国百篇散文奖。著有诗集《生命的庆典》《走进神木》,散文集《黄浩散文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