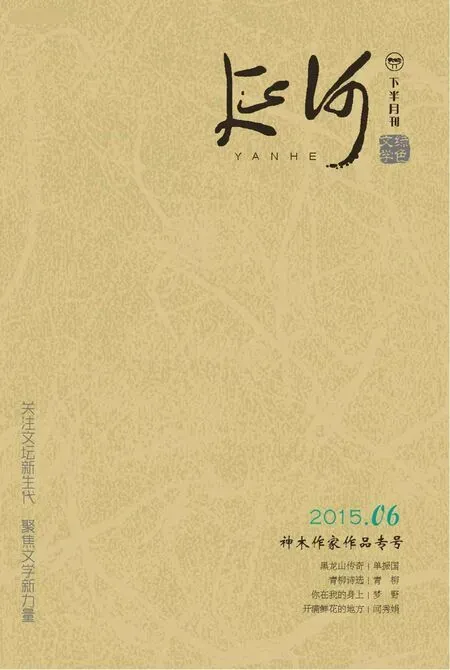隔世的疼痛(外一篇)
郝卡厚
隔世的疼痛(外一篇)
郝卡厚
冬至一过,天突然出奇的冷。在刺骨的寒风中,脸像刀子似的刮过,生疼生疼。疼痛中,不禁使我又想起了在天堂的母亲。
农历十一月二十日,是母亲的忌日。
时光飞逝,岁月无情。不经意间,母亲离开我整整两年了。在这700多天里,母亲曾十多次托梦给我,其音容笑貌一如在世:那个腰弯得很深,拄着拐杖、满头银丝的小脚老太太活灵活现地来到了我的面前。
多少次,我在梦中与母亲对话;多少次,我在梦中吃着母亲拿手的揪面片;多少次,我在梦中搀扶着母亲颤巍巍的身子向前挪动……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在人间,你在天堂;虽然隔世,母爱犹在。想你呀,我亲爱的母亲!
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没念一天书,不识一个字。但母亲又是一个极其坚强和伟大的女人。虽然身高只有一米五,虽然裹着一双奇小的秀脚。
由于家境贫寒,十二岁那年,母亲就过来给父亲做了童养媳。从此,母亲就成为了家里正儿八经的顶梁柱。下地劳作,打理家务,做饭洗锅,砍柴喂猪,缝补浆洗,一样少不了母亲。因为父亲一只眼睛有点残疾,只能干些重活粗活,所以家里门外的大多活儿只得靠母亲操持了。
在那个谁都知道的闹饥荒年月,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父亲饿得成天睡在炕上下不了地,甚至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母亲强打精神,每天起早贪黑到山上挖野菜、拔树皮、刨草根,实在撑不住倒在地里躺一会,回到家就想着法子、做出花样,哄着父亲和哥姐吃,硬是把一家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母亲的伟大之处还不止于此。说来不怕笑话,想起让人心疼。从十八岁生第一个孩子到五十岁的三十多年间,母亲先后生了十二个孩子。然而,也许是老天不保佑,更主要的是那个时候的医疗条件所限,十二个子女只留下我们姐弟三个。那些不在的孩子,最大的六岁,小的也有一两岁、几个月的。就在母亲五十岁那年,连她自己也没想到,我挣脱了母亲温暖舒适的怀抱,来到了这个世界。母亲常给我们讲,她那时生孩子,往往是临盆了,才从干活的地里往家里赶,生下孩子没几天,就要下地烧火做饭,甚至还要包着头巾到地里干活。为了保住那些孩子的性命,母亲和父亲不知到庙上求了多少次神、烧了多少次香、请了多少次神官巫婆。结果,头磕了、神敬了、香烧了、马下了、愿还了,孩子一个个去了。那对母亲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需要母亲多么坚强的意志呀!怪不得,我和姐姐的名字里都有一个“卡”(陕北方言:“抱”之意)字。原来,我们姐弟是各路神仙给抱来的。母亲,您可谓用心良苦。
我是母亲的老生儿(方言:老来得子),故母亲格外疼我。我生来被母亲宠爱着,所以嘴特别细,吃饭爱挑剔,常常是父母哥姐吃窝窝头,母亲给我坐一碗黄米粥,然后用黄油拌了我才吃;要么给我做一碗揪面片吃。当然,揪面片不可以天天吃,隔三差五就很不错了。
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我的家乡有蒸面人人(用白面捏成人、狗、羊、猪、鸡、鱼等形状,蒸熟,在大锅里烤干或晒干)的习俗,弄好后主要是分给小孩吃。每次我分得比姐姐和哥哥多,姐姐、哥哥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虽有看法,但没办法。我却引以自豪。就这还不算完,我常常是舍不得吃自己的,趁姐姐和哥哥不在时,偷吃他们的。为此,我也挨过揍。
我清楚地记得,我七岁了,上学了,但每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哭闹着要吃母亲的奶水。至于晚上,我则要噙着母亲的乳头进入梦乡。母亲吃的是粗茶淡饭,流出的是甘甜的乳汁。其实,那时的母亲已经没有多少乳汁了,可她还要忍着疼痛,任我不停地吮吸。现在想来,我是多么的自私和残忍。
母亲一生爱干净,长有一双巧手。虽是农村,喂着家禽,养着牲口,干农活的家什一样不少,可家里始终很利索,啥有啥的地方。那时家里贫穷,穿得衣服、鞋子、袜子虽补丁搭补丁,但干净整洁,每一块补丁都放得有板有眼,恰到好处。同龄的小伙伴们经常投以我们姐弟羡慕的目光。我们姐弟一直是穿着母亲一针针、一线线缝制的千层底布鞋走向成年的。至今,我仍保留着我三十岁生日时,母亲用半年时间给我纳的那双好看的绣花鞋垫。
立志参军报国,是我儿时就有的梦想。为此,我连续三年报名应征,前两次因年龄小没走成,直至第三年才梦想成真。我心里清楚,母亲根本就舍不得让我离开她。可农村艰苦的劳作,甚至连碗饱饭都吃不上,她老人家也只能忍痛放手了。
那年的冬天来得早。农历十月中旬,就落下了一场大雪。那天一大早,母亲就起来烧火做饭。饭桌上,母亲不停地给我夹菜,生怕路上饿着。可是,十多年来,连一趟远门都没出过的我,在将要别离疼我爱我母亲的时刻,我哪还有胃口!

神木剪纸 任粉翠《抓髻娃娃》
我要启程了,母亲蹒跚着身子来到我面前,用她枯瘦的双手抚抹着我的脸,发颤地对我说:“厚儿,去闯吧,好好听部队首长的话,可要出息呀!”好半天,母亲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愿松开。凝视着母亲历经六十八载风雨已是满面皱纹但仍然和蔼可亲的脸庞,似有万语千言倾诉,然嗓子眼发哽,最终一句话没说出口。
父亲在我参军的第二年就过世了。这么多年来,母亲一直是哥哥照顾着。作为母亲疼爱了一生的儿子,我只是每年回家休假时,买一些吃的给母亲。短暂的假期,又能尽多少做儿子的孝道?可每次回家,母亲总要给我做几顿我爱吃的饭菜;离家时,母亲总要拄着拐棍送我到村口。我一向心软,与母亲的一次次别离,都会泪水噙满双眼。我分明也看到母亲的泪眼啊!
天有不测风云。白发人送黑发人——人生之最大的不幸和痛苦给了我善良的母亲。三年前的初冬,一直在农村老家服侍母亲的我唯一的哥哥,因疏忽从我家大门楼子上摔了下来,虽经医护人员全力抢救,但最终还是没能留住他五十二岁的年轻生命。在料理哥哥后事的日子,母亲表现出难以言表的坚强,反复叮嘱我,一定要把哥哥的后事办妥。但没人的时候,母亲老泪纵横,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哥哥的名字。那几天,我发现母亲少有的几根黑发完全变白了。
人生自古谁无死。即使身体硬朗、从来没有毛病的母亲。她毕竟年过九旬了呀!就在哥哥走后的第二年,由于年岁已高,母亲走路时常常摔跤,其中一次摔倒后再没下过炕。半年多时间,一直由嫂子侍候,偶尔姐姐也来住上一段。可就在去世前的一个月,母亲突然不会说话了。见了我,只是张张嘴,发不出声音。我看到母亲很努力、很用劲、很着急,但就是说不出话来。抚慰我的双手更加有力。目睹母亲日益消瘦的面容,想着不久就要离我而去的情景,我的心情难过而沉重。只能比划着双手,尽最大可能与母亲交流,给母亲喂饭,洗脸,梳头,修剪指甲……
万没想到,那一次成为我与母亲的永诀。在离开家回到单位的十多天,我几乎每天都要打电话询问母亲的情况,得到的答复是暂时没事。可谁知道,那天早上一起来,就接到村里的一个侄子的电话,说我母亲可能不行了。挂了电话,我立刻动身,总嫌车子开得太慢,恨不能插翅飞翔。谁知道,半道上就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瞬间,我泪水肆意,喉咙哽咽,一路上再没说一句话。难怪那次离家时,母亲端详着我的脸,很久很久;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忠孝难两全。没能守在母亲身边为她老人家送终,是我一生抹不去的痛。为此,我常常愧疚不安。其实,我欠母亲的情和爱,何止于此?!母亲,您老人家能原谅我吗?
母亲,你虽平凡,但却伟大;你虽走了,但你的笑容却永刻我心中。我常想:人类的生生不息,不正是因为千千万万个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吗?!
每每想念母亲,我从心底疼痛不已。虽然她已隔世,祈愿天堂的母亲在天之灵安息!
生命的守候
刚入初夏,古城就热了起来,气温骤升至摄氏30多度。
正午时分,太阳又大又圆,像一个悬在头顶上的热鏊子,烤得人火烧火燎,烦躁难耐。
西京天桥上,往来的人流如织;行走在天桥上的人们,步履匆匆,多数是朝着拯救生命的同一个目的地而去的——西京医院。
这家医院为目前军队系统四个军医大其中的一个,所以老百姓习惯叫其四军大。她在西北乃至全国享有盛名,在古城就称得上老大了。因而,来这儿就医问药的人用摩肩接踵形容,有过之而无不及。从黎明时分到夜幕降临,从年头到年尾,几乎每天都像盛大的集会。
在出入这家医院的数日里,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为何看病的人比赶集的人还多呢?或许是中国人口太多;或许是医院的师资力量雄厚、医疗技术精湛;或许是今天的食品安全成了问题……
或许还有很多,我静静地思索着,对着清一色的白墙自问。此刻,一股来苏儿的味道扑鼻而来。
是啊,诺大一个医院,不论走到哪儿,都是前拥后挤、人满为患。挂号要排队,缴费要排队,各科室候诊要排队,就连办理出院手续也要排队!那一排排的候诊人群,少的几十人,多则上百人,常常是下班时间到了,仍叫不到所排的号,只能是除了等,还是等。
到这里看病的人,天南海北,操着南腔北调,行色匆忙,脸色凝重。应该说,大多病得不轻,多是慕名而来。是的,但凡小毛小病,谁愿意跑大老远的路、花那么多的钱,来这遭罪呢?
一个50岁上下的中年男子讲,他来自湖北大悟山区,妻子得了一种怪病,跑了当地多家医院无果。于是,他领着病妻乘汽车、坐火车,辗转4天来到这家医院。可是,3天时间过去了,连个入院前的基本检查还没搞完,住院就更没准了。看着妻子饱受疾病折磨的痛苦状,目睹妻子一天比一天憔悴的脸庞,这位毫无办法的男子心疼不已,眉头紧锁,一脸的无奈!
现在,社会上传一种流行的说法:“有人一路绿灯,没人寸步难行”。这句话正确与否,没予考证。但的确有一种现象是明摆着的:办任何事情都要讲关系、论人情,要么“金钱开道”。往往是正门不通“邪门”来,前门不开“后门”进。这种情况在社会的各个行业、各个部门、各个角落,已属正常,算不得新鲜事了。办事讲亲近疏远,“烟酒烟酒”;看病需朋友引见,熟人关照;甚至人死后的最后一站进火葬场,不也要早早地托人、“打点”,才能上了“第一炉”吗?
我亦如此。得知姐姐有病的消息后,我焦急万分。辗转打了十多个电话,总算拐弯抹角找到了在这家医院工作的一个“朋友”。有了朋友的帮忙,入院、治疗自然顺当。
但实际情况,仍然比想像得复杂了许多。费了多少口舌不记得,想了多少“妙招”终管用。这天早上八点多,主管教授终于同意为姐姐手术了。可是,当姐姐迈进手术室门槛回头的一刹那,手术室的门突然关闭,我的心一下子咯噔了几下,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和滋味。刚入院的那几天,盼望医生早一天给姐姐手术,可真要动“真刀”时,我却害怕了。

神木剪纸 杨慧萍《老虎团花》
手术室的门口聚集了几十号家属,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坐在椅子上,有的席地而坐,有的来回踱着步子。看得出来,大家的心都在悬着,谁都不轻松。这个时侯,大伙多是不说话的,偶尔也听到三三两两议论着什么。这时,一个年轻女人突然跪在几个正说着话的人面前,眼里噙满泪水。她说:“求求你们别说话了,里面做着手术呢!”如此,女子先后跪求了三次,像发疯似的。可是,她怎么能够管得住那么多张嘴呢。有人说,这个女人一定是个神经病人。
末了,这个女子像一只被人丢弃的小猫,蜷缩在墙角,不停地抹着眼泪。我想,她绝对不是一个有病的人。她分明是担心和牵挂手术室里自己的亲人啊!
六个小时,在人生的长河中,只能算作弹指一挥。但对我而言,这几个时辰的确称得上是一个漫长的等待和揪心的守候!期间,手术室的门多次开启,术后的病人一个个被推了出来。只要看到开门的迹象,家属们就会蜂拥而上,看是不是自己的亲人。接上亲人的家属多会喜极而泣,说着安慰祝愿的话,抚摸着亲人的手,推着手术车高高兴兴地回到病房;反之,只能再无奈地回到自己的座位,默默地祈祷着亲人能安然无恙。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守在手术室外面的亲属更加焦虑和不安起来。有的坐立不安,来回走动;有的不停地看着手表、算着时间;有的偷偷地擦着泪水……那种紧张的表情,那些焦急的眼神,那个祈愿的虔诚,那份真诚的守候,写在每个人的脸上。
说实话,我是第一次目睹那种场景,她让我为之动容。这段经历,将会深深刻在我的脑海!
婴儿降生,亲人们要守护在产房外,迎接一个新生命的到来;逢年过节,家人要在路口守望平安归来的亲人;亲人有病住院尤其是手术,亲属要自始至终守候着,祈祷上帝保佑……
守候生命,既是一种幸福,又是一种煎熬,更是对一个人耐力和意志的磨练。
人之最宝贵的,莫过于生命;谁都没有不珍重生命、珍惜生活的理由。
活着,总是幸运的,美好的。
◎郝卡厚,陕西省神木县政协调研员。业余热爱散文写作,曾在《解放军报》《榆林日报》等处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