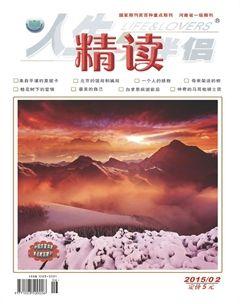一生只做一件事
池莉
在很长的一个人生阶段里,我只长年岁不长心眼,想来真是痴长。
从前,我外婆家屋后有一座大园子,园子里头长满花木蔬菜和中草药,芙蓉花、鸡冠花、桃树、垂柳、小白菜、香葱、车前草、鸡血藤等混长在一个园子,引得蜂来燕往蝶飞蚓爬,使儿时的我玩得十分着迷。当然,这种私家的园子后来很快就没有了,支援了国家建设。园子变成了一座丝织厂,工厂的围墙抵在我家屋后,整日整夜哐当哐当地响。我不喜欢这声音,我从来就不喜欢工厂。从此,我一直心怀渴望,非常非常想养花种草。渴望与日俱增,可多年来就偏是没有机会,既没有自己的住房也没有自己的一寸土地。十几年熬过去,去年分得一套公寓,奔到阳台上一看,发现竟然留了养花槽。这一高兴,头脑轰地发了热,不知不觉拿业余爱好当了正经事做。一连好些日,提只篮子和小桶,四处挖湖泥。在大大忙了一阵之后,花种上了,草也养上了,菜籽也撒上了。然后,抱着肩来来回回欣赏,倒真有一种了却了某个夙愿的感觉。以后每逢出差或笔会,凡遇上奇花异草,都挺执着地弄点回来栽进盆里。家里厨房三天两头做鱼、肉,也常记得将洗鱼洗肉的水倒入花槽。
可是到了秋季,结果并不理想。葡萄才结了几颗,花儿没开几朵,从庐山植物园特意带回的碗莲之类也都死了。怎么回事呢?
为此,我特意找了《花经》来读,读着读着,心中渐亮。合上《花经》,扔下花铲,淡然一笑:我不再养花了。
实际上,《花经》这本厚书我翻来覆去看的只是前面一小节:序言。序言里简洁地记叙了本书作者之父黄岳渊先生的一段经历。黄岳渊先生在宣统元年的时候本是一名朝廷命官,斯时年将三十。有一日黄先生想:古人曰三十而立,我该如何立人呢?他想,做官要应付人家,做商呢又要坑害人家,得做一件得天趣的事才好,才算立了為人的根本,于是,黄先生毅然辞官隐退。他做什么呢?他购买田地十余亩(时田价每亩约二十金),渐扩充至百亩。黄先生从此聚精会神,抱瓮执锄,废寝忘食,盘桓灌溉,甘为花木之保姆。果然,黄家花园欣欣向荣,蒸蒸日上,花异草奇,声名远扬。每逢花时,社会名流裙屐联翩,吟诗作赋。更有文人墨客指点花木,课晴话雨。众人深得启示:既混浊之世,百无一可,唯花木差可引为知己。
据说当时的文坛名人周瘦鹃、郑逸梅等人皆为黄先生的花木挚友。
黄先生养花养出了精神文明,养出了人间知己,养出了《花经》这等好书,恐怕这才叫养花种草!这才叫做了人生一件事!
一件事要做好,岂能凭你心中有一点喜欢?有一点迷恋?三天浇点水,五天上点肥?
少年狂妄,自以为聪明。把表面的一些由头借来,实际标榜自己为至情至性之人。这也做做,那也试试,好听人评价个多才多艺。近年来国家大兴经济,文人纷纷“下海”,我也曾与人发议论说作家的智商是足够经商的。最近由读《花经》而获顿悟:人的一生只能做一件事。政客们终身搞阴谋,商人们终身搞欺骗,情种终身搞爱情(比如贾宝玉),黄岳渊先生终身搞花草。一生的时间并不多,一生的精力也不多,要搞好一件事实在不容易。用去一生,搞好了一件事,那也就够可以了。世上不知多少聪明人,一生没有搞好一件事。
总之,我是不敢再说文人经商之类的话了。也不敢再狂热地养花弄草。就连剪裁时装、研究烹调之类的兴趣也淡了下来,兴致所至,偶尔为之,拿得起,放得下,决不长期牵肠挂肚。
应该是不受诱惑的年纪了。傻一点儿,笨一点儿,懒一点儿,冷一点儿,就做一件事——写作——我这一生。
(摘自豆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