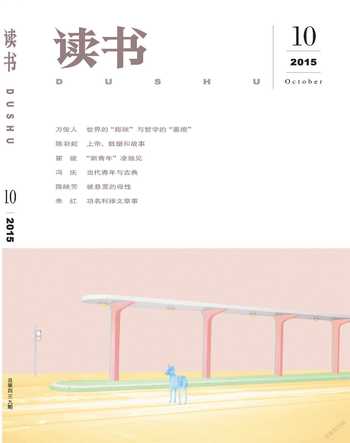西看佛树几千秋
朱浒
印度与中国同为文明古国,两国间的交往历史悠久。佛教承载了两国间的精神纽带。佛教自两汉间传入中国后,逐渐获得长足发展,最终成为中国主流信仰之一,由佛教而生发的艺术亦几乎涵盖着整个中国大地,构成了中国宗教艺术的主脉。在整个中国思想史或艺术史上,从来没有哪一种外来文化能在中国产生如此深广的影响。而就印度佛像的出现到传入中国以来的历史进程看,中国佛教艺术的发展与印度佛教及其艺术的兴衰密切相关。
为了追溯佛教艺术从古印度经中亚远徙中国,继而经海上传至日、韩的世界化宗教之路,研究者们曾不遗余力搜集种种证据。在遥远的犍陀罗等地,欧美学者主持了作为其殖民地的印、巴的考古工作,亲身参与了一些重要的早期佛教遗址的考古发掘,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如福歇、索普、马歇尔、德·黎乌等率先对印度佛教艺术的起源展开研究,提出了所谓犍陀罗佛教艺术的“西来说”,同瑞典人安特生对中国仰韶文化彩陶的“西来说”遥相呼应,带有一定的殖民主义的色彩。而日本也不甘示弱,在脱亚入欧的进程中开始对同为亚洲国家的印度艺术进行过系统研究,对中国佛教文物的掠夺和搜集也不遗余力。遗憾的是,中国在这一轮佛教艺术起源研究中自顾不暇,处于缺席状态。甚至中国佛教艺术研究的早期成果大体上可以视为西方和日本学者在中亚探险式考察的衍生物,如伯希和、斯坦因、斯文·赫定、冯·勒柯克、大谷光瑞等先于中国人研究中国的佛教艺术。这种破坏性和掠夺性的考察是中国佛教艺术研究中的最大憾事。
然而当我们回望历史,对佛教真理的探索是中古时期中国伟大的先行者—求法僧们的孜孜不倦的动力。我们有过三人游记(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重塑半部印度历史的伟大壮举,出现过法显、宋云、玄奘等文化使者和探险家。由于历史原因,近百年来有关古印度佛像起源及早期佛教艺术传播的研究中国学者处于缺席状态,是十分遗憾的。今天,这一现状正在逐渐改变,伴随中国的经济腾飞和中国学者学术视野的拓展,使得我们重新审视这一影响中印两千年的精神纽带—佛教及其艺术的传入与本土化问题。
今年二月,笔者来到印度最大城市孟买,并以此为起点,开始了对印度早期佛教石窟的寻访。在这里,我切身感受到现代印度社会中民族、宗教、文化的强大感染力。从孟买至德干高原之间的西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广袤土地上,分布着数十座风格各异、年代跨度很长的佛教石窟。这些佛教石窟虽然没有桑奇与巴尔胡特大塔的声名远扬,也不似迦毗罗卫、菩提伽耶、萨尔那特这般佛教圣地丈量过佛陀生前的足迹,但作为印度早期佛教艺术的重要载体,它们无疑代表了佛教在西印度的早期发展。其年代上溯公元前二世纪的巽加王朝与安达罗王朝,下限可至七世纪之后,足有上千年时间,囊括了印度佛教艺术发展的古典时期。这些石窟见证了佛教艺术从“象征物时期”至佛像蓬勃发展时期的过渡,构成了同遥远的犍陀罗、秣菟罗、阿玛拉瓦提三大中心的佛教艺术可比较研究的序列。
当年,玄奘在游历天竺时曾经走到这里,目睹了阿旃陀石窟的庄严伽蓝,写下“国东境有大山,叠岭连障,重峦绝巘。爰有伽蓝,基于幽谷,高堂邃宇,疏崖枕峰,重阁层台,背岩面壑,阿折罗(唐言所行)阿罗汉所建”(《大唐西域记》卷十一,季羡林校注,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版)。在阿旃陀第十六石窟外,两只石象分立左右,恰合《大唐西域记》中“伽蓝门外南北左右,各一石象”的记载。这一石象是将玄奘的记叙同一八一九年由英军士兵偶然发现的阿旃陀石窟关联起来的直接证据。更难能可贵的是,第二十六窟支提窟的铭文中刻有供养人“Achala”的铭文,其发音与《大唐西域记》所记载的阿罗汉“阿折罗”的读音一致,成为语言学在历史、考古研究中的应用佳例。在玄奘法师曾经造访过的千年伽蓝中,历史被浓缩在这长度不到六百米的断崖间的石窟建筑、雕塑与壁画中。阿旃陀石窟有很多来自东亚的朝圣者,我们在石窟间偶然邂逅到几位身着藏传僧衣的僧人,他们虽然长着一副东方面孔,但并非中国人。
在找寻一处并不知名的早期佛教石窟锡万内里(Shivneri)石窟途中,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它位于锡万内里山断崖上,在之前几乎没有中国研究者亲身造访此地,甚至当地居民也闻者甚少。锡万内里山得名于印度十七世纪著名民族英雄贾特拉帕蒂·希瓦吉(Chatrapati Shivaji),这里是他的出生地。此时莫卧儿王朝国势衰弱,马拉特族的勇士希瓦吉乘势起兵,击败莫卧儿帝国,建立了当时印度强大的政权马拉特帝国,后来形成了马拉特联盟。希瓦吉也被后人尊为印度教的圣人。然而在希瓦吉出生的一千多年前,这里的山石就被上座部佛教徒所利用,开凿出雄伟的毗诃罗窟。在找寻锡万内里石窟的途中,在当地向导的指引下,我们爬过几乎垂直的峭壁,从缀满落叶、残损的石阶上拾级而下,在西德干高原的山中攀爬,追索古老佛教石窟的凄凉与辉煌。当我们终于在希瓦吉城堡(Shivaji Fort)的后山断崖上找到了石窟的入口,同行的十五位队员中仅有三位成功进入了锡万内里石窟。
对西印度石窟的详细调查,日本人是捷足先登的。佐藤宗太郎的《印度石窟寺院》一书已经出版了三十年,而这里刚刚钤下中国人学术考察的足迹。日本青年学者筱原典生近期出版了一本《西天伽蓝记》(兰州大学出版社二○一三年版),再次拉开了同中国学者的差距,也使我们陷入自责。对佛教义理的追索,玄奘犹如不可超越的丰碑,但对佛教艺术的探寻,中国在近代学术发展中有太多的亏欠。这种缺憾深深激发了我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经过二○一一年与二○一五年两次西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之旅,我走访了西印度佛教石窟群中的十三座,分别是珀贾(Bhaja)石窟、伽尔拉(Karli)石窟、根赫里(Kanheri)石窟、贡迪维蒂(Kondivie)石窟、贝德萨(Bedse)石窟、兰亚迪(Lenyadri)石窟、锡万内里(Shivneri)石窟、杜尔贾莱纳(Tulisa-lena) 石窟、门莫迪(Manmodi)石窟、奥兰伽巴德(Aurangabad)石窟、纳西克(Nasik)石窟以及著名的阿旃陀(Ajanta)石窟与埃洛拉(Ellora)石窟。它们同中国河西走廊沿线为数众多的石窟一样,缀满了佛教曾经兴旺的土地。
无论是精神信仰抑或是学术研究,中国人在骨髓深处都有一种不服输的探索精神,一种求法精神,也反映在学术道路的追索上。
对中印文化关系的研究并不是中国近代学术的主脉。由于科学技术、社会政治制度均远远落后东、西方列强而饱受欺凌,中国人将视线长期集中在对发达国家典章、军事、科技等方方面面的研究和效仿上,而作为古老近邻的印度,由于近代完全沦为殖民地,并不为中国主流价值观所倾慕。虽然有汤用彤、季羡林等诸先生致力于“熔铸古今、接通华梵、学贯中西”,在中、西、印三者之间寻找契合点,对印度的哲学、语言、文学等方面采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治学精神,但并未引起足够关注。在艺术领域尤甚乏力,常任侠、王镛等先生将视线投向印度美术史,先后著有《印度与东南亚美术发展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八○年版)、《东方艺术丛谈》(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印度美术史话》(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译有《印度艺术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四年版)等书,但同西方美术史研究相比,对印度美术的研究仍显薄弱。近百年来,佛教艺术研究的先机被西方和日本探险家占领,一方面,研究的对象往往依靠被西方掠去的材料,如敦煌藏经洞的文献,被斯坦因、伯希和、勒柯克、华尔纳、科兹洛夫等人疯狂盗掘的西域佛寺艺术品;另一方面,对佛教遗迹与文物的保护还要依靠外国的资金帮助,甚至对印度阿旃陀石窟的保护也有日本财团的捐款。一百多年过去,中国和印度作为曾经的落后国家虽然在经济上翻身,但在文化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必须直视丝绸之路沿线诸国曾经创造的灿烂文化,并在当下增强文化的互动交流与对遗产的保护。
玄奘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人物,更代表了一种孜孜不倦的求法精神。狭义的玄奘之路只具有地理意义,而广义的玄奘之路有很多种,有探险之路,有政治之路,有商贸之路,有军事征服之路,更重要的是追寻真理之路。在佛教艺术领域,同样需要弘扬玄奘精神。从近两千年的佛教义理与艺术在中国的流布与发展脉络来看,对佛教艺术源流的追索也是求法的目的之一。这条道路曾经存在着三次高峰,首次为犍陀罗艺术在汉晋间的初渐,其次是笈多艺术在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典范效应;最后为藏传艺术在十二世纪之后经藏、蒙、满各部族信众而遍及全国,以至西方学者习惯将深受印度帕拉王朝影响的中国藏传造像和尼泊尔的造像一起称为喜马拉雅艺术。
艺术在世界几大文明中的传播,中国人习惯采用“拿来主义”,加以融会贯通与改造,进而远播日、韩。近代以来,在对佛教艺术源头的研究中,欧美、日本、印巴学者都走在了中国的前列。中国学者大都仅关注国内出土的新材料,而鲜有关注域外的材料,更缺乏向玄奘那样勇敢走出去的勇气,使得这一学术研究的体系出现了缺环。统观历史,中国向来不乏探险家与求法僧,从张骞、甘英、朱士行、法显、宋云、惠生到玄奘,穿越沙漠,深入不毛,“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并不向恶劣的条件妥协。近日一则新闻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一位硕士研究生只身深入伊拉克腹地去寻访古迹,被当地武装误认为是极端组织成员而被控制。类似的事情在玄奘身上也发生过,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他在恒河中遇到强盗,差点被杀祭天,幸而天气突变,强盗惊以为触怒天神而释放了他。玄奘在尼莲禅河边曾撰写过一首名为《题尼莲河七言》的诗:
尼莲河水正东流,
曾浴金人躯得柔。
自此更谁登彼岸,
西看佛树几千秋。
这首诗曾散轶千年而被重新发现于莫高窟藏经洞,后来被斯坦因盗至大英博物馆。在玄奘精神的指引下,在中国文化复兴的进程中,印度与中国在文化上的联系将更加紧密。随着“欧洲中心说”受到愈来愈多的质疑,人类文明的多极化发展态势愈发清晰,屹立于东亚的佛教文明势必迎来更大的发展。印度与中国的关系,长期以来被比喻为“龙”与“象”。龙之精神,在于坚韧而适应环境;象的长处,在于负重而宽仁。对这两个承载了太多历史积淀的国家和民族来说,在佛教精神的浸染下,“龙象之争”可以变为“龙象之和”。我们迫切需要玄奘精神的现代重生。而我们的西印度佛教石窟的考察之旅,也正是在龙、象之间迈出的一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