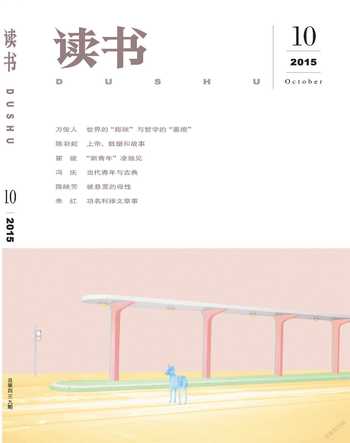写在巨变时代的伤痕上
李宗陶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自由欧洲电台跟播音员G.R.厄本做对话节目时,借用物理学概念谈出两种不同的历史书写:“速度历史”和“质量历史”。前者指能够分辨历史规模和规律的;后者指能够对史料进行细节整理和分解的。汤因比认为,理想化的历史书写应该既是“速度的”又是“质量的”,但这两种方法被同一个人成功采纳是很难得的。
我重读了杨国强的几本专著:从一九九七年的《百年嬗蜕》、二○○八年的《晚清的士人与世相》、《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曾国藩、李鸿章及其时代》,然后再读二○一四年末中华书局出版的《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发现浸淫清史四十多年的作者以其绵密深沉的书写,为世人提供了既是“速度的”又是“质量的”难得范本。
新近出版的《衰世与西法》收录了十四篇专论和一篇媒体访谈,时间跨度是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海战的三十多年。这是中国近代化意义上的巨变时期,上接康雍乾三朝构成的十八世纪“盛世中国”,下启一个由“变局”而“危局”进而“残局”的百年。
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国由盛而衰,盛世里那些潜在的矛盾慢慢积聚、生长、发酵,成为十九世纪社会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困境。书中提到:一八三五年,道光皇帝召见翰林院编修张集馨时,吩咐他多读经世之书,少赴文酒之会。经世之学兴起在嘉庆道光年间,是以学问济时、以儒生的议论策论针砭时弊,尽管这些议论并没能进入国家权力而转为事功。然而康乾盛世天下太平之时,流行的可是乾嘉考据之学,纯学问。学问被要求入世,说明天下出了毛病,毛病在哪里呢?
作者用两篇五十四页的篇幅分析了病灶所在:一是吏制的失范和败坏。清代二百多年,做官的正途本是科举入仕,但“道光朝一变,而咸丰朝大变”,到了同治后期,卖官已相当普遍。朝廷为什么要卖官?因为康熙帝从明亡中吸取教训,立下“永不加赋”的祖宗家法,只能维持一种脆弱的平衡,遇上兵事、河工、灾荒,国家钱不够用,于是“道光辛丑、壬寅间海疆用兵,始大开捐例”。捐钱就可以有官做,导致官场里“流品之杂已极矣”:广东省的逃犯逃到广西可以捐成一个候补知府,而江浙两省逃难的人可以一个一个通过捐纳变成京官。书中提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后,通过捐官成为四品到七品官的,已超过科举入仕的人数。而捐班中人用钱买权力,意在收获更大的财利,是“以商之法为官”,作者准确地给出一个字:劫。“这种‘以弊为活’的生存方式,决定了地方衙门里的胥吏常常会与枉法、勒索、侵渔、贪赃连在一起,做出种种丧心病狂的事;‘以弊为活’,在本义上便是以世相的黑暗为活和人性的黑暗为活。”这洞见亦可烛照后世。
吏制的崩坏必然导致民变,若遇天灾,更是对国家权力的考验。我记得曾经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饥馑发生后国家机器可发挥的作用请教过作者,他举清代的荒政为例:每逢灾年,各地粮仓大开以赈饥民,从容裕如。在此书中,则读到“君权重荒政”的传统在衰世中的窘迫:官力枯竭,无可措手。所以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一路绵延的台风、海潮、雪雹、干旱中,在光绪年华北的“丁戊奇荒”中,妇女儿童被贩卖、父母食亲子、“妇人枕死人之身,嚼其肉者”层出,骇人听闻。有地方设了粥厂收养饥民,因为争抢和时疫蔓延而死人的,南北都有记载。然而,作者也同时拣出这些史料给我们看:朝廷仍然从军费中挪移二千多万两银子赈灾,皇帝和地方官向天求雨,七岁皇帝下罪己诏,还有县官因救灾积劳病故,临终留下沉痛内疚的手书,都“在一个变迁剧烈的时代里折射了儒学民本主义和民生意识的最后一点余辉”。在同一时间里,也有克扣、侵渔、玩视赈务的官员,作者视为“全无心肝”,而从朝廷处分的“下手极重”和“动了杀机”看出国家权力维持全局的紧张和艰难。这是国家权力不得不下移的前兆。
在这样一个走下坡路的时代里,大清朝不幸遇到了西方列强的一次又一次冲击。作者曾在课堂上对学子们发过感慨:中国倒霉就倒霉在这里,一是在由盛而衰的过程中遇到西方,二是在清代学术即汉学(追求知识渊博却缺少本根的一种学问)的文化背景下面对西方―倘若在宋代理学(追求价值和本源的学问,有底气和血气,所以日本维新时有识之士捧读朱子)的背景下,自强、洋务、维新这一系列应变,会不会应付得体面些?
他也常说,后人读史,不免“百感交集,既惊且诧”―国家内部由盛而衰,而衰世之中恰逢列强环逼,这两个局始终纠缠着,一路陪大清走过十九世纪,从庚申之变到甲午战争,一步步走向解体,催生出一个四分五裂的民国。
在作者看来,咸丰十年(一八六○)的“庚申之变”而非道光二十年(一八四○)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开端—打了三年的英法联军之役在那个庚申年收官,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城、火烧圆明园;此前,三十一岁的咸丰帝已带着近臣和后妃仓皇北上,避走热河,号称秋狝(打猎);留守紫禁城与英法二国签下两份《北京条约》的恭亲王奕这一年二十八岁,在英方随军摄影师费利斯·比托的偌大镜头面前,“这位皇帝的兄弟惊恐地抬起头来,脸刷的一下就变得惨白……以为他对面的这门样式怪异的大炮会随时把他的头给轰掉”(这一幕记录在英国陆军司令格兰〔Sir James Hope Grant〕的日记里)。这一年,在奏议中首次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曾国藩五十岁,而在皖北操练淮军的李鸿章三十八岁。这一年,朝野上下都在说“自强”。
将“自强/富强”观念的移入视为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发端,作者看重与深究的,是中西交冲的痛感程度和其中的义理转向。在首篇《经世之学的延伸和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起点》中:“庚申之变以沉重一击致创巨痛深……与二十年前的士议比中英鸦片战争为‘海疆骚动’,这是一种明显的不同。”在第十二篇《近代中国的两个观念及其通贯百年的历史因果》中:“作为一种思想和义旨,‘富强’原本出自法家并归属于法家。因此,在儒学灌输浸润二千多年之后倡言‘富强’,不能不算是显然的大变。……由此形成的历史因果,则使古老的中国社会在移花接木之中不复再能尽循旧时故辙,同时也是古老的中国借助于这种变化而获得了一个近代化的真实起点。其间既有时势造人,也有人造时势。”而其中涵摄的“营造物力、技术主义和民族意识”,使得中国的近代化从一开始就有别于西方,“自其发端之日便已带着与生俱来的不平衡性和不完整性”。中国是被被动拖入近代化的。笔到之处,一次次点明这样一个事实:在被动中引入的各种陌生事务因为不是内生的、自主的、从长计议的,常常在仓促和错解中被夹生地楔入中国社会,并在日后不断反嗝出消化不良的隔夜之气。
最先对接中西的“抚夷局”在原先的设想里是个应急的临时机构,稍稍太平后是要“裁撤”以“符旧制”的,不想业务繁忙,升格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辛丑后改为外务部),四十一年间俨然成为这个国家“综乎六部”、“牵汇万端”的所在,并在身不由己中一变再变。与此同时一次又一次刷新的,是朝廷中那些自大陈腐、僵化迷信的脑袋。两江总督裕谦剥下“白黑夷匪”两张人皮、抽其筋以做马缰的血性没能阻退夷人,相反引来更强烈的报复。一个月后,英国人就攻占了镇海(《晚清的士人与世相》,109页)。在一轮轮的败阵吃痛之后,在蔑视、愤怒、畏惧、痛恶和惊讶的情绪迭变之后,那一代人心中便有了刻进骨头里的困境意识,陪伴他们终老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智勇俱困”。
因自强引入的“制器之器”,在三十多年里开出了以江南制造局为代表的近二十个造枪炮的机器局和以福州船政局为代表的若干船政局。五千多万两白银的开支和万余雇佣工人造出了成千上万仿制的来福枪(在一位西人笔下,当时中国所用来福枪有十四个不同种类,从最新型的到古老的粗抬枪)、林明敦枪、黎意枪、快新利枪、马梯尼枪、毛瑟枪和田鸡炮、乌理沼炮、阿姆斯脱朗炮;林壳明轮船、木壳暗轮船、木胁兵船、铁胁兵船、钢胁快船、铁甲兵舰、鱼雷舰、浅水舰,等等。
然而,西方的制器是工业革命的结果,它们属于与社会技术革命相协调的经济形态,却被中国因为政治而急迫引进了切割掉头尾的生产片断:它上不接技术(到了后期,造价常常几倍于直接从国外买枪炮),下不接市场(由朝廷“拨济”到南北军队,没有进入成本、利润、再生产的经济链),一旦朝廷投入的白银难以为继,便不得不列入“奏销”之列。
而且,因为国家权力下移,制器分散在封疆大吏们的手中,而疆吏多用幕府经管,在各自的辖地分散、重复、毫无分工概念地生产着,既缺少可以连接的原料工业和重工业,又依赖外国专家的二手传授,彰显出那个时代里的自强始终带有强烈的个人性、地方性和局部性,所以“师夷制的事业在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都难以伸展扩张”。以兵工业的困境为例,作者深刻地揭示出自强这种义理落地到中国当日现实中的重重阻隔和受制,并借刘坤一的感慨写下这样富含哲理的句子:世间人多数不能真正怀想长远,所以多数不能有恒。
《衰世与西法》大致有两条线,一条描绘庚申到甲午中西交冲下政治与社会的几个重要关节,如上文中提及的吏制失范、天灾与赈济、兵工业的开局与困境,以及未能一一展开的条约制度对中国的改造、绅权的伸张、因借法自强而进入中国历史的外国人,还有层出不穷的教案。另一条则着力展开晚清士人的思想世界。中西交往由暴力开始,慢慢演化成文化的交接―当一个民族对外来侵逼做史无前例的回应时,文化一定会成为一种支撑精神的力量,所以承载了中国文化的士大夫历史地成为这一过程的主体。
在前一条线上,晚清绅权的伸张很是精彩:与绅权相对的是国家权力,与绅衿(没有进入仕途的读书人)相对的是地方官和皇帝,天下太平时后者一定不喜欢前者。在十八世纪绵延的文字狱里,在“哭庙案”、“奏销案”里,绅权都是君权有意摧锄的东西之一,于是“不同于编户齐民的缙绅先生们则在前朝的‘横桀’之后丧失了足以干预公事的心力和臂力,他们在二百多年里大半都活得非常安静”。
但十多年间,东南有太平天国,华北有捻军,西北有回民起事,内战烽火烧得地方官为练兵筹饷不得不向地方上代表民间权威的“士人”和“局董”们俯趋,再加上西人的闯入,绅权在内忧外患的召唤下重回世间。其间,与卖官相类似且同步发生的,是各省乃至地方的举人和生员也可以花钱捐了,所谓广额。同样,与卖官导致的官场“下流”相似,被一起编入绅权之中的,必有“人才固不足观”和“人品尤不可问”。这是一个相当壮观的变化,相当于在纯正的读书人中间掺进一捧一捧的沙子,而这些人代表的绅权“开始成为一种茁壮生长的社会力量,起伏翻腾于四面八方,为衰世的中国增添了种种动荡”。
大概因为生于浙江,作者爱提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在京做官的浙江人与地方绅衿相互呼应,历时两年而掀天揭地,进而翻局。浙江官场上涉案的巡抚、知府、知县、候补知县因“枉坐重罪”、“玩视人命”纷纷跌倒,成为绅权打倒官府的案例,可见当日绅权已能表达公共意识和公共意见。文中反复强调晚清国家权力下移,也许可以说,绅权的廓张是广义的、隐性的国家权力下移。
绅权本是中国社会里非常古老的东西,但在晚清渐有“潜伏民权”的意思,显然是在时势裹挟中,在主动被动中更张了原义,派生出新义。从魏源在以“制夷”为抱负的同时对西方议会制度流露出明显的推许赞赏开始,社会变迁带来的思想变迁绵绵不绝,汇成一波又一波的西潮,并且在晚清的后几十年里越来越显示出思想变迁反过来促成社会变迁的特点。但这是一种“冲击—反应”下的被迫之变,且囿于一个读书人群体,所以始终与社会现实生生脱节。
中国两千多年来,素有清流。清流的根基是士大夫的清议,它是一种公共舆论,既参与评判又接受评判;它从儒家传统中来,是一个群体现象,这个群体以道德自律。在明代,清流因上言而遭廷杖,屁股被打得血肉模糊,旁人敬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清流比洋务派更能得到士大夫群体的拥护,而清流反洋务,在于坚守“成法”,更在于不能容“以夷变夏”。但到了甲午、乙未年间,清流们被日本人的“弹丸黑子”打醒过来,追根溯源又回到洋务派“自强/富强”的老议题上;他们在共指李鸿章为祸首、公敌的群议中走到一起来,主导了当时的舆论和人心向背。
作为京城和长江中下游的清流领袖,翁同龢与张之洞各成门户,由此筑成一种人际勾连,一方面影响和导引士林,士林中人也会影响常熟与南皮,由此影响和导引政局;另一方面,它成为上达庙堂和君侧的一条通路。也因此,清流造就了本在清流渊源之外的康有为。
康有为如何成功走到光绪身边一段读起来颇有味道,是其细腻笔触令当日场景鲜活的一例:一八八八年开始,康有为不断上书光绪、上书徐桐、上书曾纪泽,也曾递名帖给帝师翁同龢,求见;但一路叩门,一路碰壁,离开北京时愤然写下“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沉沉叫不得”。张之洞门下的梁鼎芬起了作用,“力为周旋”,有心将其引到张之洞面前。而京中清流也对康有为“尽涤旧习”以图“气象维新”的志向颇有好感,在许多官员奏劾康有为“惑世诬民”时施以援手。正是这样的汲引托举,康有为才得以拾级而上,层层登高,终于叫开“帝阍”而一展怀抱。“曾久被目为士人典范的清流群类显然已不再全是旧日模样和全守旧日范围了。就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而言,比之一人一身的叫开‘帝阍’,这种群体的变化无疑更内在,并因之而更深刻。”
然而,“清流始旧而继新,洋务本新而反趋于旧”。一九一三年,康有为忆起当年七上皇帝书以及创议立宪等维新主张,追悔为“不察国情之巨谬也”。在他身后,当年的新党们(严复、章太炎、梁启超等)在二十年间一个个蹙额疾首,先后掉头而走,群体性地回归旧途以寻安身立命之所,不能不成为一种更加引人深思的历史文化现象。究其原因,作者以为也在“夹生”:这些人大声疾呼“全变则强”,从一开始就羼杂懵懂和盲目,引入脱空的西学西法为中国诊病必然失真,而滔滔从之的众人和倾附的西学之间深深隔膜着,仅有风气而无学理。其后新学随波逐流一变再变,经兼爱变保种,平等变强权,民族主义变帝国主义,一路走向民权论、国权论、无政府主义、军国主义……曾出现过老子是清流,儿子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怪象,难怪潘光旦面对各种思潮有“河流带走落叶留下石头仍在原处”之叹。这一场西潮回澜内含的矛盾、怀疑、复杂和深度,从思想角度折射出士人心灵和精神的大变,折射出富强和价值之间的撕裂。如果说《晚清的士人与世相》集中呈现清流保守的一面,本书则展示了这一群士子在“国殇”激迫下比洋务派更激进,以至于失去常态的另一种面相。
对于一位历史学者,寻找档案、寻根溯源总是令人上瘾,而这件事是没有底的,永远有这样或那样的史料在未来的某个角落等着你。我不确定每一回合作者怎样给自己按下暂停键―二○○八年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旁听晚清史课,偶尔会见他带出手头正细读的书,像岭南大儒陈澧的《东塾读书记》,章太炎弟子、经学家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等等。听他分享其中细微感性(通常不会写进正经文章)的部分,比如王闿运尤怕打雷;慈禧是个不善于表达母爱的女人;赫德值得书写;反对袁世凯称帝说明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没有沦丧……投入到创造性的历史写作中。没错,历史写作是一种创造。他坐下来就着苦茶用心思量,小心谨慎地将从史料中梳爬出来的脉络、特征和他的思想洞见转化为一条条风骨棱棱的句子。而我们,总能读到他深埋其间的慨叹。
(《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杨国强著,中华书局二○一四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