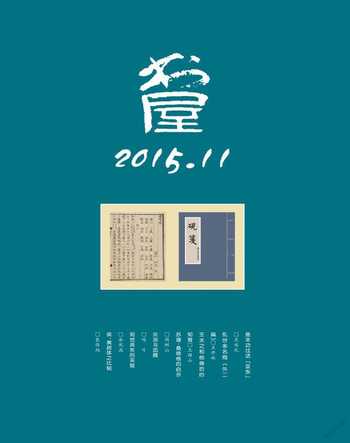辞书情结
周朝晖
钱钟书先生博闻强记,冠于群伦。尤为难得的是“聪明人偏要下最笨功夫”的治学精神,“于书无所不窥”,甚至连辞书、字典也在他津津乐读的阅览视界之内。著名法学家、钱钟书小学同窗邹文海先生晚年追忆钱钟书中有这么一段轶闻:
1939年秋,邹文海赴湖南安化国立师范学院任教,钱钟书正好想去探望在此执教的父亲钱基博,遂一路同行。彼时抗战军兴,连月关山羁旅,行途备尝艰辛,然钱钟书却一路手不释卷,自得其乐。邹文海以是为什么了不得的好书,一看竟是一部英文字典,颇不以为然。钱钟书说:“字典是旅途的良伴。随翻随玩,遇到几个生冷的字,还可以多记几个字的用法。更可喜的是,前人所著字典,常常记载旧时口语,表现旧时之习俗,趣味之深,不足为外人道也。”邹文海先生是厦门大学法学院拓荒人之一,据该校耆老及后生学子回忆,邹先生为人治学严谨笃实,这段回忆应该是靠谱的。无独有偶,读钱钟书夫人杨绛《我们仨》时,我也发现书中对钱氏嗜读字典的癖好也多有言及:抗战期间钱氏一家被困孤岛上海,物资贫乏,生活拮据,又无书可读,钱钟书就读字典度日;“文革”期间,钱钟书下放河南省罗山县“五·七干校”,在炉灶间专司烧水之职,闲时总抱着一部比砖头还厚的外文原文辞典阅读,一坐就是大半天。字典、辞书只是语文工具书,能好读不倦并从中受益,这种读书功夫恐非常人能及。
不过,以嗜读辞书、字典为乐事者,似不唯钱钟书先生个例,日本作家、学人中有辞书情结者亦不乏其人。年初有客自东瀛来,赠我一部《广辞苑》,这是我当年学生时代常用的辞书,虽是新出的第六版,与我当年常用的版本隔了两代,但一见之下仍有如遇故人之后裔的亲切感,摩挲把玩之间不禁浮想起日本人与辞书的种种。
看日本作家、学人生活照,常见他们在榻榻米房间盘腿或跪坐读写的情景:一方矮桌上,或散乱或规整的原稿纸张、文具之外,边上总有一部或几部字典、辞书在焉,这种书房风景在日本至今习以为常。对字典、辞书,日本不少学者、作家有着近乎“拜物教”般的情结。
早年读福泽谕吉的《福翁自传》,非常惊叹那些幕末武士用刀头舔血的精神追求新知的劲头,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福泽谕吉学外语的历程,又一次路过大阪时特地去观瞻福泽谕吉青年时代求学的“适塾”。福泽出身于幕末中津藩(今大阪)一下级武士之家,青年时代的福泽没有像绝大多数武家子弟进藩校或私塾学习居于官学顶端的朱子学,而是选择到大阪医生绪方洪庵门下修习兰学。所谓兰学就是荷兰文以及用荷兰语写成的有关医学、筑城、造炮等西方科学技术。江户幕府时代,日本锁国二百多年,唯一允许长崎一地可和清国与西欧的荷兰通商。兰学在彼时虽说是末流之学,却成了日本人接触西学、吸收西方文化的一个源泉。塾主绪方洪庵的外语教学方法很特别,作为对前来门下求学的生徒的一项必修基本功就是每日抄写日荷字典,然后熟读记诵,再去直接读解、翻译荷兰文原著。穷困的门生还可以用抄写翻译荷兰文著作充束脩。靠这种抄读字典的教学法,适塾为近代日本成功转型输送大量第一流人才,也使这座普通民宅成为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学校。至今适塾旧居的玻璃柜里还保存着当年学生们抄写的《和兰字典》,密密麻麻,蝇头小楷,一笔不苟,抄在绵薄的和纸上有三千多张,令人望而生畏。靠着这种扎实过硬的功夫,福泽很快成了精通兰学的高手,不出几年就荣任适塾教头。为了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他应奥平藩的派遣前往江户城效力。1853年5月,美国东印度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四艘涂黑的铁甲船前来叩关,幕府掂量一番后,日本和佩里签订城下之盟,被迫开国,横滨成为对外商港,欧美政府机构和商社人员接踵而来。福泽受命到横滨办事,和洋人打交道傻了眼:时代变了!如今横行世界的是他完全不懂的英语,耗费多年苦功习得的荷兰语全泡汤了!但福泽没有气馁,得知横滨有个会英语的幕府官员,又萌生了一丝希望,他千方百计求人引荐向那位官员学英语。但这个幕府外交官,尽管英语能力也不过洋泾浜的水准,却是当时日本国内屈指可数的能用英语和洋人打交道的大忙人,根本没有时间教福泽学英语,被福泽的求学若渴的所打动,作为补偿,特许他来家中借阅当时日本独一无二的《英荷字典》。福泽喜出望外,决心将这部字典一字不漏抄出,为此不惜从江户(东京)徒步来横滨。如今乘坐京浜东北线电车从东京往横滨不到两个钟头的路程,但这条在一个半世纪前铁道未通的东海道,单程就要一个昼夜,不唯奔途劳累,更有性命之忧,尤其是夜黑风高之际,野兽出没,还有埋伏密林中图财害命的强梁和拿独行者练刀的变态浪人。福泽几度虎口脱生仍一如既往,终于把那部字典抄完。以荷兰文为桥梁,福泽终于掌握了英语,得以了解当时处于深刻变革之际的日本最需要的西洋学问和思想,他本人也成为幕末极少数通晓西洋事情的“洋才”,被幕府高层擢拔重用,不仅改变了自身命运,也以强大的影响力促进日本向近代化国家的成功转型,其拓荒启蒙之功余威犹在,至今日本仍恭恭敬敬把他肖像印在面值最大的万元纸钞上。
某种意义上,敲开日本的近代史大门的力量,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器”的威压冲击之外,或许也有几部手抄字典所带来的“知”的强大辐射能量吧?
日本现代意义上的辞书字典拓荒人是比福泽小了一轮的日本国学家大槻文彦,我是在阅览琉球文献时间接了解到他的档案的。此人是幕末史地学家,写有《琉球新志》一书,所附地图异常详尽清晰。同时大槻又是日本现代文法学的拓荒人,运用西方的文法逻辑对东洋(中日)的语汇经典进行理论上的整合,对日本现代辞书事业发展,影响甚巨,不必说日本,至今我国语言学界仍在沿用的所谓“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文法概念,即来源于大槻文彦的发明。当今我国媒体或日常中一日不能或缺的词汇“企业”,却是源于早在百年前经由他编纂的辞书《言海》的创意。
现代日本作家中,川端康成酷爱读辞书字典是出了名的,以致在日本有“国民辞书”之誉的《广辞苑》三番两次出版都请他捉刀写序。在序言中,他说平日最喜欢读辞书字典一类的书物,一再强调:只有辞书才是真正值得购买、收藏的书;礼赞新村出编纂《辞苑》这类经典辞书的功德,说它是“书房无上的装备,总带来超乎期待的回报。数十年来片刻不离,是书桌上的良师益友”,甚至到了“无《辞苑》处绝不动笔”的地步。川端的文章典雅、洗练,是举世公认的“名文家”,莫非其卓越的文学表现力也得益于长年耽读《辞苑》这类经典所受的锤炼和熏陶?
川端康成推崇不已的《辞苑》即是朋友惠赠我的《广辞苑》前身,1935年由博文馆出版,比我国最权威辞书《辞海》还早一年问世。后来由于战乱等因素博文馆遭遇不况,版权让渡给岩波书店。战后,为了适应日本社会大量涌现的新词汇新用法,经过大规模增删,1955年5月由岩波书店改名《广辞苑》发行。自此仿效国际惯例,这部大型辞书与时俱进基本上每隔十年就会来一次大修订,迄至2008年,半个世纪内已经编修刊行到第六版了。而每度修纂必汇聚上百个活跃在各个领域的专家学人,持续多年精心研磨而成,所涉内容森罗万象,解词精湛扎实可靠,又及时吸收新出现的语汇或知识,因而深受读者信赖。自问世以来,《广辞苑》一直是日本最畅销的大型辞书。据统计:不算日本图书馆、教研、学术机构,也不计海外订购、流通的数量,在日本国内,迄至1998年第五版问世之际,拥有这部辞书的读者就达一千一百万人,平均十人(两户人家)就拥有一部,这在人口只有中国十分之一的国度可谓全民性的经典读物了。现在又过了十年,统计数量应远远超过此数。
对川端康成执弟子之礼的三岛由纪夫,在日本文坛有“文学鬼才”之誉,其别具一格的美文风范,在同代作家中罕见其匹。据熟悉三岛由纪夫生平创作的研究者介绍,三岛深厚的文学功底来自少年时代所受纯正严格的语文训练,尤其是熟读辞书字典打下的牢固基础有关。三岛出身官僚家庭,从小寄养在外祖母夏子家里。夏子是受过严格教养训练的幕末家道中落的上流武家闺秀,她把光耀门楣的期待全倾注在三岛身上,为此颇煞费苦心。幼年时代三岛在祖母膝下接受启蒙,作为一项必修功课就是让他雷打不动每天捧读辞书,熟练掌握优雅、纯正的日本国语,据说在他上中学时已经能把整部《国语辞典》全背下来。步入文坛之初,三岛不同凡响的文章表现能力大受川端康成青睐,得以脱颖而出。
在一般人常识中,辞书、字典就是需要时便于翻查的工具书,当代著名女演员兼名作家神津十月小时候也是这么想,直到有机会聆听三岛由纪夫的指点,深获启蒙,才认识到所谓“常识”的肤浅。十来岁时曾向三岛请教写作秘诀:“写出好文章有秘诀吗?”三岛说:“常读辞典”。神津不解:“字典不是用来查的吗?”
“不,必须捧起来读。等到需要时才去查不管用!”三岛不容置疑答道。
为什么是“读”而不仅是“查”,三岛没有说,但神津十月记住了这句话,直到其后走上专业写作之路后才心领神会。
常读辞书字典,就像钱钟书所说的,“可以多认几个生冷的字”,“多记几个字的用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丰富词汇量,这是作家写作修炼历程的童子功。有人对古今中外作家词汇量做了统计研究显示,作家的文学成就大小很大程度上与词汇量多寡存在着有趣的对应关系,据说古今世界文豪中,莎士比亚素以词汇量恣肆汪洋著称,其全集中的词汇量高达两万四千,高居榜首,狄更斯位居第二,也有近两万多,鲁迅将近两万……词汇量的拓展,非靠长期积累不办,这其中需要长期阅读和实践的积累,辞书字典是某一语言,某一门类学科、知识的集合,长期亲近浸染心领神会功到自然成。
同时,某一特定词汇,背后往往潜藏着这一知识的相关分野,拓展开来就是某一领域知识的集合。辞书字典的最大功用之一,还在于知识面、阅读视野的拓展。辞书,尤其是举一个时代之文化实力编修的大型辞书,不仅释义准确、可靠,更在内容上具有森罗万象的丰富性以及紧跟时代的及时性。辞书没有其他读物的炫目光华,但严谨、规范、科学,另一方面,某一门类的辞书又是古今文化的集大成者,浓缩人类文化的精华,兼以每隔一定时间定期修订增补的形式追踪时代发展的步伐,一定程度上保持了语汇和知识的新鲜度。日本经典辞书种类繁多,最常见的除了《广辞苑》外,日本大型权威辞书还有三省堂的《大辞林》(已出到第三版)、小学馆出版的《大辞泉》等,均在书店里处于最醒目的位置。各种权威辞书之间风格各有侧重,各具特色,满足不同读者层的需求。像《大辞林》主要注重“当下”,尤其是在时尚服装和料理词汇的汇聚和释义上,无人能及。语言用例多采用现代文学经典作品,对于媒体网络出现的有可能传播的新词汇也不放过,同时也兼收新出现的百科知识,与时俱进的姿态,使得三省堂版辞书有“和蔼可亲的万事通”之称;岩波书店版的《广辞苑》的特色在于偏重于日本传统语言、文化的解说,几乎包含了日本古今的一切,那种将日本风土文化和文学艺术等诸领域知识一网打尽收入囊中的气派,可以说是日本文化的百科全书,最受本邦学人、作家青睐。日本笔会会长、作家井上厦念念不忘这本辞书对开拓视界的恩德:“在(《广辞苑》)二千三百页中,我觉得自己的人生都已经涵盖在中了。不,不仅是我,应该说整个日本列岛,全体日本人的生涯都被囊括其中了。”这部辞书也是我求学时代的常用工具书。到日本第二年我曾从一个即将到大阪研究生院深造的前辈那里“继承”一部半旧的《广辞苑》(第四版1991年12月版),青砖般厚重,看了就让人头皮发胀,最初置于书桌一角,更多只是当文镇使用。此前我一直用一本从国内带去的日汉词典。当时二十年前网络搜索不像今天这么便利发达,读写之际困惑重重,不得已只得时常从厚实的《广辞苑》里翻找,但久之成习就觉得它的好处,读写之际置于书案,如有博学师友在旁。此书图文并茂,释义精确凝练之外,知识性的浓度和密度也很高,尤其关于日本历史、文化、习俗的知识有时无事随便翻翻,总能看到一些有趣的词条,常常一两个小时不知不觉就过去了,词条之间又连带相关知识点的线索和索引,可以作为延伸阅读。
当今新进女作家三浦紫苑,孩提时喜欢到父亲书房里玩,瞪着好奇的眼睛把书斋里几部大字典翻得哗哗响,虽尚未识文断字,但结下了日后亲近辞书的因缘,长大后以收集、研究各种辞典为乐事。给她带来巨大声誉的小说《编舟记》,写的就是与出版社里辞书编辑部众生相:辞书编纂人的酸甜苦辣、担当和操守,也揭示其中感悟:人类知识、学问有如浩瀚的海洋,辞书就是泅渡汪洋的一叶扁舟;辞书里有真爱:无论世道如何变迁,在隔阂、冷漠和浮躁的人海里,可以凭借辞海,寻找最准确,最精炼、最有表现力的语言,超越鸿沟通向彼此心灵。因此,辞书,不是冷冰冰的语言、知识的简单堆积,而是一面千人,与活生生的人一样具有鲜明的个性和体温的存在,对社会对个体人生,兼有无上的价值,为此有人不惜付出一以贯之终生厮守的代价。此书道出了当下处于网络时代日本社会的某种境况,一出大畅其销,2012年夺得全日本书店销量桂冠奖,次年又被拍成影片拿回好几个国际电影大奖。三浦紫苑的小说和电影也在日本卷起一阵“读辞书热”,2013年由东京、大阪的大书店发起倡导“读辞书运动’,全国共有一千五百家书店积极响应参与,到去年已增加到一千九百多家。
网络触屏时代,在我国,纸质阅读似乎已经开始渐渐淡出我们的日常读览习惯,字典辞书之类的工具书也许已经成为明日黄花,成为书橱一角的摆设。常听语文教育家感叹:信息时代学生读写水准大幅度下滑,诸如别字连篇,生造乱用,把肉麻当经典,国家语文素质教育前景堪忧云云。
那么,就回到原点,引导学子从养成多用、多查、多亲近字典、辞书做起,未必不是一种可靠性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