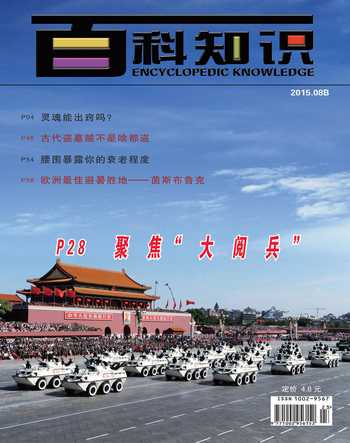天山大峡谷
刘小方

火红山谷清凉地
天山山脉自东至西横亘于新疆中部,成为南北疆草原文化与绿洲文化的分界。数列东西走向的褶皱断块山绵延2500多千米,是一处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山脉。平均海拔5000米的山体终年积雪覆盖,大小冰川横陈,构成了中国西部最宝贵的“固体水库”。基于此,酷冷的雪白成就了古人对天山的整体记忆,骆宾王诗曰“忽上天山路,依然想物化,云疑上苑叶,雪是御沟花”;岑参说“天山有雪常不开,千峰万岭雪崔嵬”;李益也感慨“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
天山逶迤南至库车段时,周身冰冷的雪白渐成炎热的火红。庞大的山体没有绿色覆盖,皆由红色砂岩、砂砾岩构成。在1亿多年的漫长岁月中,这些红色岩层在强烈上升的地质构造中断裂、弯曲、变形,加上地表径流与沙漠热风的不间断侵蚀,造就了大片光怪陆离、造型怪异的山体样貌,术语称作“雅丹地貌”。在当地,山叫“克孜利亚”,维语意为“红色的山崖”。
南疆干渴缺水,但源自“克孜利亚”山系的库车河却水量充沛,由北自南狂放流去,沿途形成树叶状冲击扇。水流之处,胡杨树高大粗壮、枝叶金黄,白杏林、葡萄园绿绿如盖,四散飘香,放眼望去尽是绿洲,这里是著名的龟兹故地、今日的石化新城库车。出县城溯流北上,蜿蜒的公路向西北是拜城,正北而行,约70千米处便是天山大峡谷。
北行的路上绿色渐淡,褐红色土石在大地上肆意展开,高耸的土石堆经风暴的剥蚀,出落成万千变化的造型。如那陡立为墙的岩层,深红、浅红的岩石层落分外清楚,真如人工炮制的夯土层;又有岩层缓倾重叠组成的孤山,在戈壁原野里兀自张望;至于那峰丛簇拥的群峰,高低起伏,百转千回,令人迷恋。沿途戈壁滩无穷尽地向远处延伸,看不到草色,偶有骆驼三两成群似在徘徊进食。
突然一个大弯,高峻的山体柔和环抱住一片阴凉而火红的山崖,一条幽深狭长的山谷向大地裂缝的纵深弯去。这峡谷宽窄相连,宽处数辆车可以并行,窄处仅容一瘦者侧身而行。谷内山影重叠,凉风习习,令人瞬间遗忘了此前的骄阳高照。脚下竟也出现汩汩溪流,那流水细小而顽强,沉淀着细沙,清而亮,掬一捧入口,沁人心脾。
步行到峡谷玉女泉,有水汽、水雾自天而落,那感觉好似在南国雁荡山的大龙湫前观瀑。此时谷底一棵小树枝叶婆娑,在那水雾和一米阳光里奋力生长;抬头仰望,红色崖壁上竟也有绿色点缀,那不知名的球状野草蓬蓬长开,或悬根于峭壁之上,或在谷隙中顽强伸出。
再往前,忽见一条铁梯从高高的崖壁上垂下,目光沿梯向上,30多米处高悬一个石洞。这是1999年才发现的唐代佛教瑰宝——阿艾石窟。龟兹是丝路文化重镇,是佛法西来的关键节点,历史遗存的佛教石窟比比皆是。从19世纪末开始,各大石窟遭到近乎疯狂的盗取,只有这隐藏在大峡谷深处、高悬于崖壁上的阿艾石窟得以独善其身直至今天。
大地裂缝里佛语呢喃
关于龟兹,《晋书·四夷传》载“龟兹国西去洛阳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可见此地佛教的发展规模。1500多年里,虔诚的佛教徒们广开佛窟以示供养之心。今天渭干河畔的克孜尔千佛洞、木扎提河边的库木吐拉石窟群、达哈尔克山口的森木塞姆石窟、汉代烽火台旁的克孜尕哈石窟等都是龟兹佛教辉煌时期的见证。
那些密集的佛窟、精美的造像,是佛法东渐中的文化印记。以克孜尔为代表的龟兹佛窟早期有鲜明的印度犍陀罗风格,菩萨、天王等造像大都高鼻深目、卷发虬髯,发丛中伸出蛇头和柔软倒卷的奇特耳朵,像极了印度教湿婆的形象;而铁线描和凹凸晕染等技法的运用则又显示了与秣菟罗(现名马图拉,印度北方邦境内的一座古城)绘画艺术千丝万缕的关联。壁画或石刻的边沿偶有文字,以龟兹时代的吐火罗文等为主。
攀着铁梯上行,纵使瞪眼细观,在这崖壁上也找不到哪怕是浅浅的石阶,或许阿艾石窟从开始修建就没有石阶,也是如此通过悬着的绳梯上下。70千米的长途跋涉,30多米的垂直高度,即使没有任何负重也会令人气喘吁吁、头晕目眩。难以想象,当年那绘图的工匠、苦修的僧侣、虔诚的供养人,是如何将信仰寄托在如此荒凉的一角。这如此僻静幽远的所在,连那些在龟兹大地上梳过、篦过的国际职业“考察队”都没有发现。若不是1999年当地一位采药青年被半山腰金黄色的麻黄草所吸引误入山洞,到今天我们仍有可能错过这处唐中期的佛教艺术宝库。
阿艾石窟不大,平面呈长方形,进深约5米左右,洞宽三四米,没有内室旁室,唯洞窟中央残存一座石质坛基,除此一览无余,空间上略感狭小。当目光一旦落在壁画上,却足以令人震惊连连。洞窟右侧的药师佛、卢舍那佛、文殊菩萨造像通体高大,法相庄严,佛像顶光色泽饱满,绿如新生的翡翠、紫若熟透的葡萄。佛手掌心朝上,或施无畏印或施吉祥印,相貌已远去克孜尔千佛洞中的中亚之风,更接近中原唐人形象。左侧上部满绘汉地风格的小坐佛,都结跏趺坐,着双领下垂式袈裟,表情严肃似已入定,佛法周围还绘有华盖、楼阁、莲花、仙鹤等物像,大都色彩鲜艳、线条流畅,造型优美。
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壁画中供养人处的大量汉字题记,例如“文殊师利菩萨似先兰为合家大小敬造”“清信佛弟子寇庭俊敬造卢舍那佛”等等,这显然是一处汉文化浓烈的佛窟,种种细节反映出这“完全是中原汉地的大乘佛教思想,具有唐代中原佛教艺术风格特征”。唐初西域设置安西都护府,后由于吐蕃与西突厥的侵袭,西域四镇主权朝夕不保。主政后的武则天力排众议,派出3万唐军精锐收复西域失地,将安西都护府重设龟兹,同时启动有规模的移民计划以稳固边疆。是当年的玄奘引入了大唐的佛法还是东来的移民带来了故土的大乘?总之,是阿艾石窟见证了佛教传播的反方向流动。
不难看出,石窟中央那残存的坛基不为佛像而设,而是为苦修者静修之用。唐代佛教已完成中国化,禅者独处山林、静坐守心已成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修持手段。远离闹市和人潮的阿艾石窟,无疑是对抗外界纷扰的理想修行之地。于高悬半空的石室,一盏禅灯如豆,间或佛语呢喃,大乘修行者追求的“便入深山中,草衣木食,养数十年,及其出来”的修禅佳境想必就是如此。
【责任编辑】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