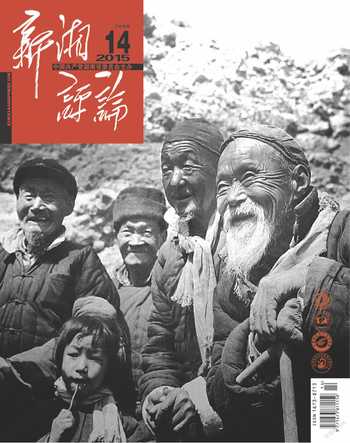喀秋莎:武器和苏联红军的代名词
郑轶
莫斯科红场阅兵仪式,《喀秋莎》的旋律是少不了的一环。我对《喀秋莎》这首歌有种莫名其妙的狂热。甚至和历史时代情怀都没有关系,单纯因为这首歌本身。常常一群年轻人在一起弹吉他唱小清新民谣时,被我欢快地一句“我们来弹《喀秋莎》吧”弄得大家面面相觑。
当然对这歌有情结的不止是我一个,很少有一首歌像《喀秋莎》那样有过无数个语言的版本,不但俄罗斯本国,甚至他们从前的敌人们也热爱这首歌,我所知道的就有超过12个语言的版本。在战争之后的漫漫岁月之中,有无数个摇滚乐团、电子乐团、DJ对它进行不断的翻唱改编。
《喀秋莎》常常被人们误认为是一首俄罗斯传统民谣,其实它是一首作曲家谱写的政治宣传歌曲。可是这些歌的意义在历史的烟尘之中早已“偏离”了它原始的面目,生长出另一个全新的自我。对于中国人来说,这首歌变成了一个浓得化不开的时代情结:对于白桦林、手风琴那个一去不复返的纯真的年代的追忆。1939年,苏联与日本在伪满洲与蒙古的边界诺门坎发生了战争,苏联桂冠诗人伊萨科夫斯基写了一首抒情诗《喀秋莎》。作曲家勃朗特尔看到这首诗歌后,马上便把它谱成了歌曲,虽然在这场战役中,苏联红军完胜日本关东军,但《喀秋莎》当时并未因战争胜利而流行开来,而是在两年之后的卫国战争中,这首歌才伴随炮火硝烟传遍了整个苏联。战后,苏联政府为了表彰《喀秋莎》这首歌在战争中所起到的巨大鼓舞作用,专为它建立了一座纪念馆,这在人类的战争史和音乐史上是首例。
然而喀秋莎究竟是什么呢?它既是俄罗斯常见的女性名字叶卡捷琳娜的爱称,也是苏联卫国战争时候一种火箭炮的名字,这个火箭炮还有一个昵称叫做“斯大林的管风琴”。
20世纪30年代末,年轻的苏联火炮设计师利昂契夫发明了一种新式火炮,由沃罗涅日州的共产国际兵工厂组织生产,取共产国际俄文第一个字母K命名并印在炮车上,并且成了德军最恐惧的武器,也就是从那以后,“喀秋莎”成为了苏联炮兵的首选武器,只要在条件允许的地方都会大量使用,甚至“喀秋莎”也成为了苏联红军的代名词。有趣的是,苏芬战争时,芬兰军队也有一种恐怖血腥的武器,同样也有一个无比温柔的名字:艾玛(Emma)。
当苏军终于攻打到柏林城下时,他们用世界上最强大的攻城臼炮轰击柏林,每一颗炮弹都有半吨重;与这些臼炮一起怒吼的,还有成千上万蔚为壮观的“喀秋莎”。
战争中爱情歌曲与爱情一样总是弥足珍贵,随着战争的深入,歌颂浪漫爱情的《喀秋莎》在世界各地传唱。在意大利,《喀秋莎》变成了《风的嘶吼》,1943年意大利人用《喀秋莎》曲调重新填了歌词,这首歌和《游击队员之歌》一起,成为意大利二战时期反法西斯最著名的歌曲,甚至比意大利的国歌更加深入人心。这首歌最好听也最著名的版本,则来自于意大利老牌乐队Moderna city ramblers,爱尔兰民谣式的配乐,前面有一段长达3分钟的solo(独奏),惊艳无比。我曾经在离法国不远的小城Cuneo看过他们的表演,几千人跟着这首歌跳舞跳疯了。其中的歌词这样唱道:“如果冷酷的死亡在我们身上降临,游击队员会为我们复仇。等待卑鄙的法西斯的命运一定是残酷的。风停了下来,暴雨也平静了,骄傲光荣的游击队员回到了家,带着他们在风中的红色旗子,至少我们自由和胜利了。”
或许人们根本不会想到,作为二战时的敌对方,日本《喀秋莎》的版本竟然是最多的,加藤登纪子的传统民谣版本非常受欢迎,她出生在二战旧时伪满洲国哈尔滨。另外,中國人熟知的《四季歌》的演唱者日本著名老牌乐队DARK DUCKS也创作了非常好听的日语版《喀秋莎》。日本之前有一部动漫《少女与战车》也把它选入主题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