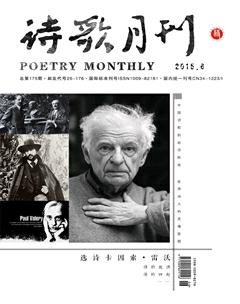禅宗佛影下的含混意象
吕维维
废名首先是一个与佛结缘的作家,他的作品早已超越了文字,达到空诸一切、心无挂碍的境地。他把佛界的圆融、空灵带到了文学作品中,达到了禅悟的境界。废名的诗最难懂,难懂的不是文字,而是文字背后的禅宗佛影。《十二月十九夜》是诗人废名的代表作,写于1936年。此诗光怪陆离,意境空灵。诗人用精炼的语言营造出拥有无限生机的虚幻美。废名引禅意入诗,诗作的意象之间没有特定的联系,缺乏逻辑,显得扑朔迷离。这种迷离感与朦胧感再加上佛家语汇的引入对读者的理解造成很大困难。但这种意象的独特连结加上禅意的贯穿,增强了全诗情感与思想的张力。我们可以尝试用英美新批评派的批评方法细读《十二月十九夜》,揭示其思维的矛盾对立和意象的幽微隐约。
在批评方法中,英美新批评派强调,一个优秀的作品必须具有复杂性和矛盾对立的包容性。这里还应当包括一首诗的辩证结构。最成功地总结了新批评派对辩证结构问题的见解的是退特的张力论。他在《诗的张力》一文中提出诗歌语言中有两个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即外延和内涵。退特提出一个完全不同的见解,他认为诗既倚重内涵,也要倚重外延,既要有丰富的联想意义,又要有概念的明晰性。如果我们只看《十二月十九夜》中意象的内涵,而将其外延抛开,那留下的只是晦涩散乱的结构。恰恰是内涵与外延的结合,让《十二月十九夜》展示出充满禅意的张力。另外,意象之间的矛盾对立、反讽、悖论、含混、张力又共同构成一个层次分明的有机整体,让整首诗彰显出无穷的艺术价值。
深夜一枝灯,
若高山流水,
有身外之海。
“深夜一枝灯”说明时间在深夜,“一枝灯”凸显孤独与寂静。从表面上看,在漆黑的屋里,空无一物,只可看到一枝明灯在闪烁,空灵与寂静随即点染全诗。结合废名研读佛经和引禅入诗的背景,我们更应将“灯”看成佛家语汇。1937年,朱光潜曾经这样评论过废名的诗:“废名先生的诗不容易懂,但是懂了之后,你也许要惊叹它真好。有些诗可以从文字本身去了解。有些诗非先了解作者不可。废名先生富敏感而好苦思,有禅家与道人的风味。他的诗有一个深玄的背景,难懂的是这背景。”
因此“灯”的外延意义可能远大于内涵意义。诗歌中无尽的张力需要我们细细挖掘。《无量寿经》说:“为世之灯明,乃人间最胜之福田。”《菩萨藏经》中也说:“百千灯明,忏悔罪。”因此在佛前点灯,是借着佛的智能之灯所放出的光明,照破我们的无明,使我们心生慧解,成就我们的智能波罗蜜。《大集经》说:“因为有许多众生心行无明愚痴,佛见了,乃教他们同修智能,令人人点燃智能之灯。”可见,灯象征着光明、智慧和幸福。因此,此处的灯乃是指引作者前进的光明之灯,也是作者的思想之灯,它象征着智慧的方向。“深夜孤灯”的意境一方面营造了空灵寂静的氛围,一方面打造了一个“冥思”的平台。
“若高山流水”一句让我们的思绪从静夜之中转移到了山水相依的自然界。这种转移似乎是突兀的,因为“深夜孤灯”与“高山流水”并无联系。其实,这正是诗的精华所在。从达摩的“壁观”修行法到六祖慧能的“无念为宗、无相为体、五住为本”,“习禅”开始由外入内。这正如诗中所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谈及此点,我们不得不提及诗佛王维的名画《雪中芭蕉》,其实它也同样体现出法在自心。《传灯录》记载过一则禅话:六源律师问慧海禅师:“和尚修道,还用功否?”师曰:“饥来吃饭,困来即眠。”六源又问:“一切人总如师用功否?”师曰:“不同,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芭蕉本是南国的产物,却与雪融合在一起,表现出异样的美感。因为在王维心中,已经没有时空的界限,时空完全变成主观化的东西。这种表面的不自然恰恰是王维主观情感的自然流露。在王维眼中,艺术创作就和“饥来吃饭,困来即眠”一样自然。
废名的诗同样脱离了时空的束缚,在心外无物的世界里游刃有余。正如废名的另外一首诗《海》:
我立在池岸
望那一朵好花,
亭亭玉立
出水妙善,——
“我将永不爱海了”
荷花微笑道:
“善男子,
花将长在你的海里。”
在这里,我们可能认为“我将永不爱海了”这句有些唐突,其实诗人已经进入禅宗的“无明”状态,后几句则表明世间花本非花,海亦非海,花海同一,爱花也是爱海。因此,从“深夜孤灯”到“高山流水”不是突兀,这恰恰反映了作者的禅心。如果我们仅从禅心的角度去看这句话,还不能够准确解读其内涵,最多只能体会作者的心境,因此我们必须借助其外延意义。倘若“高山流水”没有外延意义,那么这两种意象始终会保持孤立。“高山流水”与“深夜孤灯”一样都属于复式语象。废名在诗作中一向喜欢“用典”,并且对庾信和李商隐的用典颇有研究。“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典故似乎可以解释这个意象,借“高山流水”象征“千古知音”不无依据。深夜的一枝孤灯就是作者的知音,这枝象征着思想智慧的灯正和作者进行着情感与思维的碰撞。这深夜中唯一的知音又烘托出孤寂的气氛。
“有身外之海”一句让我们将视线转移到海上。视线转移之快,跨度之大,让人目不暇接。此句中的“海”可以解读为“人世”,正如佛家常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海”之前有一个限定词“身外”。这说明“海”在作者心中是复义的。既然有身外之海,那就会有与之对应的身内之海。如果说身外之海是除自己以外的茫茫人世,那身内之海就一定指自己广阔无边的思维与情感的世界。“深夜一枝灯,若高山流水”还是作者借着那盏智慧之灯苦思冥想,与身边的这位“知音”交换思想情感,转眼间,作者又认识到思维之外的茫茫人世。“有”字让我们感受到身外之海存在的必然性,其存在是无法抗拒的。前三行为一句,其构成一个完整的回路,深夜一枝灯在写实,闪烁的灯火让作者进入思维的空间,而后又回到身外之海的现实人世。
星之空是鸟林,
是花,是鱼,
是天上的梦,
海是夜的镜子。
“星之空是鸟林”会给人一种含混之感,让我们难以理解“星之空”与“鸟林”的联系。燕卜荪将含混分成七型,第一型为:“一物与另一物相似,但他们却有几种不同的性质都相似。”燕卜荪举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第七十三首中的句子:“荒废的唱诗坛,再不闻百鸟歌唱。”他还列举了百鸟歌唱的树林与教堂中唱诗坛的相似之处。比如教堂中有歌声,树林中也有歌声。唱诗坛被教堂建筑的墙掩着,正如树林一样。我们从表面上看星之空和鸟林,确实难以将二者关联起来。在我看来,星之空给人一种繁星闪烁的感觉,而鸟林里有着绵密的鸟群,繁密是其共同的特点。再者,在黄昏的日光下,鸟林中的小鸟就像星星一样点缀着广阔的树林。星空的广大与鸟林的广袤也有相似之处,甚至二者都可能指向“自由”。因此,不论在整体上还是局部上,两者都具备一定的相似性,我们通过联想,完全可以理解二者的共性。新批评派曾采用柯尔律治的“想象论”即“形象思维论”,把不协调的品质调和起来,把不相容的经验结合起来,正如“爱情”与“斯宾诺莎”,“打字机的声音”与“厨房的味道”。
如果说前三行构成的第一句是从思想回到现实,那第二句同样是在意识世界与现实世界徘徊。“星之空是鸟林”的上一句为“身外之海”,即现实人生,此句“星之空”在空间上与“海”相对立,表明作者又回到了思维的广阔天地。诗人的视角正如电影镜头一样,进行了一百八十度的翻转。这种空间的对立,也是作者思维的对立,更是现实视角与虚拟视角的对立。这种矛盾对立与含混使诗歌的张力倍加凸显。
“星之空”是一种虚幻,是作者思维世界的化身,它如鸟林一样广袤而充满生机,如花一样美,如鱼一样自由自在。作者接下来说那只是“天上的梦”。“是天上的梦”说明作者开始逐渐从思维世界向现实世界过渡。他已经认识到,美丽的星空只是一场梦,那并不是现实。虽然自我的精神世界是美好的、自由的,但现实还是来到了眼前。“海是夜的镜子”从表面上看,可以理解为广袤的夜空映照在海面上。对于“镜子”、“海”这些意象,废名是经常使用的,我们能够联想起废名的另外一首诗《妆台》:
因为梦里梦见我是个镜子
沉到海里他将也是个镜子
一位女郎拾去
她将放上她的妆台
因为此地是妆台
不可有悲哀
我是个镜子,镜子沉到海里,那么我也就沉到了海里,并且我坚信,那镜子一定会被女郎拾去。这种想法奇特新颖,令人费解。据张新颖考证,废名在《谈新诗》一书里收录了《妆台》,这并非出自其本意,他没有把这首诗算进他最好的几首诗之内,是林庚选的,林庚认为这首诗的基调是悲哀的,废名却认为这首诗的主调是“美”。他的理由是:“当时我忽然有一个感觉,我确实是一个镜子,而且不惜于投海,那么投了海镜子不会淹死的,正好给一女郎拾去。往下便自然吟成了。两个‘因为,非常之不能做作,来得甚有势力。‘因为此地是妆台,不可有悲哀,本是我写《桥》时的哲学,女子是不可以哭的,哭便不好看,只有小孩子哭很有趣。”
而在《十二月十九夜》中,“海”却变成了一面镜子。可见,某一个意象在废名那里并没有固定的意义,他信手拈来,为己所用。如果《妆台》透露出的只是“悲伤”,那么这首诗便失去了最起码的艺术美感,因为哀伤的诗文俯拾即是。在废名那里,艺术的美在于物我两忘,在于无明之境,在于顺其自然。“当时我忽然有一个感觉,我确实是一个镜子,而且不惜于投海”这句话正说明了,废名的诗完全是由一个自然的意念引导,而并非是做作、抒情。“往下便自然吟成了。两个‘因为,非常之不能做作,来得甚有势力。”这句话正可谓“饥来吃饭,困来即眠”,绝没有那么多陈规俗套。
在《十二月十九夜》中,“夜空”本身既然是作者思维的象征,“海”则是茫茫人生的体现。结合全诗孤寂的笔调,我们可以将此诗解读为:在茫茫人海中,我看到自己孤寂的身影。此句将作者的思绪彻底拉回到现实中。
思想是一个美人,
是家,
是日,
是月,
是灯,
是炉火,
炉火是墙上的树影,
是冬夜的声音。
第三句是诗歌的结尾部分,这一部分自然收束,沿承前两句从精神世界回归现实世界的线索。此句一开头就阐明作者的观点,即思想是一个美人。作者开始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而不像前两句那样含混与暧昧。自我的精神世界在作者的眼中是美好的,是一个美人。中国古典诗歌中常常出现“美人”意象。“美人”往往象征着诗人的理想与追求。诗中的美人又往往居住在遥远的彼岸,表明了理想之虚幻。自我的精神世界像家一样温馨,像太阳一样火热,像月光一样柔和,像灯一样富有智慧,指引着前进的方向,像炉火一样在冬日里为人提供温暖。“炉火是墙上的树影,是冬夜的声音”一句表明作者又由奇幻的精神世界回归到现实之中,即“冬夜”。作者隐约看到的所谓“炉火”原来只是墙上斑驳的树影,恍惚的“树影”再次映衬了那凄寒静寂的冬夜。作者幻想到的炉火那“噼里啪啦”的声响原来只是冬夜里零星的声音,这细微的响动又独显冬夜之静。直到最后一句,整首诗浑然天成,作者完成了第三次从精神世界向现实世界的转变,意境幽深,收束自然。
“思想”与“美人”、“家”、“日”、“月”、“灯”、“炉火”是异质的,“星之空”与“鸟林”、“花”、“鱼”、“梦”也是异质的。本体与喻体的异质性再加上隐喻的结构,使诗歌产生独特的陌生感,同时兼具禅宗佛影。“玄学派”靠远距异质,产生智力性关系的隐喻。“浪漫派”靠近距类质,产生明喻。按照新批评派学者的说法,明喻表现了浪漫主义之哕嗦与因循,而隐喻则表现了“玄学派”式的“独创和凝练”。废名的诗作正表现出这种凝练与创新。
瑞恰慈在《修辞哲学》中提到一个概念,即“语境间的交易”。比喻如果要有力,就需要把非常不同的语境联在一起。这在废名的诗作中体现得尤为突出。“深夜孤灯”与“高山流水”,“星之空”与“鸟林”、“花”、“鱼”、“梦”,“海”与“镜子”,“思想”与“美人”、“家”、“日”、“月”、“灯”、“炉火”,“炉火”与“树影”、“冬夜的声音”等,这些比喻贯穿废名的诗篇,可以说是废名使用的最为频繁的手法。约翰森指责玄学派“把异质的东西用暴力枷铐在一起”,但新批评派却对这种语言特色赞不绝口。
在我看来,废名这首诗中本体与喻体之间不但距离远,甚至完全符合伯克所说的“不相容透视”的特点。因为除去读者刻意的联想,废名所营造的意象之间的联接是完全违反逻辑的逻辑。但从整体看来,这些矛盾与含混又是诗歌无尽张力的体现,因为这些矛盾与含混最终都融入到了“孤灯长想”的总意境之中,意味深长,令人流连忘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