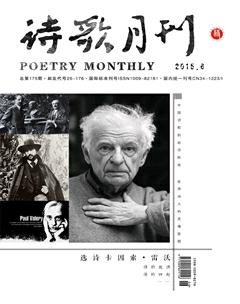“吱呀”声中拨转指针
霍俊明
将三十年间的诗,挑挑拣拣,分门别类,从岁月沉暗的抽屉里重新拿出来晾晒,让大家再次长长眼,这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自信。而对于写作的历史来说,谁都逃脱不了时间和诗学的双重“减法”。甚至这本诗选也没有收入邱华栋在新疆时期受到新边塞诗群影响的早期诗作,因为在他看来那是带有“虚假的浪漫和豪情”的。但其实也未必尽然。这显示出诗人对自我的严格要求,但“悔其少作”似乎是很多作家都难以挣脱的类似于魔咒的法则。而对于一个诗人或作家而言,早期的诗和现在的诗有时候很难一刀切开,说这一段是现在的,那一段是历史的。实际上二者更像是一条河流的关系,现在的诗歌无论风浪多大气象如何蔚然,总归有你最初源头的元素或斑驳的影子。当然对于一本诗选来说,“减法”是必然的。但要想知道三十年来邱华栋整体的“诗人形象”,他早期的诗歌也不容错过。其实,这些早期的诗很值得重读。转眼,与邱华栋相识也有十几年的光景了。据他说,我还是第一个给他的诗歌写评论的人,时间大约是在2005年的6月份。实际上,我还曾给邱华栋做过一次访谈,后来收入到2008年他出版的诗集《光之变》中。时间的深处,唯有诗歌碎片还在暗夜里闪亮,偶尔刺痛你的中年神经。
邱华栋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当代小说家,而我作为一个诗歌阅读者多年来却一直读他的诗。2005年6月在花园村读完他的《18年诗选》。此后他也经常自印“限量版”的诗歌册子。每次都是在参加文学会议的人群中迅速地塞给我。这多像当年的地下党接头!而这正是诗歌的秘密,读诗带来的是朋友间的欢娱。我认为这是兄弟间的诗歌信任。记得在2013年的春天,绍兴。江南的雨不大不小地斜落下来。在去沈园的路上,邱华栋又从怀里迅速掏出一本自己刚刚出炉的热气腾腾的诗集。一看封面,更让人期待——《情为何》。这本诗集与江南的沈园气氛如此融洽。那是一本火热而沉静的爱情诗选,那一瞬间烟雨的沈园似乎已经被邱华栋灼灼的情诗烫伤。
邱华栋曾是志得意满的少年诗人,赶上了那个火热的诗歌黄金时代。他是幸运的,这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是如此。但在我看来,这更是一种诗学的挑战。在一个风起云涌的诗歌年代,在大学生诗歌和校园诗歌以及先锋诗歌的热潮中,能坚持下来并能够获得最终认可的诗人最终也寥寥无几。而邱华栋幸运地找到了那匹鬃毛发亮的诗歌黑马。邱华栋成了懂得各种骑术且最终找到了确定了自己诗歌方向的骑手。而对于邱华栋而言,他比之其他诗人还具有另一种写作的难度和挑战。有时候,诗歌与“知识”和“阅读”之间并非是进化论式的相互促进。当然这并不是说“知识”和“阅读”对诗人和诗歌写作没有裨益,而是说其中存在的潜在危险。自古“诗有别才”“诗有别趣”,即使诗歌与“知识”有关也必然是“特殊的知识”。邱华栋是小说家中阅读西方文学最多的作家之一(也有可能可以去掉这个“之一”?),反正其阅读量惊人。甚至这种阅读差不多已经与西方的文学进行时达成了同步。华栋的家里有三个空间。一个空间是大量的书籍,一个空间是红酒,一个空间是放置的自己的诗稿和古今中外大量诗集。我能够想象深夜的时候邱华栋从外散步或约会回来,在房间里一边品着红酒一边读书一边写诗的“资产阶级高大上生活”。而大量的西方小说和文学阅读以及小说写作,对于诗歌的影响则是正负利弊多方面的。即使90年代以来诗歌界津津乐道的“叙事性”与小说的叙事也完全是两回事。况且阅读成为惯性之后很容易导致诗歌陷入到“性情”“趣味”“抒情”“吟咏”之外的套路或桎梏中去。而我重新翻检阅读邱华栋的诗歌,我之所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诗人,一个具有写作难度和个性的诗人,这完全来自于他的“诗人形象”的自我塑造。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刚才说到的他并没有坠入到“小说家诗人”的路向上去。而就是一个“诗人”在写作。这至关重要,而邱华栋深得其法。
重读这本三十年诗选,我是从后向前读完的。这样能够更清晰地回溯邱华栋诗歌的成长轨迹和自我完成的过程。“语言的敏感度”,邱华栋深谙此道。这是诗人成长和成熟最关键的所在。语言,实际上关乎诗歌整体的和全部的纹理、肌质和构架。语言不单是技巧和修辞,而是一首诗“完成度”的核心。因为语言不仅是一个诗人的表达习惯,语言还涉及到一个诗人经验、情感、想象的视域和极限。而几十年能够在书桌上摆放这张“语言敏感度”的字条并且能够在写作中践行的诗人,是可靠的。这种可靠必然是诗学层面上的。
读完三十年的诗,我最强烈的一个感受或者一个问题是,“轻型”的诗与“精神体量庞大”的诗是一种什么关系?在很多专业读者和评论者那里二者很容易被指认为两个截然的阵营。但是,邱华栋则刚好通过诗歌完成了这一诗学疑问。在邱华栋这里,他的诗歌几十年来几乎不涉及庞大和宏旨的诗歌主题,也就是在惯常意义上看来是属于“轻体量”的写作——轻小、细微、日常。但是这些诗歌却在多个层次上打通和抵达了“精神体量”的庞大。这实际上也并不是简单的“以小搏大”,而是通过一个个细小的针尖一样的点阵完成了共时体一般的震动与冲击。具体到这些诗歌,我提出更为细小的几组关键词。这些关键词不仅是来自于邱华栋的个人写作,他平衡地非常好,而且还在于这些关键词与每个诗人甚至整体性的时代写作都会有着切实的参照和启示性。这些关键词如果能够调节和践行到诗歌中,诗歌将会呈现出重要性的质素。这些关键词组是“看见”与“写出”的关系,“冥想”与“现实”的关系,“抒情”与“深度”的关系,“个人”与“历史”的关系,“细节”与“场域”的关系,“行走”与“根系”的关系,“纯诗”与“伦理”的关系,“体式”与“气象”的关系。这些关键词组实际上正好构成了一组组的诗学矛盾。也就是每一组内部都很容易成为写作上的矛盾和对抗关系。而只有优秀的诗人才能予以平衡和相互打通。当然并不是说邱华栋在每一个关键词组上都能够做到没有缺陷,而是说他的写作让我们提出了这些重要问题。
这是一个在黄昏回家的路上,透过车窗清点冬日树上鸟巢的诗人。这是清点,也必将是时间的挽歌和语言的生命“乡愁”。
也许,再过十年,三十年,这个诗人仍然会再次打开抽屉,清点那些诗歌。然后在一个清晨或黄昏,在喧闹的人群中走近我迅速从怀里抽出一本散发着温度的诗集。
201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