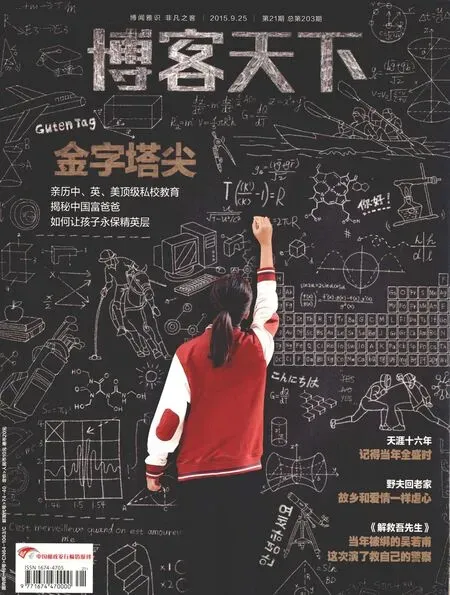桃花源记
文 Alex Halberstadt 译 萧东兮
桃花源记
文 Alex Halberstadt 译 萧东兮
为了躲避挑衅的目光与公然的歧视,一群同性恋者躲进了大山里的丛林,建造了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
几年前,美国田纳西州环境保护部门的动物学家大卫·威瑟斯(David Withers)在迪卡尔布县(DeKalb County)附近溪流的河床间研究小龙虾时,意外发现了一条没有标记的路。那本是无人问津的地方,至于这条路就更没留意过。可是那一天,他打算一探究竟,于是开着卡车前行,很快他就置身于一片奇怪的营地之中。
威瑟斯下了车。周围的几栋房子就像无法辨认的野生菌类一样,东倒西歪地散落着。引起他注意的是附近一个牲口棚,一侧刷着巨大的黄色字母“欢迎回家”(Welcome Home)。出于好奇,他走向一栋看似有人居住的简陋小屋,抬手敲门。
前来应答的女人看起来满脸惊讶。她告诉威瑟斯,他闯入了同性恋公社,并礼貌地请他离开。晚些时候,威瑟斯给他的朋友,附近卡侬县(Cannon County)的艺术中心总监、公开出柜的尼尔·阿佩尔鲍姆(Neal Appelbaum)打电话讲了自己的见闻。阿佩尔鲍姆一点也不意外,告诉他那个地方叫艾达(Ida),住着十几位LGBTQ人士(编者注:指女同性恋者Lesbian、男同性恋者Gay、双性恋者Bisexual、跨性别者Transgender及酷儿Queer,也是同性恋者的意思),而牲口棚上的字母并非“欢迎回家”,最后一个字母是“o”,不是“e”—“欢迎同性恋者”(Welcome Homo)。
如果你是LGBTQ,但年纪不超过35岁,想必不太会有和整个社会格格不入的记忆。更早一些,同性恋们的社交活动只是主要集中在几个大型沿海城市,小心躲避着公众视线。酒吧、餐厅、海滩度假屋、偏远的社区,成了他们的“避难所”。人们彼此心照不宣,大部分时候不会遭遇挑衅的目光与公然的歧视。生活在这些社区的年轻人常常将对方视作家人,因为大部分人早就脱离自己的原生家庭。但对个别人来说,这种逃避式的生活显然远远不够,不断地掩饰、伪装,就像是给出了让别人定义自己生活的通行证。于是,这类人渐渐选择远离城市,寻找不用对自己身份认同做出过多妥协的庇护所。
1979年,同性恋权利活动家、共产主义分子,来自洛杉矶的哈里·黑(Harry Hay),热切地向同性恋群体喊话—“抛弃那层模仿异性恋者的丑陋的绿色青蛙皮吧”。同时,他也是 “激进的精灵”(Radical Faeries)这场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创办人。跟提倡同性恋者要与异性恋者享有同等权利不同—比如可以结婚或者领养小孩,“激进的精灵”推崇的是同性恋者拥有独特天性,有着与异性恋者不同的使命。正是这种使命感,将他们带往美国的乡村,并逐步汇集、聚居下来,边远地区的定居点是这些“精灵”们的“圣殿”。如今地球的三块大陆上,松散地分布着十几个类似的被奉为“圣殿”的地方,但在哈里发出呼喊的那一年,“精灵”们的处女航刚刚抵达中田纳西的制高点之一—肖特山(Short Mountain)。直至今日,那里依旧是美国规模最大,历时最久,最负盛名,并吸引最多人造访的同性恋及跨性别恋者的家园。
从房屋建造的样式,放养的山羊和种植的菜园看,这里就跟课本上的公社没什么两样。可不用太多时间,你会发觉那里有个地方被命名为“变性脊”(Sex Change Ridge),而爬山道的名字是“另类摇滚”(Fruit Loop),有办事员称自己是“女皇”(Empress)—事实上,居民都按各自的喜好取了新名字。每隔两年,还会有一次历时约一周的集会。

肖特山的一对伴侣
同性恋者主要还是住在相对偏远的地方,且大多选择远离政治,而卡侬县的人则对政治抱有某种天生的狂热
在被开拓为定居点的数十年间,来自各地的人们在这里相聚又别离。尽管不时有人搬去附近不计其数的卫星村,但仍把这里当作第二个家,享受着它私密的氛围。这里的存在谈不上是个秘密,只要你在搜索引擎里敲进几个关键词不用费劲就能找到。不过,“占领华尔街”运动之后,这里的人们出于对个人身份曝光的担忧,很多与我交谈过的人都拒绝透露真实姓名。这么一来,我想就简单地把这里叫作“公社”吧。
卡侬县的每个人都知道公社。在过去36年间,大家相安无事,几乎没有发生过捣毁财物,扎破轮胎,或者用喷雾书写谩骂性话语的事。这种和平得以维持,并不是什么地方性的奇谈,或者说是自由主义思想逐渐渗入县里人头脑的原因—同性恋者主要还是住在相对偏远的地方,且大多选择远离政治,而卡侬县的人则对政治抱有某种天生的狂热。“在我们南部有种说法,每个男人都是自己城堡的国王。”县长麦克·加努恩(Mike Gannon)说,“如果你来这里只是埋头做自己的事,那么没人会来管你的。”
这里的不同党派正是如此各自埋首于自己的事务的,直到2003年。那年,阿佩尔鲍姆买下了位于伍德伯里(Woodbury)市原先属于保罗·麦尔登农场(Paul Melton farm)的土地。他是个5英尺6英寸(约168厘米)高的犹太光头男人,时年47岁,留着络腮胡,以前是注册会计师。很快,他成了全县最忙碌的开发商、地主和房产商。他相继当选县商会和工业同业会的主席,并受聘成为艺术中心主管。当地人按照南部的习惯,称他是“尼尔先生”。他几乎染指了所有县里的功能部门,毫不讳言县长加努恩在2018年任期届满后,他会投身竞选县长。在加努恩看来,阿佩尔鲍姆得胜率极大。这将会使他成为全县历史上首位非基督信仰、非异性恋、非娶女性为妻的县长,并且他或许还会是美国南部地区第一位公开同志身份的县长。
在美国,同性恋者正经历着史上最快速、最具颠覆性的变革。6月,最高法院宣布同性婚姻合法。在一派欢呼声之余,也触发了一种哀悼式的追忆。丽萨·科伦在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说:“我怀念的是身为同性恋的那种特别之处。”她是畅销书《欢乐之家》(Fun Home)的作者,还是同名百老汇音乐剧的词作者。
让我好奇的是那些住在荒郊野外,比如田纳西州的“同志们”,是否也感到了类似的失落。在远离东西海岸的中部腹地,同性恋与异性恋者会如何相处,毕竟他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分歧—虽然选择乡村生活的反社会同化的同性恋者,和他们保守的福音教会派邻居们都反对同性婚姻,但理由却天差地别。我也对公社的未来心存好奇:如果人们拥有自由来去的权利,所谓“圣殿”,对他们又意味着什么呢?
圣殿
不得不承认,同性恋者会选择卡侬县,实在奇怪极了。在肖特山陡峭的北部,有一个马厩,游客们可以在马背上端着倒满啤酒的高脚杯慢慢享用。接近山顶处,聚集着很多教堂。1万4千名居民中,拥有超过70座教堂,比例甚至超过了传统的“圣经带”(Bible Belt,美国中西部正统派教徒聚集的地带)。20%的人住的是拖车。最近一次国家电视台来这里架设播出天线是1994年,那时一个名叫“同盟退伍军人后裔”(Sons of Confederate Veterans)的组织差点说服县里答应他们在县旗上加上内战时南方联盟军旗帜的元素。
同性恋者并非最早来到肖特山的一群怪人。这里曾是非法酿酒商的根据地,茂盛的植物也在经年累月中掩盖起脾性倔强的人的踪迹,令他们免遭外人不友善的窥视。肖特山的奇特之处在于,平地就像从半球形的小山间突然冒出那样,当地人把它叫做“凸岩”,更形象的说法是,这里的地势就像热气腾腾的披萨饼上鼓起的起司泡一样,因此无论是工业还是大农场都没法在这扎根。不远处的卡侬县不时会传来几声狗叫,或者是汽车引擎回火的声响,声音在山坡间来回震荡,能传出好几英里远。
在“变性脊”得名很久以前的1973年,一群大概十几个来自加利福尼亚北部的政治激进分子从一对退休夫妇那儿买下了肖特山的一大片土地。他们呼吁停止越战,改善种族间关系,还出版了一份地下报纸。“我们听说过争取同性恋自由的运动,并且支持他们,”米洛·派恩(Milo Pyne)是那个激进政治组织最早期的成员之一,“对于性取向,这里的氛围很包容。”
没过多少年,来自西海岸的那些人就选择了离开。“有人觉得他们无法彼此忍受,有人组成了家庭,向往更稳定的生活。”派恩回忆,“但我希望这个社区能够继续存在下去,于是就四下打听其他适合来这里住的人。”
在一次前往新奥尔良(New Orleans)的旅途中,派恩(那时他的名字还叫做格思里Guthrie,如今他认为自己是双性恋者)碰到了几个同性恋。一个念头在他脑中冒了出来。他在一本同志间很流行的杂志上刊登了广告,邀请大家来肖特山。“那时,全国各地都可以嗅到一种危险逼近的气息。”派恩告诉我。在1978年,丹·怀特(Dan White)在旧金山市政厅枪杀了美国第一位公开同性恋身份的政客哈维·米尔克(Harvey Milk)。当法院裁决怀特犯下的是过失杀人罪而不是谋杀罪后,旧金山的同性恋团体洗劫了商店,掀翻了警车。
肖特山的最初几年相当艰难,好在一直有从城市来的同性恋者决定常住下去。之后,艾滋病的流行更加增添了这里的庇护色彩。有一段时间,这里几乎成了艾滋病人的收容所。“不过,在丛林里根本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医疗看护。”派恩回忆。也开始有女性搬来,成为公社的一部分,但那时是少数群体,还引发了不少争议。
1985年,派恩决定离开,谋求成为植物学家。那时的公社已经成为一块磁石,吸引着四面八方的同性恋者。“对县里很多上了年纪的人来说,肖特山上的居民从最早的嬉皮士变成后来的同性恋者,这种改变几乎察觉不到。”派恩说,“他们看到的只是那里住着一群长头发的年轻人,总在山里干一些奇怪的事。”
对绝大部分搬来这里的人来说,公社是他们第一次接触乡村生活,把这里当作思考人生各种可能性与假设的实验室。桑德尔·卡茨(Sandor Katz)在公社住了17年。他是在十几岁时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的,不久后就决定要离开城市。那是1970年代。卡茨陷入回忆:“我漫步在纽约的东村,看到一张别人扔了的缺腿的咖啡桌。我找来一个朋友,问他怎么修。那时我28岁,完全不懂怎么才能给桌子装上一条腿。”不久后,他得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那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的生活,虽然我说不清楚具体究竟是什么”。认识几个在公社住过的人,他们建议他去肖特山看看。自1993年搬来这里,卡茨就一直住到现在。
去山里住,意味着必须具备一些生存技能。卡茨后来学会了打猎、造屋、掘井、保存食物。在他53岁的时候,他懂得怎么让食物发酵,还在距公社几英里远的地方开办了工作坊。上课的地方是一间1820年代建造的农舍,就是由他修复和扩建的。“城里的男同性恋者正在成为逐渐失去技能的群体。”卡茨认为,“学习这些带有阳刚气质的技术能够给人很多能量。”他和几位朋友有时会开玩笑把公社叫做“肖特山返工进修学校”(Short Mountain Refinishing School)。

位于肖特山的一家酒厂
离开
1月底的整个纽约覆盖着灰白的积雪,笼罩在一片忧郁的气氛中。我动身前往肖特山,租来的尼桑轿车的前保险杠还在路上碰掉了。到达了伍德伯里(Woodbury)后,阿佩尔鲍姆和他的丈夫加思·霍金斯(Garth Hawkins)带我走完了通向公社的最后一段路。
如果是孤身一人,我想肯定没办法找到公社的入口,它隐蔽在山脚一条看起来危险又可疑的路边。之后,我们跟其他十几个公社居民在建于内战前的农舍里享用了素食晚餐。那里是人们的厨房,也是平时聚会的地方。我向一个穿着鼻环的女人介绍自己,当时她正在用金盏花和其他我无法辨认的植物泡茶。“你好。”她握了握我的手,“我叫‘Altercation’(有争执的意思)。”我想去厕所,有人给我指了路,到了那儿才发觉竟是个露天的四座“马桶”。就在我去厕所的路上,不知道什么活物突然在我的面前一闪而过,无边的夜色中我们距离如此之近,以致脖颈后的汗毛立刻倒竖了起来。在这里的每分钟都提醒着我不要离开城市的理由。
我是在1980年代后期,在中西部学院(Midwestern college)上学时认识阿佩尔鲍姆的。那时他就展现出了擅于解决问题的天赋,这种才能在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当中十分难得,并且他从不拒绝承担责任。毕业后,他在芝加哥住了十多年,是艾滋病联盟Act Up(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的活跃分子,开了一家回收公司,买下了自己的第一个物业,并遇见了现在的丈夫霍金斯。霍金斯如今是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的预备役成员。
渐渐地,他们越来越疲于应付城市生活,选择了搬到卡侬县。卡侬县至少同时具有两个其他地方没有的好处,首先这里有规模可观的同性恋社区,其次由于生活成本低,他们未必需要做全职工作就能应付得来。当然,这里并不完美。如果他们要买一本书,或者买一颗洋蓟菜,需要前往25英里外的默夫里斯伯勒(Murfreesboro),但对阿佩尔鲍姆和霍金斯来说,优势远远胜过了它的不便之处。
他们搬到伍德伯里不久,阿佩尔鲍姆得知一家伐木公司正在出售一大块与公社相邻的土地。当地人很担心地会卖给他们不熟的外人,以及过度伐木可能带来的危害,但没人有什么解决的方法。最终,阿佩尔鲍姆用从父亲那里借来的钱买下了535英亩(约2.2平方千米)土地,禁止森林采伐,随意架设天线,以及过度开发房地产,并把土地分成小块,以成本价卖给一些愿意在公社长期生活,但买不到或买不起公社土地的人。正因为此,他喜欢将自己称为中田纳西男同嬉皮士们的大施主。
当阿佩尔鲍姆陷入沉思时,他的额头会稍稍往后仰,手臂交叉在胸前,下颚向前伸出,从领口处露出一小撮胸毛。他的打扮看起来像夏令营指导员,说话的语气有点单调,没什么感染力。因此,当他提起邻居罗尼·蒂蒙斯(Ronnie Timmons)家的公牛挣脱了缰绳,上下蹦跳着逃去路边时,我一下竟没有搞清楚他是不是在开玩笑。但他容易情绪激动,上下挥舞的手势完全不足以流露他内心的波澜。“我不擅长上电视。”阿佩尔鲍姆说,“我没法稳稳当当地坐着超过21分钟。”
阿佩尔鲍姆对金钱的态度很特别。他相信钱在各个领域发挥的巨大影响力,并乐衷赚钱,但另一方面好像又不太在意积累财富。他痛恨任何形式的浪费。我不小心在桌子上撒到了一些咖啡,正想伸手去拿纸巾,他立刻递给了我一块海绵。
“没关系,尼尔。”霍金斯那抑扬顿挫的声音从客厅里传来,“他可以用那些纸巾的。”阿佩尔鲍姆和霍金斯住的房子,是中田纳西第一座完全使用太阳能源的房子,霍金斯的声音就在其中久久回荡着。

卡侬县的两个居民。左为服装设计师,二人身上的服饰由他设计。
房子建得很好又牢固,但楼下他们睡觉的地方用的是水泥地和夹板墙。“这房子的装修远远超出了我的需求。”我刚到那不久,阿佩尔鲍姆就这么跟我说,“你看!它简直是一座宫殿!”他开的是有些破旧的雪佛莱2000型轿车,每小时的车速不超过35英里。这种节俭风格,令宠物都感到不安。阿佩尔鲍姆只是用单个英文字母给他的猫儿们取名。在一只叫A的猫丢了、另一只叫B的猫死后,他给接着收养的两只猫分别取名C和D。在这个家里,最奢侈的东西恐怕要数那辆久保田拖拉机了。我去的那天,拖拉机正好借给了他们的邻居,安静地停放在牲口棚附近。有些时候,喜欢戴牛仔帽,穿西部样式衬衣的霍金斯会跳上拖拉机,在上面悠悠然地抽完一整根雪茄。
2006年时,这个地方再度掀起一阵波澜。药品执法管理局(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和一队郡治安官逮捕了名叫杰夫·杨(Jeff Young)的当地人,在他的物业内缴获了大量大麻,并没收了杨在肖特山的土地,很多都位于公社附近。美国法警局(US Marshals Service)决定向开发商开放竞拍这块土地,又是阿佩尔鲍姆化解了这次危机。
动物学家布瑞恩·米勒(Brian Miller)曾在附近的洞穴里发现过一些品种奇特的甲虫和火蜥蜴。得知此事后,阿佩尔鲍姆辗转打了很多电话,找到了后来误入公社的威瑟斯—或许在这个地方还能发现什么其他珍稀物种。威瑟斯在属于杨的土地上,开始挖掘一些溪流的河床,还真的找到了两种濒危物种—布劳利叉龙虾(Brawley’s Fork crayfish)和肖特山龙虾(Short Mountain crayfish),之前在科学界谁都没听说过。接下来就好办了。阿佩尔鲍姆开车拜访了联邦和州办公室的各个官员,连续向他们发去不计其数的邮件、电话和备忘录。2012年,当他们终于决定宣布将这个地方作为野生动物管理区保护起来时—田纳西州历史上第一块成为动物保护区的土地—阿佩尔鲍姆登上了国家新闻。
他做的远不止这些。此外,他买下了一些房屋,雇了一队工人翻修,把它们改造成出租屋,还设法给身无分文的公社成员找住处。即使是伍德伯里(Woodbury)这样的乡下地方,心怀慈悲的地产商人也不好找,因此阿佩尔鲍姆又设法拿到了地产经纪人执照。很快,人们在碰到问题时会想到给他打电话,他看起来也乐意解决大家的各种问题。他帮助快失明的邻居翻修了房子,帮助其他人申请医疗保险,领结婚证,甚至预约牙医……
以家庭护理工为生的约翰·格林威尔(Joh n Greenwell)在肖特山住过一段时间,在69岁时死于癌症。他给家人留下一份遗书,将25万美元遗产赠予了阿佩尔鲍姆。他把这笔钱用于建水池、道路,购买糖尿病药物,还为公社买下了另外90英亩(约0.36平方千米)土地。
谈生意的时候,阿佩尔鲍姆总会特别强调自己的同性恋身份,这种做法常常惹恼他的朋友,对手,其中也包括霍金斯。在应聘艺术中心总监时,他开诚布公地告诉招聘委员会,“我是同性恋—如果这会对你们造成困扰,请直接告诉我”。“我们都是有罪之人。”其中一个面试官回应。
2013年,阿佩尔鲍姆和霍金斯在纽约曼哈顿的市政厅登记结婚。“我要让卡侬县的每个人都知道他是我的伴侣。”阿佩尔鲍姆这么说。他的这种坦率并非每个人都买账。“尼尔从不带他的丈夫出席任何场合。当然,我也希望他最好不要那样做。”88岁的奥斯丁·简宁丝(Austin Jennings)说。她曾是国际狮子会(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总会会长,也是卡侬县的名人(霍金斯说,其实阿佩尔鲍姆去哪儿都带着自己,只不过简宁丝不认识他罢了)。“我才不在乎你是不是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女黑人政治活动家)。”伍德伯里的副市长查理·哈勒尔(Charlie Harrell)认为:“你来这里了,那么就好好干,我们会像对待别人一样对待你的。”
我与哈勒尔,还有市长帕特里克是在市议会大楼走廊尽头一间装修考究的办公室里进行这场谈话的。当被问起与公开出柜的同性恋共事有何感想时,“我不认为尼尔是同性恋”,帕特里克这么说,“他就是卡侬县的居民。”
公社的事务不再能够完全占据阿佩尔鲍姆的精力。2009年,他从当地的报纸上看到卡侬县很有可能会失去“三星地位”,这意味将流失一大笔可观的补助。卡侬县落选的主要原因是县里没有自己的网站,事实上,那里的当政者没有一个明白电脑是怎么回事。阿佩尔鲍姆让自己的朋友制作了网站,并以1000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县里。“我其实只是在这里随便转转。”他说。县长加努恩对阿佩尔鲍姆随处可见的身影并不反感,于是他来这里的次数就更多了。
“那时我一边和太太养着孩子,一边和另一个男人过着‘双重生活’,直到再也无法忍受。”布莱克说
他似乎总能找到解决各式问题的方法。县议会和本地高中需要更换取暖设备和空调,是阿佩尔鲍姆亲自填写了各种表格,从联邦政府那儿申请到了补助。“我也看过那些补助申请材料,但完全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69岁的市长帕特里说。此外,阿佩尔鲍姆还靠出售“肖特山咖啡”赚来的钱帮忙重新修整了公园里的绿植。
用阿佩尔鲍姆的话来说,他很多为人处世的方式都是从母亲多萝西·利伯曼·格鲁斯金(Dorothy Lieberman Gruskin)那儿学来的。格鲁斯金是位举止优雅的女性,在她的中年犹太女性朋友圈里有着能完美应对各种困扰的好名声。“她并不是特别吸引人,也说不上热情,但她是那种会帮离婚的朋友找公寓,帮人找工作或者谋生计的人。”阿佩尔鲍姆说,“我一直都想成为像我母亲那样的人。”在婚礼上,阿佩尔鲍姆戴了母亲的一条古董珍珠项链,当他为这篇报道拍摄时,也坚持换上了那条项链。

这是“激进的精灵”组织中的一名成员。在一次聚会中,她向上帝“献酒”
狂欢
我是个重度咖啡上瘾者以及超级宅男,因此对肖特山的生活没什么很大兴趣,但有一个疑问一直盘踞在我的脑中—在“同志骄傲大游行”如此盛行的当下,为什么还会有人成群结队跳上火车,或者开上几天几夜的车去肖特山这样的地方“朝圣”。终于,到了两年一度集会的时候,我又再次回到了那里。
在这场春季狂欢中,肖特山几乎被人潮淹没了,根本不可能把车开到公社的入口。我只能一路走着上山,置身于一片朴树和爪子树林里,粗糙的葡萄藤错综复杂,缠绕其中。当我的眼前豁然开朗,竟有一种库克船长第一眼瞥见考艾岛的冲动。
山上各种性别、年龄,身形、肤色的人都有,个个穿着奇装异服—就像在有哈利·波特历险记之前,他们就听说过有那么一个地方。草绿色的山丘上站着人身牛头怪、半机械人、魔术师,或者一些人身上只是孤零零挂着几片金属或常春藤枝蔓。一个穿着皮革装,女施虐狂打扮的人,一边牵着一只独角兽,一边和我打了招呼;一个孤独的男人坐在木头上,T恤上是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的画像;我经过两个躺在草地上的年轻人,听到他们说“……或者我们该起来给自己弄些咖啡喝。”
集会上,我无法对那些画面视而不见,对那些声音充耳不闻,但它们却没有给我留下过于深刻的印象。肖特山不像其他同性恋聚居地,这里似乎并不会向你索取什么。狂欢节上所谓的阶层—性别、种族、年龄、魅力、金钱、权利—似乎只在那几天里存在,便迅速烟消云散了。从早到晚,大家吃着东西,喝着酒,我能够想到的唯一适合描述眼下场景的词是“克制”。绝大部分穿过大半个国家来到这里的人实在太年轻了,根本不知道60、70年代是怎么回事,也不懂得公社里过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生活。
我跟一个细胳膊细腿,穿着斜粗纹棉布上衣的男人交谈起来。看样子,他年轻时应该是个帅小伙。赫克托·布莱克(Hector Black)在纽约的皇后区长大,打过二战,从哈佛大学毕业,加入过贵格会(Quakers,没有成文的教义或圣礼,直接依靠圣灵的启示指导宗教活动与社会生活,具有神秘主义特色)。他的大半辈子都投入了政治运动,同时在田纳西州的库克维尔(Cookeville)经营着一家有机农场。
据他说,自从出柜后,他每一次都参加肖特山的集会。那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
“那时我一边和太太养着孩子,一边和另一个男人过着‘双重生活’,直到再也无法忍受。”布莱克说,“我已经70岁了,从没有错过这里的任何一次集会。”
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两个20多岁,身形瘦长的年轻人经过他的身边,身上只有几块布,还抹着不少迷彩颜料。“你们叫什么名字?”布莱克问。
“我叫Artemis(阿耳特弥斯,月亮与狩猎的女神),”其中一个回答,“他是Summer(夏天)。”
“真的很高兴能够认识你们。”布莱克很有礼貌地大声回话。然后,他挥舞着手中的藤条,就像在给自己开路那样,一步一步朝肖特山下走去。■
本文由《纽约时报》资讯与版权公司授权《博客天下》使用
——基于对国内某大型形式婚姻网站征婚广告的内容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