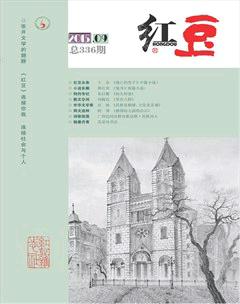错位(短篇小说)
刘益善,祖籍湖北鄂州,生在武汉江夏,中国作协会员,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长江文艺》杂志社社长、主编、编审;现任湖北省报告文学学会名誉会长、湖北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主任、《芳草潮》杂志特邀主编、武汉东湖学院驻校作家。发表小说、散文、诗歌500余万字,出版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作品20余部。组诗《我忆念的山村》获《诗刊》1981-1982优秀作品奖,纪实文学《窑工虎将》获全国青年读物奖,中篇小说《向阳湖》获湖北文学奖与汉语女评委奖,短篇小说《东天一朵云》获湖北文学奖。
墓地在村后的那面向阳的山坡上,离公路不到五十米。墓地终年都一团葱郁,柏树挺拔,山松常青。松柏浓荫掩着的大大小小的坟茔,也是绿草缠覆,野花纷开。墓地是村子的一处景致。
有夜鸟在村后呜哇一声,在床上倚靠着打盹的老五,惊得一个鲤鱼打挺地翻坐起来,用电筒照了照床边小桌上的闹钟,十二点过了二十分。老五站在黑屋里静心听了听,四处悄静,村子沉睡得好深。可以行动了,老五心里说。
老五摸着系牢鞋带,扎紧腰带,把短钎和锤子放在麻袋里裹了,手电筒揣在腰里,提了挖锄和板锹,出了自己的屋子,反手把门掩上。也不需锁,屋里没几件值钱东西。
真是个好夜晚,无明月,但有掩在云里的月光透出来,四处朦胧。看不真切,但也不是墨黑的锅底。
农历九月底了,夜里还是有股寒气,老五打了个冷战,眼睛很快适应了夜色,就快捷地朝村后墓地走去。
路是熟路,走了几十年,出了村,就见那团在夜色里的墨黑。风吹松柏飒飒有声,墨黑里透出股阴气,直朝这边飘来,老五立时感觉到了,不由得停了脚步。脚步只停了一刹,老五又朝前奔去,直对那团墨黑。妈的,胆小鬼只够格饿死。老五决不做胆小鬼。
五六分钟的时间,老五已接近了墨黑的边缘。有刷啦刷啦的声音,是一块高粱地,高粱穗子已割了,只留一地的无头秸秆,风吹叶片,刷啦刷啦不停。
“格格格……”一串女人的笑声从高粱地那边传过来。老五的头皮一炸,双腿软了,妈的,碰到女鬼了。老五吓趴在高粱地里,大气都不敢出一丝。
“珍珍,下次回来,我给你买串珍珠项链,戴在你这白颈子上,一定漂亮。”一个男人声音。
“求你了,波波,别动,别动好不好!”女人的声音,有气无力的。
接着是粗重的喘息声。“好,我不动不动!”男人的声音嘟嘟囔囔的。
妈的,真是碰到鬼了,深更半夜的,还跑到这里调情。老五松了口气,他听出那一男一女的声音是谁了。村里的两个年轻人,男的在城里建筑队当泥工,赚了些活钱。明天碰见他,敲他一包烟抽。这地方调情好,胆子也够大的,就不怕墓地的鬼么?真是色胆包了天哩!
怕鬼,我怎么不怕鬼!老五突然想。胆子这东西是靠其他东西撑大的,偷情的胆大,干我这事的胆也大。
那俩年轻人在那边干柴烈火地烧,老五这边是决不能行动的,老五就自叫晦气。趴在地里又不能乱动,老五听着年轻人的动静,就想心事。
老五也不老,过了年才四十一岁。老五好长时间没碰女人了。老五现在没有女人了,女人走了,不知到了哪里!
老五没兄弟姐妹,两岁时娘病死。爹是当娘又当爹,把老五拉扯大。娶了媳妇,爹才去世。爹本来可娶个后娘的,但怕老五受委屈,爹就打了几十年光棍。
老五在他的堂兄弟中排行第五,在他爹这房就他一根独苗,娶的媳妇没想到是个寡蛋,不生孩子。
是个老鼠也生崽,这么个大活人就是不鼓肚,每每想起来,老五就伤心。他这房不能在他这一代绝了种呀!
跟媳妇吵架,媳妇骂:“你怪我?这事怪你自己,你们屋里缺德,是个绝户头。”
老五心里火起:“个婊子养的,不生孩子还有理把责任推到我头上来了,欠揍!”
口里说欠揍,老五的拳头就挥过去了,打在了媳妇脸上。鼻子打破了,流了血,媳妇就杀猪般叫唤起来。
三个月前,媳妇就走了。丈人家、亲戚家都找了,不见了人影。有女人嫌女人,没女人想女人。有女人还是好,缝补浆洗做饭种菜,家里也热乎,单身汉的日子难呐。
那边的女人还在哼呀哼的。老五心里骂,骚狗日的们,还有完没完?别坏了老子的大事。
媳妇跑了三个月,到处无消息。有一天,在城里贩鱼的同村人告诉老五,说是有次看到买鱼的一群提篮子女人中,有一个好像是老五的媳妇。他正准备问话时,那女人掉头就走了,他也不能丢下鱼担子去追。
老五问:“是真的,你没看花眼吧?”
贩鱼的说:“千真万确!我能看花眼?笑话,称鱼时秤杆上一星一毫我都看得清,我还看不清你媳妇?”
老五就按贩鱼的说的大致方位,进城去找媳妇。
老五分析,她提篮子买鱼,很可能她在某人家里做保姆。只要是做保姆,就得买菜,我就在这买菜的女人中去找,总有一天要找到。
老五现在已经想通了,没子女就没子女吧! 中国人口太多,没子女的人又不是我一家。
老五一定要把媳妇找回,老五要对媳妇说:你别再走了,我再也不打你骂你了,要好好待你,我们俩过日子吧!我们这辈子没有孩子都行。
老五在城里找了三天,没见着媳妇的影子。老五把家里的积蓄六百多元钱带上了,白天找媳妇,夜里就在街头找个地方过夜。第四天早上,老五从一处院墙边爬起来,身上的钱都被小偷摸去了。
媳妇没找着,钱被偷光了,回家的路费也没有了。老五就去找同村的那个鱼贩子。鱼贩子见了老五,问:“找着了吗?”老五丧气地摇摇头,并向鱼贩子说了自己的钱被偷光的事,找鱼贩子借钱买车票回家。
鱼贩子说:“媳妇不找了?”
老五说:“不找了!
鱼贩子说:“你一个人,回去做么事,乡里地是没得种头了,一年种到头,还不如我贩两担鱼来得快!”
老五说:“我又没路子贩鱼,又做不了其他生意。”
鱼贩子说:“看在乡亲的分上,我给你介绍个事情,一天也能挣个五六十元的。你就在城里一边做这活路,一边找你的媳妇,好么?”
鱼贩子把老五带到江河鱼行,是一个老板经营的。一进鱼行,就有一股臭烘烘腥烘烘的味道。
鱼行老板说:“可靠么?”
鱼贩子说:“和我同村的兄弟,可靠极了。”
老五夜里再不睡街头了,而是到鱼行里上班。
老五的工作就是把一粒粒黄豆大的碎石子从鱼口里塞进去,一条鱼可塞两三粒。
老五觉得这工作是缺德,这明明是坑害人么,我老五怎么做起这种事情来了?他心里很不安。
可是,每晚工作五六个小时,下班时,老板塞给他五十元或六十元钱,老五的心就又动了。这钱可是真的,这钱也真好赚。在乡下,一担谷子也只能卖百把多元钱,我两三个夜晚就赚一担谷子。
拿了钱,就能买碗面条买只馒头吃吃,一边找媳妇,一边在城里四处逛。
逛得多了,看得多了,也就觉得这城里人赚钱也真心黑。明明看他是在这条街上买的衣服,四十元一套,他拿到另一条街上,用电喇叭叫得响响的:“快点快点,出口转内销,一百元一套,一次性处理!”
竟然就有许多人去买,一套赚六十块,老五看得目瞪口呆。
他得出了个结论:胀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乡下人胆小的多,所以受穷的就多。
晚间再去鱼行里上班,往鱼嘴里塞小石子时,老五也不觉得内疚了。他妈的,都在赚黑心钱,只苦了种田的。我这一个晚上赚五六十元钱,是劳动换来的,心安理得。
同村的鱼贩子那天一担鱼卖了好价钱,碰到老五在街头逛荡。鱼贩子问:“有影子没有?”老五只是摇头。
鱼贩子说:“我是千真万确看到了,我是不骗你的。走,跟我去喝两盅,今天高兴,你陪陪我。”
在家很小的餐馆里,鱼贩子和老五对酌起来。两盅酒下肚,鱼贩子拍拍老五的肩说:“怎么样兄弟,这不比种田好多了!种田卵子打得大胯响,能挣六十元钱?”
老五说:“这钱赚得有点不安分,心里有愧。”
“哎哟哟,你还圣人起来了。这是什么时候了,谁他妈圣人谁吃苦。假农药假化肥假种子,我们种田的上当还少了?一条鱼塞两把石子,也骗他们一下,不应该?”
老五喝了几盅酒了,想了想,觉得也该。他妈的,那些骗人的人,也该受点骗,要不,就不公平。
那是个晴天,老五从鱼行里出来,口袋里已经有好几百元的票子了。他在小馆子里吃了两碗热干面,就又在街上转悠起来。媳妇他妈的跑哪儿去了?怎么再不上街来买鱼呢!只要你在这个城市里,我总有一天要把你寻到的。老五这么想着,不觉间就逛进了一条窄街。
窄街很窄,不通汽车,两边摆的都是摊子,中间仅够自行车推着来往。窄街上的人不很多,也不很少。没有吵吵嚷嚷的,蹲在地摊跟前的人,多是干部和知识分子模样的,他们和老板轻言细语聊着,文明得很。
老五就情不自禁地走进窄街,蹲在一个地摊跟前看稀奇。摊主是个老头,胡子一大把,可那双眼睛好亮灼。摊子是一块长方形塑料布铺地,上面摆着缺了口的碗,断了把的壶,还有黑黢黢的铁罐子烂铜钱。更可笑的是,有两块青砖,三片烂瓦,一个瓷烧的菩萨。就那菩萨还完整,老五想,这摆的是什么摊子?这也有人买么?
再看附近的摊子,嗬,都是这些玩意,跟老头子摊子上的东西差不多。而且每个摊子跟前都有人在谈。
一个穿着西装头上没头发的男人,提只亮晃晃的黑皮箱,在老头摊子边停下来,然后蹲下。
老头说:“要点什么?”
那光头男人没作声,把那堆烂铜钱扒了扒,挑了几个出来,拿在手里细看了看,又从西装里拿出只有把的圆镜子照着看了看。完了,光头男人把铜钱放在手心里掂了掂。
老头说:“真正的汉代古钱。”
那光头男人说:“出价吧!”
老头说:“你是识货的,我不多要,五枚钱五百元。”
光头男人就掏出五张一百元面值的人民币递过去,抓了铜钱就走。
老五呆了,这破烂铜钱这么值钱啦,买了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城里人真是有些怪。
老头做了笔生意,颇高兴,见了老五,说:“兄弟,你要什么货?”老五摇摇头。老头又说:“你有什么货?”
老五就问:“你这摆的东西都能卖钱?”
老头说:“当然啦,不卖钱摆在这里干什么?”
老五突然想到自己的裤带上有两枚铜钱,一直缀在裤带上,是爹传下来的。老五就从腰里解下裤带。递给老头说:“这两个铜钱你要吗?”
老头看了那两枚铜钱,笑了笑说:“你这是清代的钱,不值钱,要卖,五角钱一枚。”
老五说:“你刚才卖给那光头,一百元一个呢!”
老头说:“兄弟,那叫文物。你这铜钱到处都是,贱着哩!”
老五说:“啥叫文物?”
老头就指了指地摊上的东西说,这都叫文物,都值钱呢!这条窄街,叫古玩一条街,做的都是这生意。有宝贵的文物,成交价在十万八万甚至百万元的也有。但珍贵文物,国家不让出口,那是犯法的事。”
老五就说:“你这些烂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呀?”
“收购的呀!”老头说,“大兄弟,看样子你是乡下来的,乡下有好多值钱的东西呢!比如说那古墓,里面埋着东西,很值钱的。碰得好,一个墓地有十万八万的收入。别看破罐破碗,都值钱昵!我前些天收购到一个铜尿罐,花了一万多元。”
说起古墓,老五脑子里立刻闪现出村后那片松柏掩住的坟茔。听爹说,那墓群中有一丘坟茔,是明代的一个举人的,那举人家很有钱,埋的时候肯定有不少陪葬品。
老五的脑子一闪念,立刻被老头那亮灼的眼睛捕捉到了。老头想,这庄稼汉子身上说不定有戏,就更加热情详细地对老五大谈古玩的价值。夜里去把古墓挖了,拿出里面值钱的东西,送到这条街上来,一夜成了百万元户的多着哩。那墓你不去挖,总有一天有人去挖,你不得就别人得了。见财不发不是行家。你挖了古墓,然后再填起来,谁知道哇?就是知道了又怎么样?现在有谁来管这些事情呢?
“怎么样,大兄弟,我这是教你一条发财的门路呢。如果你或是你的朋友有这类东西,可以送到这条街上来找我,我姓宋,这是我的姓名和家庭地址,咱们交个朋友。我这人是走江湖的,讲的是个义字,决不让你吃亏的。”
老头递给老五一张喷香的乳白色名片。老五忙推辞着说:“不,不,我不要!”
但老五终究还是把那喷香的名片接下来了。
呜哇呜哇,夜鸟凄厉的叫声,把在高粱地睡着了的老五叫醒了。老五摸了摸手边的麻袋包、挖锄和板锹,立即明白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了。
老五听了听,高粱地那边已没了男人的喘息和女人的哼哼声。这两个狗日的过足瘾回村去了,个婊子养的,硬是耽误老子这么长时间。幸亏夜鸟叫醒了我,要不我还要睡到明天天亮。
老五站起身,穿过高粱地,碰得高粱叶子刷啦刷啦响,他直直地朝墓地的那团墨黑走过去。
一进墓地,一股阴森森的凉气扑过来,老五又打了一个寒噤。老五看到那黑暗中的一丘丘坟茔,静静地卧着,老五想,那里面都躺着人呢,不过人都已经死了,已经不能动了。老五的爹和娘都躺在这里,村子里死的人都躺在这里。老五在心里说:“各位长辈乡亲打扰了,对不起。你们不要惊慌,我老五今天来,决不碰你们一下,你们放心吧!我今天是找那个举人的,他死了几百年了,我是想借他陪葬的东西用用。别人愿出高价钱买呢,他留着埋在地里一点用也没有,不如借给我,换几个钱用,也发一回财。行吧,举人老爷。”
老五念叨着,在墓地里转了转,找到了举人的坟茔。坟茔很饱满,被青草覆盖着。这座举人的坟,村里人谁不知道?老五是闭着眼睛也能摸到的。
老五在坟头跪下,磕了三个头,然后站起身,举起挖锄,朝坟头挖下去。
呜哇!突然一声尖叫,老五吓得丢了挖锄,一屁股坐到地上。待明白又是那只夜鸟时,老五骂了句:“个婊子养的吓老子半死。”就捡了块土坷拉朝树上打去,那鸟就刷地拍着翅膀飞走了,飞起时,又呜哇地叫了一声。
老五静听四周,没一点声音。老五想,今天得抓紧点,在天亮前把事情办成,下午就可赶到窄街去找那宋老头了。宋老头看到老五提来的罐子,眼睛里的光都能烤熟鸡蛋了。这是真正的举人的东西呀,宋老头递给老五一沓沓叠一百元面值的钞票,老五就装进麻袋里。娘的,走就走了,不生蛋的鸡,该你没福气。我老五有钱,再去娶个年轻女人,能像珍珍在高粱地里那样哼哼,然后再给老五生儿子,那时多好呀!
老五胆子大起来,老五举起挖锄,挖那坟头,一锄挖下一大块土,老五越挖越有劲,嘴里还偶尔发出“嘿嘿”的叫声。村里人不会听到,公路上深夜没人,也不会发现。
挖下了一大堆土,坟头已经平了。老五放下挖锄,用大板锹把土铲开。铲完了土,老五举起挖锄又挖起来,土块一块块被翻起来,又用板锹去铲。
坟坑出现了,慢慢地凹下去,老五心里越来越激动,他好紧张啊!棺木就要出现了,举人的棺木,一定不同寻常,那是雕龙镂风的樟木棺。奇迹就要有了,举人的棺里一定有大堆的文物古玩。
挖锄“砰”的一声,碰到什么了,是棺木。老五心跳着,放下挖锄,站到坟坑里,用板锹铲土挖土,把棺材盖上的土都挖开铲光了。
老五站在棺盖上了,但他感觉到那举人的棺材并不是很大,好像就与一般人的棺材差不多。怎么回事呢?举人家难道没钱,死了睡这么小的棺材?老五小心地打开了手电筒,那棺材上既无雕龙也无镂凤,而且边缘已经朽烂了,根本就不是什么樟木。
管他呢,棺材是什么木料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棺材里的陪葬品。那金晃晃银灿灿黑乎乎的各种东西,才是老五的目标和追求,棺材有什么用?宋老头才不收棺材呢!
老五越来越激动了,他把手电筒开着,放在坟坑的一边,从麻袋里拿出短钎和锤子。老五把短钎对着棺缝,用锤子敲了敲。短钎很快就扎进了棺缝,老五握着短钎用劲一撬,棺盖动了。老五把短钎在棺盖的周围撬着锤着,棺盖终于撬起揭开了。
一股尸气扑面而来,冲得老五一阵头晕,他晃了晃,稳住了身子,眼睛随着手电筒的光,在棺材里搜寻着。
棺材里没有金晃晃银灿灿的东西,只有一堆白骨。老五喘了口气,失望地靠着土堆吐涎水。担惊受怕,熬夜下力,满怀的希望,发财的梦,难道就是这堆白骨么?难道是白干了?老五好不甘心。
老五跳到棺材中,用短钎翻动着那举人的骨头,希望在骨头里能发现点什么,哪怕是一只缺口碗、断把壶,或是一只尿壶也好呀!
老五最终还是失望了,妈的,狗屁都没有一个。这举人家的子孙真他妈的小气,老爷子死了,连一丁点的陪葬品都不给,真不像话,真是个狗日的小气鬼!是畜牲不是人!老五气得乱骂。
没有收获,老五气得用手中的锤子把那举人的骨头锤得乱糟糟的,害得老五白干一气,你这把老骨头。
老五爬出墓坑,把撬烂了的棺材盖子胡乱地盖住了墓坑,再握着板锹,把刚才挖出的一堆浮土铲到墓坑里,浮土落到棺材上啪啪直响。
墓坑很快就填平了,老五再把所有的土归拢起来,堆成一个坟堆,并依其他的坟茔模样,堆得头大尾小。坟茔堆好了,把乱乱的青草往坟上细细铺了,与其他坟茔无异。明天即使有人来,不仔细看,是看不出这坟被人挖过的。
忙完了这一切,老五出了一身臭汗。娘的,得不偿失,一无所获。老五沮丧地捡起短钎锤子,还用麻袋裹着,夹在腋下,再提起板锹挖锄,软软地悄悄地溜回村子。
推开虚掩的门,回到空空的家,老五扔了工具,疲倦极了,倒在床上就呼呼睡去。这一睡就睡到下午才醒。
老五从床上醒来,看到破闹钟已到下午四点了。老五在床上躺着没有动,脑子在回忆着什么。老五觉得自己刚才是做了个梦,梦见爹浑身血淋淋地回到家来。爹眼泪汪汪地站在老五床边,爹说:“儿呀,我把你含辛茹苦地养大,爹对得起你呀,爹省吃俭用给你娶了媳妇,让你成家了呀!你不该把爹砸得血淋淋的,没一块好肉啊!”
老五说:“爹啊,我没有打你砸你啊,你是冤枉儿子了。儿子再不孝,也不至于打爹呀!”
爹说:“我明明看见是你打的砸的,你还不承认。孩子啊,为人心要正,要走正道,做良心事,千万莫做坑害人的事情。”
老五正要说什么,爹就走了,老五也就醒了。
老五想到这梦,不知是何意思。想不清就不想了,老五就起床,烧了锅水,洗了个澡。然后再煮一碗面条,饱饱地吃一顿。
老五想,财没发,可不要把城里鱼行的工作丢了。再说,媳妇也还是要找的。乡下娶个媳妇难,如果不去找,难道白扔了不成?
第二天一早,老五就锁了大门,对隔壁堂兄弟交代了一下,说去城里找媳妇去。这回不找到就不回。老五背着只破人造革的包包,慢慢地离开村子,上了公路。老五在公路上一抬头,就看见了那一片葱葱郁郁的墓地。见了墓地,老五就想前天夜里的事。真他妈的怪,一座明代举人的墓,里面任什么都没有,还是老五没福气哟。
走着,老五想,那墓挖了后,不知堆盖得怎么样?反正只几步路,我为什么不去看看呢!
说去看就去看,老五从公路上一拐,就拐向去墓地的小路上。墓地柏树浓绿挺拔,山松摇曳,一派森森阴冷,直向老五扑来。老五不怕,老五怕就不干。
老五走过那片高粱地,进了墓地。墓地深处,有村里的放牛娃子在骑牛吹横笛,曲曲牧歌从笛孔里飘出,乡趣无穷。
老五找到那举人的坟茔,坟茔青苍苍的好饱满,头大尾小,坐北朝南,根本看不出被人挖过了的。
老五奇了,心想这不见鬼了么?我前天夜里明明挖了的,今天坟茔上的花草就长得这么茂盛了。
老五的眼睛就在坟茔堆里转悠,突然他看到一个坟茔坟土泡浮,坟草枯萎,野花零落。老五跑过去一看,立时天昏地转,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在坟前,叫了声:“爹!”
老五再没去城里,他大病一场。病好后,就安心种庄稼。不久,老五的媳妇也自己回来了。
责任编辑 练彩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