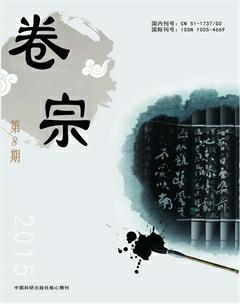扒窃入刑若干问题刍议
摘 要:扒窃犯罪在我国一直处于高发态势,且与人民群众的幸福安康密切相关,《刑法修正案(八)》已经把扒窃行为正式规定为盗窃罪的一种形式,但是就目前学界关于扒窃行为的研究现状看,还存在着很多争议之处。本文基于这些问题的启发进行讨论,从扒窃行为的涵义、行为对象等方面进行论述,以期对扒窃行为的理论研究更加全面和科学,进而为司法实务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扒窃;公共场所;随身携带
自2011年5月1日开始施行《刑法修正案八》以来,关于“扒窃”的司法适用就一直争议不断,鉴于此,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颁布了《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泛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司法解释,在该司法解释中对扒窃的概念、行为方式和犯罪的对象,以及如何认定扒窃等问题未有清晰的规定,理论界与实务界也对此充满困惑,笔者拟对扒窃的含义以及认定等问题进行系统地分析,以明晰扒窃人罪应注意的相关问题。
1 扒窃的涵义界定
关于“扒窃”的含义,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颁布的《關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泛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并未对“扒窃”进行一个清晰地解释,仅表述为“在公共场所或交通工具上盗窃他人随身携带财物的,应当认定为扒窃。”从法学理论角度看,目前学者对扒窃含义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扒窃行为是指“在公共场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趁人不备,采取不同的掩护手法,利用一定的技术手段,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1] 第二种观点认为,扒窃行为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公共场所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2]第三种观点认为,扒窃行为是指,“采用割包、掏包的方式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3]
上述这三种观点,归纳来说,主要有以下不同之处,第一,扒窃行为人在实施扒窃行为时是否需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第二,扒窃行为是否必须为秘密窃取。笔者认为关于扒窃的含义界定可以参照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理解为指在公共场所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行为,其与盗窃之间是特别和一般的关系,也就是说,扒窃是盗窃的特殊形态,所有的扒窃都属于盗窃,但盗窃不一定是扒窃,实践中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界定扒窃,一是在公共场所实施,二是窃取随身携带的财物,所谓公共场所,是指不特定人可以进入的场所以及有多数人在内的场所,如公共汽车、地铁、火车、大型商场等,关于扒窃的认定,还应注意以下几点,携带凶器不是对扒窃的必然要求,扒窃的对象不限于体积微小的财物、扒窃不要求具有技术性、惯常性、流窜性以及秘密性等。
2 对“公共场所”的界定
对于何为扒窃中的“公共场所”,目前学界对此并没有统一观点。不少学者认为,“公共场所”的特征在于人流量大并且人员组成的不特定,需要根据客观标准来判断,不能因人的主观因素将不属于“公共场所”的范围认定为“公共场所”,也不能随时间和人数的变化而改变“公共场所”应有的属性。张明楷教授认为公共场所是不特定人可以进入、停留的场所以及有多数人在内的场所,而且只要行为发生在公共场所,即使公共场所的人不是很多,也不影响扒窃的成立。例如在公共汽车上只有少数几个人时,行为人实施扒窃行为的,也应认定为盗窃罪。因此,认定“公共场所”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除了依据原有“公共场所”的概念外,还需要根据具体的场所特点具体分析。也就是说该概念应不仅仅局限于通常一般正常的普通人可以理解的公共场所的含义,如公共交通工具、大型商场、影剧院等;还应当对某些特定的场所如高校课室、企业集团大型厂区等,根据该场所的具体用途、对外开放的程度、具体进出的人数等进行具体分析,如果符合公共场所的特点,那么也应当认定为“公共场所”,而不能简单的认为相对封闭的区域如办公室、大型阶梯教室课堂、大型会议室、集体宿舍等,因人口流动性差、进出人员相对固定且互相比较熟悉,就不界定为扒窃所实施的公共场所。具体而言,扒窃犯罪所指的公共场所可以这样定义:是指不特定或者多数人能够进出的场所,它既包括公共的娱场所、商贸营业场所、集会场所等大众经常光临的场所,也应包括不特定或特定的多数人能够自由进出的场所。
3 对“随身携带的财物”的界定
如何界定“随身携带的财物”对于“扒窃入罪”具有重要意义。两高的《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泛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仅认定对随身携带的财物进行盗窃的行为构成扒窃,但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随身携带的财物”。各地司法实践对“随身携带的财物”的理解和运用存在很大争议。对何为“随身携带的财物”,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随身携带,是指放在身体上或者说是放在身体附近的物品”。[4]第二种观点认为,“扒窃行为的对象只能是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通俗地讲,应当仅限于受害人放置在身上的财物,除此之外,即使在受害人可控制范围之内的财物,如果没有放在身上,也不能称为随身携带之物”。[5]第三种观点认为,应以贴身禁忌作为扒窃行为的思想基础。“贴身禁忌,是指未经允许或者缺乏法律根据,不得侵入他人的贴身范围。”[6]
随身携带往深层次上说,实际上就是占有的一种类型,其实质就是财物所有人或占有人对自己占有的财物客观的实际支配或者客观的实际控制的一种客观事实,财物所有人或占有人对自己占有的财物可以随时支配的状态。由于“随身携带”与财物占有人对财物占有、支配状态的紧密程度有密切关系,因此,财物所有人或占有人对其财物占有、支配是否紧密以及紧密的程度如何,就成为决定其对该物是否随身携带的关键定性标准。当前就“随身携带”而言,较流行的说法是第一种观点指财物所有人或占有人对其占有的财物虽然未实际、现实的与财物所有人或占有人相接触或者附着于该财物所有人或占有人的身体上,但该财物所有人或占有人与该财物相距极近,该距离近到其可以随时用其支体直接触摸、检查、支配使用,此时即认为该财物即为财物所有人或占有人随身携带的财物。张明楷老师认为“所谓携带,是指在从事日常生活的住宅或者居室以外的场所,将某种物品带在身上或者置于身边附近,将其置于现实的支配之下的行为。笔者较为赞同第二种观点。其理由如下:首先,刑法是法律中最严厉的法律,也是人身和财产权利保障的最后 道屏障,适用时要更加严格、苛刻,不能随意使用,更盲目的扩大使用。所以,依据刑法的性质和地位,应对“随身携带的财物”进行更加严格的限制性解释。其次,普通盗窃的侵害对象是被害人具有随时支配可能性的财物,扒窃是盗窃特殊方式的一种。如果将扒窃的对象扩大为具有随时支配可能性的财物,而不是放在身上的财物,那么扒窃和普通盗窃就没有区别了。
综上,“随身携带”实际上就是对财物的实际掌控及随时支配情况的描述,应当仅限于受害人放置在身上的财物,除此之外,即使在受害人可控制范围之内的财物,如果没有放在身上,也不能称为随身携带之物。
4 结语
《刑法修正案(八)》适时的将“扒窃入罪”,这体现了我国刑法在不断的进步和发展。但是只是将“扒窃入罪”还远远不够,司法机关还需要对“扒窃”做出进一步的解释。笔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公共场所”、“随身携带的财物”的进行了解释,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建议,希望这些在司法实践中够运用,体现我国刑法的严肃性,从而能够更为有效的实现对扒窃行为的治理。
参考文献
[1]任继纯.扒窃犯罪初益论[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08(3)
[2]贾雷.论刑法修正案(八)中“扒窃”的有关认定[J].中国东盟博览,2012(1)
[3]陈兴良.口授刑法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6)
[4]李齐广.论刑法修正案(八)中”扒窃”的认定[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2012(10)
[5]张伟珂.扒窃独立成罪仍需细化[J].人民法院报,2011(4)
[6]车浩.“扒窃”入刑:贴身禁忌与行为人刑法.中国法学,2013(1)
作者简介
查洪,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刑法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