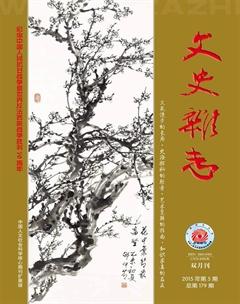1938年:何其芳在成都
易明善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何其芳于1937年8月从北京回到家乡万县。1937年9月,他应聘到四川省立万县师范学校任教。在完成了一个学期的教学工作以后,他于1938年2月初,离开万县来到成都。他的主要考虑是成都有较好的条件,较大的活动空间,也有一些熟悉的朋友,可以为宣传抗日,推动抗日文学的开展,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1938年2月初,何其芳到达成都的当天,他乘坐的汽车在抵达成都外东牛市口汽车站时,当时正在成都的两个妹妹何频伽和何曼伽,以及同乡好友吴天墀,早已等候在汽车站。吴天墀是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于是,他们就一起到吴天墀在四川大学留青院的学生宿舍休息。
何其芳到成都后的第一夜,也是在吴天墀于留青院的寝室留宿。[1]这两位同窗好友,阔别多年,现在相聚蓉城,尽兴畅谈。他们谈到了一些同学,以及家乡的近况,也谈到了有关文学问题,以及本位文化等话题,直到深夜,仍谈兴不减。2月初成都的深夜,尚有寒意,以致何其芳伤风感冒,一周后才逐渐痊愈。[2]
何其芳初到成都,兴奋不已,满怀信心,对他的蓉城岁月,充满期待。
围绕教学开展文学辅导活动
何其芳来到成都以后,应同乡好友曹葆华的介绍,到成属联中担任国文课的教学工作。成属联中是一所历史悠久的中学,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校名。当年的成属联中,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成都四中,现在的石室中学。
成属联中当时的国文课教学有着明显的保守、复古倾向。当年成属联中的一位学生曾撰文谈到国文课教学的一些情况。他说:“《国文课》就连当时政府‘锁定’课本也从不采用,而以曾国藩编的《经史百家杂抄》或姚姬传编《古文辞类纂》为自定教材,随老师的爱好在授课年级选用一种。……至于五四运动以来已普及白话文,则不屑一提。”[3]
何其芳在成属联中的国文课教学中,从内容到方法都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改革。在教学内容方面,他选讲了鲁迅、郭沫若、茅盾、朱自清、艾青等“五四”新文学作家的作品,以及高尔基、马克·吐温、莫泊桑、都德等外国作家的作品,为学生初步了解和学习新文学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在教学方法上,他以讲授为主,辅以讨论,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一扫以前课堂上那种昏昏说教的沉闷空气,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学习气氛,给课堂教学带来了新的气象。何其芳不仅重视课堂教学的改革,同时也对作文教学进行了改进,改变了用文言写作的陈规,树立了用白话写作的新风,使作文教学也出现了新的风貌。
何其芳既重视课堂教学和作文教学的革新,也关心学生的课外阅读和写作。他对学生的课外阅读和写作给予了热情的指导和具体的帮助,使学生们扩大了阅读范围,开阔了文学视野,提高了写作能力。当年的两位学生,以感恩的心情,回忆了何其芳对他们的热心辅导和对他们产生的重要影响。一位学生说:“课外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他的周围。……我们每去找他,他无论在读书、在写作,总会立刻停下来,热情、耐心地回答我们的问题。在他的指引下,我们逐渐扩大了视野,广泛读着各家的小说、散文、诗歌和戏剧,也读译作。我们一谈起来,漫无边际,他那小小的斗室,却成了我们思想驰骋的广阔天地。”[4]另外一位学生说:“他第一次给像我这样的少年人,打开了一扇通向新文学的窗:原来在‘唐宋八大家’之外,还有着多么丰富、多么浩瀚的世界啊!于是,我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我所能找到的一切文学著作”。[5]
在何其芳的关怀和引导下,学生们不仅认真阅读作品,努力学习写作,而且还创办了自己的文学园地。低年级学生创办了发表习作的墙报;高年级学生创办了公开发行的文学刊物——《学生文艺》半月刊。低年级的一位学生说:“正是在他(指何其芳)的鼓励之下,我们普十二班的几个学生,办起了全校有史以来的第一张墙报。而我,也在墙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首诗。”[6]高年级的一位学生回忆了创办《学生文艺》半月刊的有关情况。在叙述了何其芳对他们的启发和鼓励后,他说:“就是这样朴实无华的语言,打开了我们的心灵之窗。我们突破迷信与禁锢,想写文章,发表文章,终于大胆地创刊了《学生文艺》。……何老师为它书写刊头,替我们审阅乃至修改文稿,指导编排,连校对用的符号也教给我们,而且从创刊号起,他就在这个小小的刊物上发表并不太短小的文章,每隔一期就有一篇,有时还代写‘答读者问’。”[7]何其芳对这份学生主办的文学刊物,不仅从设计、编排、出版,从文稿的选题、写作、修改,都给予了认真的指导和具体的帮助,而且还以亲自为刊物撰写文章的实际行动,对学生们开辟的这一创作园地、这一大胆的创举,给予有力的支持。他在《给〈学生文艺〉社的一封信》等文章中,对学生的文艺创作中应注意的问题,发表了精辟的意见。他简明而切实地论述了“为人生而艺术”的创作态度,“丰富的生活经验”的不断积累,以及“从比较成熟的创作和外国的名著学习”等问题的重要性;他特别强调了“在这民族解放战争进行得很剧烈的目前,凡是有良心的作者都认定文学工作同样应该以有利于抗战为前提,无论直接的或间接的。”[8]
何其芳在《学生文艺》半月刊上,还发表了《一个关于写作的附注》等文章;在另外一份也是学生创办的文艺刊物《雷雨》周刊上,发表了《给〈雷雨〉周刊社的一封信》等文章。[9]他的这些文章,针对学生文艺习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爱好文艺的青年所关心的问题,发表了中肯的意见,给予了具体的帮助。
何其芳在课堂和课外与学生们的频繁接触,使他在仅仅半年的时间,就与学生们建立了相当亲密的关系。他把学生看作自己的“同伴”。他把与学生相处,高兴地称之为“生活在比我更年青的一群中”。他满怀激情地表示,“和他们在一起就犹如和希望、和勇气、和可以互相信托而又相互鼓励的同伴在一起一样。”因此,当他所执教的毕业班的学生,提出希望他们的敬爱的老师为他们的《毕业纪念册》撰写一篇《序》时,他欣然同意,并特地把这篇长达二千多字的《序》,加上《给比我更年青的一群》的标题。在这篇《序》中,他像兄长、如朋友,满腔热情地抒发了对同学的惜别之情和良好祝愿,语重心长地写下了对同学们亲切的嘱咐和深切的希望。他写道:“走出这个学校,同学们无论到大学里去继续深造,无论到社会上去作事,都需要不断的奋斗。”同时,他还特别强调,“而在目前,在这民族解放战争还剧烈的进行着的目前,更不可忘记了我们对民族国家的责任,应该一方面充实自己,一方面发挥出所有的力量,作有利于抗战的工作。”[10]
以《工作》半月刊为阵地的抗日文学活动
何其芳在成都的本职工作,是在成属联中担任国文课的教学任务。他在教学工作之余,也进行一些文学活动。在他看来,从事文学活动,既需要一个阵地,也要有一些朋友的支持。因此,他到成都不久,就提出由朋友们共同创办一份以宣传抗战、针砭时弊为宗旨的小刊物。他的倡议得到了朋友们的赞同。在经过短暂时间的筹划,这份刊名为《工作》的半月刊就于1938年3月16日出版问世了。
《工作》半月刊,是何其芳与卞之琳、朱光潜、谢文炳、方敬等共同主办的。何其芳是刊物的实际负责人,他主持了刊物的编辑、出版、发行等各方面的工作。刊物的编辑工作,是在四川大学进行的,因为刊物的主办者多数在四川大学工作。朱光潜是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卞之琳、谢文炳、罗念生是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工作》刊名下的通讯处:“成都四川大学菊园”,就是在“皇城”内朱光潜、卞之琳、罗念生等所住的教师宿舍。
《工作》半月刊的宗旨是:宣传抗战、针砭时弊、支持正义、传播文化。刊物的内容,既有对沦陷区和作战区状况的记叙,也有对社会黑暗、丑恶现实的揭露;还有对祖国河山、风土人情的描述,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战斗性。刊物主要发表散文,包括杂文、随笔、速写、通讯等;其主要撰稿人,有何其芳、朱光潜、卞之琳、谢文炳、罗念生、沙汀、周文、陈翔鹤、陈敬容等。
何其芳在《工作》半月刊上每期都有作品发表,计有《论工作》、《论本位文化》、《万县见闻》、《论救救孩子》、《论周作人事件》、《坐人力车有感》、《论家族主义》等七篇杂文与一首诗歌《成都,让我把你摇醒》。这些杂文和诗歌,观点鲜明、内容充实、文笔犀利、语言明快,揭露了日寇汉奸的卑劣行径,抨击了破坏抗日救亡和妨碍社会进步的种种言行,赞颂了人民的伟大力量和抗战的光明前途。这些诗文,宣示了他用文学为抗战服务的决心和尝试,体现了宣传抗战、针砭时弊的主张和实践,从内容到形式都显示了一些他过去所不具有的新特色,展现了他的思想和创作的新发展。《论工作》是他发表在《工作》半月刊上的第一篇文章,鲜明地体现了他服务抗战、针砭时弊的自觉性和责任感。《论周作人事件》抨击和剖析了周作人堕落为汉奸的可耻行为及其种种原因;《论救救孩子》和《论家族主义》批判了家庭和教育中的复古倾向;《论本位主义》强调了发扬本位文化中积极、进步的传统,批判其消极、落后的内容的重要性。诗歌《成都,让我把你摇醒》,是他在写于1937年春的诗歌《云》以后,时隔近一年半后发表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与他以前的诗歌有很明显的不同,歌颂了全国人民英勇抗战的大无畏精神和必胜信念,赞扬了广大军民顽强抗战的钢铁意志及其光明前途。
《工作》半月刊是何其芳与几位朋友合办的一份小刊物,但是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同人刊物。这份刊物有明确的宗旨、共同的目标,而发表的文章,观点有所不同,文责自负。刊物的几位朋友,在对待周作人事件上有不尽相同的看法,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周作人事件在当年成都的报刊披露以后,在知识界反响颇大,认识不一。在《工作》半月刊同人中也是这样。卞之琳曾读到过有关情况。他说:“当时初传周作人在北平‘下水’,《工作》刊物同人中想法不同。有的不相信,有的主张看一看,免得绝人之路,有的惋惜。”[11]
1938年5月8日,成都的报纸刊出了周作人堕落为汉奸的新闻。在三天之后即5月11日,何其芳就撰写了观点鲜明的批判文章:《论周作人事件》。[12]卞之琳以编辑者之一的名义,为何其芳这篇文章写了四百多字的“按语”。这一措辞委婉的“按语”,首先指出:“事情既然真的做错了,扼腕而外,大加挞伐,于情于理,当然都没有什么说不过去,即使话说得过火一点,在敌忾同仇的今日,也自可以原谅。何其芳先生这一篇,写得虽然还不十分冷静,但已经与众不甚同。”“按语”最后则说:“不过研究的时候不能不慎重,不能不客观,并且我个人觉得在目前遽下断语似还嫌过早。”[13]朱光潜写了《论周作人事件》,对何其芳的文章予以质疑。他认为:“现在对于周氏施攻击或作辩护,都未免嫌过早。”他还认为,“日本人想利用他(按:指周作人),是事实。一直到现在为止,据我北平友人的来信,他还没有受利用。”[14]何其芳对朱光潜的质疑,写了《关于周作人事件的一封信》[15],作了说明和答辩。何其芳、朱光潜、卞之琳对周作人事件的看法,显然各具不同,而事实和是非,却是清楚的,当自有公论。卞之琳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也说道:“其芳感觉最锐敏,就断然发表了不留情的批判文章《论周作人事件》。不久事实证明是他对。”[16]
对成都时期文学活动的定位和评价
1938年,对于何其芳来说,是十分重要而又难忘的一年。他说:
一九三八年。那是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那是抗日战争初期汹涌澎湃的来潮激动人心、而在我的一生里又是把我划分为前后两个大不相同的人的难忘的一年。[17]
1938年的大部分时间,何其芳是在成都度过的,他2月初来到成都,8月中旬离开成都去延安。他在成都生活和工作的这半年多时间,是他一生两个大不相同的阶段中,前一个阶段即将结束,而后一个阶段就要开始的交接期,也可以说,是这两个阶段的一个界石。了解这一特定时段的有关情况,对于分析他的思想和创作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何其芳曾多次谈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对他有很大的影响。
抗战发生了。对于我抗战来到得正是时侯。它使我更勇敢。[18]
抗战来了。对于我它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我不复是一个脸色苍白的梦想者,也不复是一个怯懦的人,我已经像一个成人一样有了责任感。[19]
由于抗日爱国运动的高涨,也由于多接触到了一些社会生活,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20]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抗日爱国运动的高涨,对于何其芳来说,的确“来得正是时候”。全面抗战前一两年间,他在天津、特别是莱阳期间的生活和工作的实际感受,使他逐渐改变了以前那种幻想、苦闷、孤独的思想状态,开始面向现实,关心“人间的事情”[21],并有“走向人群,走向斗争”[22]的意愿。在他人生历程的这个重要时段,全面抗战的兴起,正好成为他的思想和创作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契机和强大动力,促使他努力适应全面抗战新形势下的新要求,紧跟时代,面向社会,力求做一些用文艺为抗战服务的工作。
何其芳在成都期间的思想和创作出现的新的变化和发展,正是他用文艺为抗战服务的鲜明起点和初步尝试。他说,那时“我的确有过用文艺去服务民族解放战争的决心和尝试”[23]。他还说,在成都写的那些作品,“从它也就可以看出一个初上战场的新兵的激动。”[24]他在这里准确地概括了当时的境况和心态。作为抗战文艺战线上的一名初上战场的新兵,他确实是极其兴奋、激动、满腔热情,投身到用文艺为抗战服务的实践中去的。他的作品,也呈现出以前所未有的现实性、战斗性的特色以及自然、朴实的风格。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初上战场的新兵,应该说这些作品,还处于尝试、探索的起步阶段。即以他的思想和创作发展历程来考察,这个时段,他尽管已经倾向进步,但是还没有走向革命,正处于他前后两个大不相同的阶段的交接期。因此,在这样一个特定时段,他的作品显然还存有一些不足或弱点,往往显得比较粗糙,不够成熟。而其中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比如,这些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文体与风格,都是他不熟悉的,还是一种初步的尝试。而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否定了过去的艺术主张和风格,而新的艺术主张和风格又还比较粗浅;强调有利于抗战、为抗战服务,但理解得还比较简单;重视作品的内容正确,力求写得通俗、朴素、自然,却忽视了必要的艺术加工和提炼,以及思想与艺术的统一。所有这些都说明,他还处于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还需要不断努力,继续前进。
何其芳在成都这半年时间的后期,对于他思想和创作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和问题,是有所察觉和认识的,而在内心深处还一度感到困惑和郁闷。他从万县来到成都,是因为万县落后、闭塞,“想在大一点的地方或者可能多做一点事情”[25]。可是,他在成都生活和工作的经历,却使他感到,这个城市竟是那样的沉闷,甚至仿佛还在沉睡。于是,他写了著名的诗歌《成都,让我把你摇醒》,来表达他的不满和希望。而就小环境而言,他在成都的一些朋友,经常一起工作和活动的“小圈子”——就以《工作》半月刊的同人和朋友来说,他的所作所为,都得不到朋友们的理解,不久还出现了不和谐的气氛,使他感到寂寞、甚至孤立,有一种“散兵游勇”之感。比如,他那篇批判周作人堕落为汉奸的文章发表以后,就引发一些风波。尽管在朋友中,有人撰文进行质疑,应是属于正常的切磋、探讨;然而,也有人却说他刻薄、火气过重;还有人劝他不要写杂文,还是写“正经的创作”,否则将成为一个“青年运动家”、“社会运动家”。[26]虽然他因此而感到困惑、郁闷和不满,但是并没有动摇他用文艺为抗战服务的决心和实践,也没有使他因此而怀疑自己选择的道路。严峻的现实和实际的体验,引发了他深切的反省和思考,使他认识到,他的生活和工作需要有一个根本的变化。他还意识到,在为抗战服务的征途中,他不是“散兵游勇”,他是有着志同道合的“伙伴”的;只不过这些“伙伴”,是“在另外一个地方”[27]。于是,他果断地作出了影响他一生的重大抉择:离开成都,奔赴延安,“去投奔一支苦战了十余年的大军”[28]。这以后,他开始与有关方面的朋友联络,安排出行事宜;同时,也作一些必要的准备,包括思想和身体方面的准备,以迎接艰苦的斗争和全新的生活。
为了锻炼身体,何其芳与一位朋友相约,每天早晨到离住地不远的少城公园去活动,主要是想学会自行车。他在学骑自行车的日子里,在公园的“射德会”茶馆,在公园附近的“新雅”饭馆,遇见的几件小事,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看见一个小姑娘带着小弟弟,因为饥饿,不敢多动,长时间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昏昏欲睡。他看见一个小女孩,把卖糖糕的掉在地上的很小一块糖糕,迅速拾起来放进嘴里。他看见在餐馆里,穿着褴褛衣服的小孩子,用一把蒲扇,给吃饭的人打扇,希望得到一两个铜板的赏赐、或者一点剩菜剩饭。他所看到这些饥饿和贫穷的现象,使他感到震撼,也引发了思考。在他离开成都前九天,即1938年8月5日,写了《杂感一则》;在到达延安后的1941年6月17日,他写了《饥饿》一文。在这两篇文章中,具体描述了上述几个孩子面临饥饿的艰难处境,抒发了他无法抑制的悲愤和激动。他写道:“我仿佛第一次看见了饥饿,它以这样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子的形象出现,反而更使我感到颤栗。……我心里像被什么堵塞着,我又是一句话也没有说。假若说那满满地堵塞着我的心的是一种还没有变成眼泪的哭泣,那就不仅仅是悲恸着人间竟像是一间地狱。”[29]他从悲愤、激动,进而从理智上思考,使他认识到,“这些现象是这种社会里必然产物。”他坚信,“由于人们努力,它们绝对有着可以消灭的可能。”[30]这些来自现实的感受,使他从中汲取了营养,提高了认识,从而更加坚定了他向往光明,奔赴延安的决心。在充分准备和妥善安排以后,他与卞之琳、沙汀夫妇一道,于1938年8月14日离开成都,途经西安等地,历时18天,行程3000里,于8月31日到达延安。[31]从此,他走向了人民,走向了革命,开启了他创作道路和人生道路上的全新征途和光辉前程。
注释:
[1]何其芳:《致吴天墀信八封》附录:吴天墀著《小记》,载《何其芳研究资料》第4期,1983年12月,万州。
[2]何其芳:《论本位文化》,载《何其芳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10月。
[3][4][7]陈见昕:《何其芳在成属联中》,载《何其芳研究资料》第4期,1983年12月,万州。
[5][6]田野:《新来的老师》,载《何其芳研究资料》第11期,1988年8月,万州。
[8]何其芳:《给〈学生文艺〉社的一封信》,载《学生文艺》半月刊第2期,1938年5月,成都。
[9]何其芳:《一个关于写作的附注》《给〈雷雨〉周刊的一封信》,分载《学生文艺》第5期,1938年7月,成都;《雷雨》周刊第1期,1938年6月,成都。
[10]何其芳:《给比我更年青年的一群》,载《川东文艺》第11期,1938年4月,万州。
[11][16]卞之琳:《何其芳与〈工作〉》,载北京《新文学史料》第1期,1983年,北京。
[12]何其芳:《论周作人事件》,载《工作》第5期,1938年5月,成都。
[13]卞之琳以《工作》半月刊编者之一的名义,为何其芳《论周作人事件》一文所写的“按语”,载《工作》第5期,1938年5月,成都。
[14]朱光潜:《再论周作人事件》,载《工作》第6期,1938年6月,成都。
[15]何其芳:《关于周作人事件的一封信》,载《何其芳文集》第2卷,1982年10月,北京。
[17]何其芳:《毛泽东之歌》,载《人民文学》1977年第9期,北京。
[18]何其芳:《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载《文艺阵地》第4卷第7期,1940年2月。
[19]何其芳:《一个平常的故事》,载《中国青年》第2卷第10期,1940年8月,延安。
[20]何其芳:《写诗的经过》,载《关于写诗和读诗》,作家出版社,1956年11月,北京。
[21]何其芳:《我和散文》,载《大公报·文艺》,1937年7月11日。
[22][25][26][27]何其芳:《一个平常的故事》,载《中国青年》第2卷第10期,1940年8月,延安。
[23][24][28]何其芳:《夜歌和白天的歌》初版后记,《星火集》后记一,均见何其芳《一个平常的故事》,陈尚哲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6月,天津。
[29]何其芳:《饥饿》,载《谷雨》创刊号,1941年11月15日。
[30]何其芳:《杂感一则》,载《文艺后防》第4期,1938年8月10日。
[31]何其芳:《从成都到延安》,载《文艺战线》创刊号,1939年2月16日。
作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教授
——兼及一类史料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