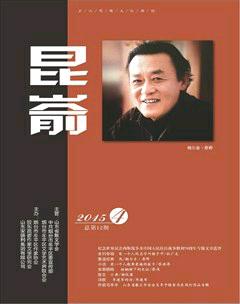异乡的天空下
(一)
微凉的秋风卷起一帘寂静,店里顾客不多。“苏州阿莲制衣”,几个新鲜的大红字,在秋阳下闪着温暖的光泽。
阿莲,是个三十来岁的江南女子,有着北方人少有的温婉外表。一双眼睛里,像是汪着江南的秋水,荡漾生辉。灰格长裙是她自己做的,再配上青葱色薄毛衫,窈窕雅致。在小城里,阿莲别具一格的美,无疑是让人耳目一新的。正像她的名字,有出水莲花般的光泽和水润,带给人美好的遐想。她应该走在江南的小巷里,袭一身自己裁剪的蓝色碎花旗袍,旖旎地自小巷深处款款而来,细细的步子轻啄着青石板,奏响一曲玲珑有致的江南小调。
她的家在苏州,她用家乡天堂一般美丽的名字,装点着自己开在遥远北方的店面,似乎也包含着无限荣耀。苏州,在北方人的印象里,有草长莺飞的风光,有吴侬软语飘在温煦的风里。
可是,她为什么要来到这干燥的北方城市?生活中总有一些无法言说的无奈,为了生存,人常常放逐自己流浪的脚步,四海为家。可不管走多远,家乡的名字,早已成为一种精神图腾,高悬着,被虔诚地放置在某一个最重要最醒目的位置上。
阿莲的一双手,也是标致极了的,仿佛电视上护手霜广告里的美手,十指纤纤,指若削葱根。这是一双巧手。她做的活,几乎挑不出瑕疵。可是,因为刚刚来,店里顾客还不多。更多的时候,阿莲安静地守在店门前,眼里扫过一丝异乡人的惆怅。
异乡人,仿佛漂游到另一个水域的水草,很难扎下根来,只能以浮游的姿态生存。
店外的阳光斜斜地落到一款素淡清爽的衣料上,浅粉色的衣料散发着温和的气息。我的手在布料上轻轻摩挲着。阿莲走过来,言笑晏晏,普通话里滑过温软细致的南方口音,似一阵和暖的风吹来。她拿过我手里的衣料,在我的肩上一披,又很专业地抖了抖,顺势一折,说:“你看,这种料子很适合你,你的皮肤白,这样把肤色衬得多好!”我看到镜子里,我的脸上有喜悦的红晕。
过了几天,我去取衣服。阿莲正和她的男人吵。两个人用极快的方言争执着,一句话也听不懂。阿莲走出来,红着眼睛说:“过几天中秋节,他吵着要回家。他回去好了,我得留下。”
冬来,呼啸的朔风抽打着枯枝,一派寒寂。阿莲的店里却暖意融融,五颜六色的衣料成衣拥挤着。店里生意越来越好了。她讲话依旧甜甜的,只是口音里已经夹杂了北方方言的味道。北方城市的色彩不经意涂抹着所有的异乡人。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人不同,人会适应环境,驾驭环境。阿莲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撑起了异乡的一方蓝天。
我以为,她终于属于这里了。可是,粗砺的北风,并没有把一切水色的记忆磨得粗糙遥远。那些漂泊而来的乡愁,一定又细又长,在心里纠结着。阿莲的脸上,开始有了一层浅浅的生活的风尘,像一朵洁白的玉兰花,沾了北方灰色的尘沙,失水一般,让人痛惜。她是属于南方的。
北方的春天,料峭而隐约,春的脚步欲来还留。一天,我看到阿莲在收拾行囊。她的眼睛里,满是激动和欣喜,仿佛被赦免的囚徒一般,青春作伴好还乡啊。她要回家了!我从她眼睛的光芒里,看到了一卷江南春意。卷轴上,飘过一行行呼唤: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现在回去,还赶得上牵上故乡的风,走遍故乡的春堤。
故乡的呼唤被风穿越,抵达千里之外。阿莲选择了乘着风的翅膀,顺着潺潺的流水,回家,回家。
(二)
小吃一条街。热闹,繁华,到处是尘烟的气息。
炸鸡店店面小得可怜。墙壁上的油污已积了厚厚一层,乌黑的,粘粘的。里面腌制好的鸡,白花花堆了一盆又一盆。屋子里昏暗逼仄,找不到一席落脚之地。但是,一点也不妨碍生意的火爆。生意是在店外进行的,炸鸡的美味足已让人们忽视这些。在小吃街上,炸鸡店外成了最热闹的景观。
油锅里“滋啦啦”的油爆声,不间断地,卖力地响着。白花花的鸡滚到汩汩的油中,立即变了颜色。一会儿,一只只黄灿灿的鸡飞出油锅,像要去高翔的雁,无限荣耀。生意太好了。顾客排起了长队,队尾的人不停翘首期盼,不时从缝隙里窥探着屋里白花花的鸡还剩多少。那些鸡,有时会因为狼多肉少早早卖光而无形中增值。店主此时便在围裙上抹一把手,咧着笑得合不拢的嘴,说:“等明天吧!”
炸鸡店店主是东北人,来了很多年了。今年,店主的儿子也来了。一个相貌有点丑的少年。十五六岁,塌鼻子,小眼睛。黑黑的脸上泛着油汪汪的光泽,像他的父亲一样。少年很聪明,很短的时间便已经学到了父亲的所有技艺。可以熟练地挥着双臂,操着漏勺,热火朝天地干上半天。他把一只只鸡放入,炸熟,捞起,称好,打包,有条不紊。少年的额头有密集的汗。脸上的青春痘更加红肿,仿佛跃跃欲试,要像他一样火火地动起来。炸好的鸡金灿灿的,看上去酥软可口。排队的顾客,有的禁不住咽起了口水。少年脸上的成就感,在油锅腾腾的热气中,忽隐忽现。
我想起了我的学生,和少年同龄的学生。他们脸色干净,在校园的木槿花下,大声与对面教学楼的同学一唱一和,对山歌一样,显得很兴奋。笑语声在花丛中穿越,青春的味道,干爽而远离尘烟。或者,他们在礼拜天把自己泡在网吧里,狂欢,毫无束缚地狂欢。再回家,睡他个天昏地暗。可炸鸡店少年的生活,已被油汪汪的炸鸡塞得满满的。
节假日,炸鸡店的生意更火了,少年更忙了。他忙碌着别人的忙碌,欢喜着别人的欢喜。我问他,想家吗?他笑起来,脸上的青春痘鼓动着。这里这么好,想家干啥。
我看着这个乐不思蜀的少年,心里豁然。原本,人都是飘飞的蒲公英,被生活的风,吹到某一个领域,从此便落地为安。
(三)
这是一家玻璃丝厂,地处郊区。常常看到一大车一大车的碎玻璃,以撕心裂肺的姿态,进入杂乱的工厂。与这些东西打交道,是件苦差事。所以,厂子里大部分都是外地人。
一家四川人,来了好几年了。厂里的人都叫他们“小四川”。他们工资微薄,租住在附近农村最简陋的平房里。有的时候,人的要求很低,解决温饱便是生活的全部。
这一家人,从来都是集体出动:男人走在前面,女人跟在后面,女人背上是幼小的女儿,他们的儿子拖着鼻涕跟在女人后面。一家人的脚步,像被线串到一起,彼此牵连。女人背女儿的方法很奇怪:背上一个红格布兜,布兜里是他们的小女儿。女人像是一只慈祥负责的母袋鼠,把孩子牢牢地拴在“育儿袋”里,从来不肯让孩子离开自己半步。这种背孩子的方法,是带有异地色彩的,常常会引来人们奇怪的目光。奇怪的目光之后,是一种轻蔑的神色。异乡人有着很多看起来怪异的习惯。
他们这个样子,几乎是一成不变的。一家人几乎没有独来独往的时候,仿佛怕自己一个人出来,会淹没在异乡的人海中,找不到回家的路。
他们常常与我擦肩而过,我向南,他们向北,奔向各自的圈子。其实,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圈子里转,渺小而卑微。他们在边缘地带,是异乡的风吹来的尘埃,落到地上,无声无息。
男人看上去总是邋里邋遢,一笑,大大的黄牙绽出来,很显眼。女人矮胖,一扭一扭跟在男人身后,像滚动的冬瓜。一家人却其乐融融,一路说笑着。一次,男人说到兴奋处,用手轻轻拍到女人头上,女人扭身,撒娇一般嘟起嘴。俩人像一对亲密的小情侣。
日子就这样过着,他们甚至把租住的小院买了下来。当然,用不了几个钱。暮晚的风,把村子里的炊烟,袅袅地缠绕在一起,不分彼此。他们,也成了村子里的一份子。他们的儿子,终于脱离了那根线,快活地蹦跳出来,和村里的孩子追闹着,玩着属于孩子的游戏。他跑得很快,欢呼雀跃着。不久,儿子和村里的孩子一样,上了一年级。
天有不测风云。一天,厂子里出了安全事故,男人死了。女人得到一笔抚恤金。
再见到女人时,是一个凄冷的冬天。大雪之后,女人自己一个人,穿着灰色的棉袄,踽踽独行。仿佛一只雪后的灰麻雀,无枝可栖身,无处可觅食。很凄凉。
没了男人,她像一只可怜的孤雁。不知她的孩子可好。
(四)
北方的冬天,天很冷了。道旁的白杨树上,还挂着几片零星的枯叶,干枯的枝桠冷冷地伸展着,分外寂寥。
他们蹲在街边,等活。面前的纸板上东倒西歪地写着大大的字:木工,油漆,水暖……等到活,他们就有着落了。要不然,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下一站在哪。他们的身体成瑟缩的姿态,人蜷成最矮,仿佛一截截矮木桩。他们的眼睛却像鱼钩一样,紧紧盯住每一个过往的行人。只要有路人的视线在他们身上停留一下,他们便会“腾”地一下站起来,满怀期待的眼神忽地亮了。有时候,我觉得他们的眼睛里有祈求的色彩,让人有悲悯之心。他们的劳动,得到的报酬是廉价的。我站在这些人中间有些左右为难,不知道该选哪一个。
他们也并不争抢生意。同样漂流在异乡,同样是这个城市里最微不足道的一个,彼此好像信守一份无言的约定。
人们分不清他们的样子,他们像城市里的道旁树一样,在飞尘里呼吸,生存,被人忽略。
他们个个静默着,却又难以掩饰无比期待的微妙心理。我走到一个人跟前,他脸上立刻堆起了笑,很僵硬的那种。他看上去那么憨厚,让人想到《天下无贼》里的傻根。我把要求说完后,他心领神会地点点头,收拾起地上的家什,像要去完成一项重大使命一样。他跟在我的后面,上楼,进门,小心翼翼。
活很少,只是一个书橱。很旧了,舍不得丢掉,因为要配合屋子里的装修,重新刷漆。他个子很矮,做起活来却精细,一丝不苟。我把茶水晾在一旁,招呼他歇歇。他羞赧地摆摆手,依旧专注地干活。他的话很少,嗯、啊,点头或者摇头摆手。可能是怕他的方言造成沟通障碍。
他干完活,熟练地收拾着工具。我把钱递到他手里时说:“快过年了,过年回家吗?”他眼睛里立刻闪出一道亮光,说:“过年要回家的,我儿子三岁了。”这是他说的最长的一句话。
他走了,悄无声息,留下几扇光滑洁净的书橱。
我从书橱最里层上抽下一本书,书里夹着我要寄给母亲的一千块钱。很久以来,我一直用这种形式关注着故乡的寒暑变迁。我不知道,母亲是否在老屋的檐下,翘首遥望,如同守望一只春归的燕。
我突然想起一句诗:在异乡的天空下,我宛如一粒流浪的沙粒,缄默里,有我藏下的三千里乡愁。
我不知道诗的作者是谁。
马亚伟,女,1976年生,中学教师,河北保定人。作品以散文随笔为主,散见于各地报刊,至今已发表500万字。《昆嵛》2013年第3期发表其散文《冬天的树》,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