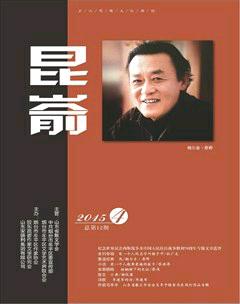爱一个人就要爱她的故乡
1
我决定去一趟陈小米的故乡。那一个名叫瓦河湾的小镇,多年来一直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我觉得我爱它甚至胜过我曾经逃离出来的故乡木镇,虽然我至今还未去过一次,但它在我无数次的想象里,已经熟悉得像在那里生活过几十年,那里的一草一木,以及陈小米小时候踏过的每一个脚印,都让我痴恋不已。
陈小米总爱傻傻地问我“爱不爱她”,这真让我无法回答。这简直就像是问我需不需要吃饭喝水一样,于是,在我决定向她求婚之前,在这个略显炎热的五月,我决定动身来一次遥远而奇特的旅行,这也足以从侧面佐证我对陈小米的热爱。我本不是个浪漫的人,但这个浪漫的想法一旦产生,就让我激动不已,我恨不得即刻启程,这也足以说明我是一个感性而易于冲动的人,但我坚信,在和陈小米恋爱乃至向她求婚这件事上,我一定是做对了。
我收拾了一个背包,特意装上陈小米从小到大的相册,还有一架刚刚买的小型DV摄像机,就匆匆上路了。我做好了一切吃苦的准备,因为据陈小米讲,从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到她遥远的故乡,先是要坐一天一夜的火车,再坐七个小时汽车,到达她们县后,还要辗转每天一趟的公交到镇上,再然后,乘坐摩的或者黑三轮到她家山前,最后再步行翻过一座大山就到了。其实,说这话的陈小米已经四年没有回乡了。自从大学毕业之后,她再也没有回去过,这固然是因为在那个遥远的地方已经没有了她要牵挂的人,父母过早的离世让她成为了无牵无挂的孤儿,更多的原因是她早就决绝地要逃离开那个被她称作“火柴盒”的小山村,因为那里,留给她的除了伤痛,还是伤痛。她是个要强的人,发誓今生要过上美好的生活,仿佛这辈子要是不能大富大贵,她就再不打算重回故乡了似的。但我知道,其实,她常常在梦中哭醒,在她最想逃离的地方,有她最深的牵挂。
我先是从地图上把那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黑点标出来,然后画了一条我将要途经的路线。我想好了,我要溯流逆行而上,从现在的地方出发,体验陈小米从故乡来到这里所走过的每一个脚印,每一个结点,从二十八岁的陈小米一直走到她的十八岁、八岁和八个月的生命隧道里去。
陈小米可以提供给我的信息不多,一本发黄陈旧的相册,藏在她抽屉的最深处,那里面隐约可以看到她的轨迹,我揣上它,将要去一个对我无比陌生但又无比亲近的地方,因为在那里,有我的爱人陈小米最熟悉的一切。一想到这些,我就无比激动,我要用相机和DV拍下每一个对于陈小米具有意义的场景和片段,我要站在陈小米曾经留影的地方,认真而全面地复原记忆,也许这将会是我献给陈小米的最珍贵最美好的求婚礼物。
2
陈小米在老家县城有一个同学,算是闺蜜。读高中的三年,两个人关系最要好,用陈小米的话说是形影不离。同学叫董雪,大陈小米一岁,家是县城棉纺厂的。父亲在啤酒厂做销售,母亲是棉纺厂的工人,家境还算不错。董雪与陈小米同桌三年,调位从未分开。周末的时候,陈小米就跟着董雪去她家住,俩人睡一个床上,你搂着我,我搂着你,亲如姐妹。董家父母看陈小米是孤儿,也十分怜爱小米,嘘寒问暖,视如己出。小米倔强,很少讲小时候的事,却常常把董雪挂在嘴边。董雪这董雪那的,说起董雪对她的好来,滔滔不绝,时间久了,弄得董雪熟悉得像我们家人似的。董雪那时候学习不如小米,高考只考了师范专科,毕业后回到县城小学,做了老师,教小学生语文。
陈小米曾说,我们结婚的时候就要董雪做伴娘。
我笑着说,那董雪漂亮不漂亮呀?我到时候可别娶错了。
她说,去你的陆昊,告诉你,人家董雪已经结婚了!她搬出她宝贝似的发黄的旧相册,从里面指出一个高高的微胖的小女孩,说,呶,她就是董雪。照片上的董雪衣着朴素,扎一个马尾巴,俏皮地和小米搂抱在一起,谈不上漂亮不漂亮。
我说,结婚的时候你没回去?
她说,那怎么可能不回去呢!
我说,我怎么不知道你去呀?
她说,老兄,那时候我还没认识你好不好?
我在两年前偶然见到陈小米,一见钟情,不能自拔。她忧郁的眼神吸引了我,现在的女孩子谁还忧郁呀?可是,陈小米漂亮的外表下,有一双略显忧郁的大眼睛,透过那一双眼睛,我仿佛看到了一颗透着微伤故事的心灵。这让我产生了一种不可遏止的想要保护她的冲动和爱怜,此后,我开始追求陈小米。半年后,她答应做我的女朋友,搬来和我住在了一起。第一次做完后,她伏在我怀里嘤嘤地哭了半天。怀抱着弱小的蜷缩的身体,我发誓这一辈子要对她好。
虽然现在火车和汽车都提速了,但绿皮火车还是咣当五个小时,充满难闻气味的汽车颠簸了三个小时,我在炎热的午后到达了陈小米老家所在的县城。
县城是个山城,很小,矮矮的房子,逼仄的街道,像一个小镇。但双脚落地,我却充满了来自体内的亲切和惊喜。要是没有陈小米,我恐怕两辈子也来不到这个地方,但有了陈小米就不一样了,仿佛这个小县城就像我的故土一般。
你是陆昊吧?一个漂亮的烫发姑娘走上来问。
你是——董雪?我吃惊地问。她与照片上的董雪完全不同,面前的这个姑娘高挑瘦削,眼睛含情。
嗯,我是董雪,有些意外吧?她笑嘻嘻地说。旁边一个男的拿着一瓶凉茶过来,递给我,接我的包。他是我老公,刘翔。董雪介绍说。
刘翔?我早听说董雪有个和著名运动员同名的老公,这让我觉得很好玩。
我伸出手,你好刘翔!我说。
你好。欢迎,欢迎。他说。
他的手很有劲,我想起来他是董雪学校里的体育老师,你别说,侧面看,他还真和刘翔长得有些像。
我央董雪给我照一张相,以车站为背景。我记得有一张照片,是八年前陈小米离开家乡去读大学时候的留影,就站在这里,和当时的情景简直一模一样。董雪替她拍的,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小字,是陈小米写上去的:
别了,我爱着恨着的故乡,我将从这里走向前方。
那是陈小米的离开宣言,虽然有些幼稚,但我可以窥见她彼时的心绪。来之前,我给董雪打电话,央她不要将我来这里的消息告诉陈小米。我说,我这次寻旧之旅,要给陈小米一个惊喜的。董雪很配合,不仅配合,而且对我的这种做法大为赞赏,她说,真羡慕小米,有你这么好的男朋友。好感人!
我说,没什么的,我只是想感受一下小米的过去,这可以让我更爱她。
她幽幽地,你可要好好对她,小米真的不容易。
我说,我会的。
董雪建议去她家,我想先去学校。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踩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感受着这里的空气和一切,仿佛陈小米就站在我的身边,那个瘦瘦的弱弱的倔强的小姑娘,她心里有许多苦和痛,我要好好爱她。
董雪想了想,说,好吧。
刘翔已经把包放进了车里,我才看见他们是开车过来的。
上了车,董雪就开始给人打电话,好像是县中学的一个老师,董雪告诉他我们很快就到了,请他带我们去学校转转。
县一中盖了崭新的大门,但里面却显得很破旧。破旧正好,我就是专程来寻旧的,要是全改成了新的,我和小米都会很难过的。
你来得算巧,当年的教学楼还在,要是明年来,老教学楼就要拆掉了。董雪说。
我庆幸我及时赶过来了。进了大门,一个年轻的男教师从一所楼里跑出来。
这是我和陈小米的同学,孙斌。现在在这里教书了。董雪说。这是陈小米的男朋友陆昊。
孙膑?我心里很诧异。想这里的名字怎么这么有趣?一个刘翔,一个孙膑。我可从来没听陈小米说过。
孙斌高高的个子,看样子有些腼腆,过来和我握手。你好,欢迎,欢迎。他说。脸有些微红。现在我很少见到会脸红的男孩子了,我马上对他有了好感。
走上三楼,随着楼梯的提升,我的心竟然激动得跳起来。这就是我爱的陈小米曾经生活过三年的地方吗?这里给了她多少苦和甜,泪和笑?她日夜在这里读书学习,那时候我在哪里呢?那一个我下决心要爱她一辈子,要娶她为妻的姑娘,要是我当年在这里陪着她,该多好。我浮想联翩,教室到了。
教室还是那个教室,但是课桌板凳已经换成了新的。只是黑板还显得很破旧。因为是周末,教室里并没有人,孙斌找人打开了教室门锁,我们一起走进去。
这里,这里,就是这里。此情此景,董雪也有些激动。她指着靠窗户的一个位置说,当年陈小米就坐在这里,她坐在她的左侧。
我坐下去,课桌上有学生摆放着的厚厚的书本和资料,坚硬的椅子,矮小的有些拥挤的桌子,我仿佛感受到了陈小米遗留下来的体温。董雪也挨着我坐下,找到了,一股酸酸甜甜的感觉涌上来,就是的,哦,小米,亲爱的。我找你来了。孙斌在我们身后的座位上坐下来,董雪说当年他就坐在陈小米的身后。
刘翔适时地为我拍下了一张照片,我翻看相机,我和董雪静静地坐在那里,像一对中学生。身后的孙斌,无辜地看着我们的背影发呆。
这里,这里,看这里。董雪突然指着我里侧的墙壁说,小米刻下的字。
我大喜,急忙低头去看,在窗户台下的水泥墙壁上,用小刀刻着陈小米三个字。落款是2005年6月。那是她们毕业高考前刻上去的,旁边好像还有两个字,已经模糊得看不清了。我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抚摸着陈小米,心里喜滋滋的。我真的好想去亲一下那三个字,我仿佛看见陈小米拙笨地拿小刀偷偷刻字的情景,她刻字是为了以后来寻找当年的印痕吗?她没有想到,这个印痕被我找到了。我拿过相机,设成微距,将这几个字连拍了好几张。
要是小米在就好了。董雪仿佛陷入了回忆。
我已经忙得快半年没有和她打电话了,我给她打个电话吧?她问我。
董雪和刘翔的孩子刚刚一岁,缠手得很,这一年多和小米联络得少了。其实,工作结婚之后,每个人都会减少和当年同学、朋友的联络的,就像我,除了现在的同事,或者偶尔在网络上找个不认识的人聊聊天,我早已经不和原来任何一个同学联络了。但我们都知道,即使半辈子不打电话不写信,那些当年一起走过青春的闺蜜和发小,只要一见面,还是亲密得如同手足。
还是别打了,我说,要不,我就白来了。这可不是我计划中的一部分。
嗯嗯,我可不能破坏你这么浪漫的计划。真让人羡慕嫉妒恨。她说。不像某些人,一点儿浪漫也没有。她看了看刘翔,鼻子里哼哼的。
刘翔转过脸去,理亏似的。这样可不好,我说,别价啊,别因为我闹得你们不愉快,我其实平时比木头还木头,我这次出来,纯粹是一次旅游。
在教室里待了一会,照了一些照片,孙斌又带着我们去校园里转了转。篮球场,单杠边,还有那个脏兮兮的小池塘,凡是陈小米走过的地方,我们又重走了一遍。一边走,我一边拍了许多照片。还拿出DV断断续续拍了一些视频。我打算回去亲手制作一个视频相册,献给陈小米,这对于我这个学计算机专业的本科生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
要是小米看到,还不得幸福死!董雪说。
到时候我们结婚,小米要你做伴娘呢。我说。
真的呀?这个小米子,我还以为把我忘了呢,哼。董雪说。
看来小米没把这打算告诉她。小米就这样,爱把事儿藏在心里。
转完了,刘翔和董雪要带我去她们家,我说还是先找个宾馆住下吧。
董雪不愿意,说,到这儿跟到家里一样。她还打算晚上把她父母一起叫过来吃饭,让他们看看陈小米找的什么样的男朋友呢。董雪说,因为陈小米父母去世早,她父母一直把陈小米当女儿看。他们还说,结婚的时候,就从家里嫁出去,他们还要配送小米一套嫁妆呢。
我听了心里热乎乎的,我来的时候就想好了,要去看看董雪的父母,他们在陈小米人生的道路上给她点燃过许多温暖的灯。这些灯也许微弱,却照亮了她内心许多角落,这才让她不至于过度的黑。
但孙斌不同意,他非要请我们吃饭不可。
那可不行,小米也是我的同学,你们来了不吃饭咋行?孙斌说。我早就定好了饭店了,还叫了几个同学,咱们晚上一块聚聚。
要不都到我家去吃?我父母说要提早过去做饭呢,就做小米当年爱吃的红烧茄子。董雪提议说。
见你爸妈也不在今天这一时呀,明天吧,明天再见。孙斌说,反正陆昊也没什么急事,就在这里多呆几天,这个小城里还有好多小米留下的痕迹呢。
既来之,则安之吧。我想。
我决定听从他们的安排,也不再和他们客气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何况我们都是陈小米那么亲密的人呢。看到他们,我就像是看到小米本人或者我自己的亲人一般,我这次出来,不就是来一个个探寻小米的足迹亲近小米的亲人朋友的么?
那天晚上,孙斌叫来了五六个同学,我们都喝高了。喝高了的他们一件一件地给我讲陈小米的“故事”,有的有趣得让我笑疼了肚子,有得又让我生出许多心疼,这一趟算是来值了,一个更加立体、鲜活的陈小米渐渐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们不说,我还真不知道呢,这些事儿,小米可是很少给我说的。
3
原来孙斌曾经喜欢过陈小米。以前我一点儿也不知道,陈小米对她之前的事儿守口如瓶。
小米太苦。孙斌喝多了,哭着说。
我搂着他,我真高兴,我知道了以前小米也有人爱过,我为她高兴。
我让董雪的老公拍下视频,永久地把这些画面珍藏。
第二天,我要去小米的老家,董雪想陪我去,我拒绝了。我要一个人去,那个归属瓦河湾镇的无名的山村,那里才有小米最初的印痕。
董雪给我画了地图,又告诉我在镇上去那个村要翻过一座大山,山里恐怕有狼。我不怕狼,当年陈小米步行去镇上读书都不怕,我怕什么呢?
县城里有一趟班车,通往瓦河湾镇,一天两趟,上午下午各一趟。车破旧得像牛车,颠簸不说,还响,吱吱哇哇,要是小米跟着,准会觉得不好意思,可我觉得很有意思,当年小米就是在这样的吱哇乱叫的破班车中考入县城一中,并飞到山外去的。
班车运行三个小时,把我抛在了一个破镇子上。我跳下车,腿脚发麻,这就是瓦河湾镇了。小米在这里读过三年初中,那时候,小米十二岁到十五岁。第一次在镇中学破败的宿舍里来了初潮,腥红的血让她发抖;第一次在这里收到了情书,落款却是匿名;第一次和人打架,抓破了男生的脸……在这里的第一次太多,小米有一次给我讲了许多,大都是小孩子的乐事糗事。那一年,初三那年,她的父母短时间内相继去世,自此之后,天降大雪,小米的世界里再没有欢乐。以后的记忆,都以痛苦的状态存在,小米绝口不提。
瓦河湾镇是一个结点,小米从此走上孤独之路。在这里的三年,小米几乎没有照过相,唯一的一张,是在镇中学运动会上,长跑得了第三名,挤在一群获奖者里面,显得那样瘦小不堪,让你根本无法相信,她还可以长跑;也无法相信,长跑得奖,她的能量来自于哪里?
我下车去镇中学拍一张照,可惜中学已经大变样了,教室成了新的,操场也成了新的,我找不到原来的位置,就在新校的大门口照相,太阳把我孤寂的影子拉得老长,阴影里是牌匾上的四个字——“瓦河湾镇中”。
不知道小米看到之后有何感慨,反正我找不到照片上一点旧痕。我不想在镇上过多停留,也不想让小米过多地看到镇上的样子,因为他的父亲就死在学校门前的马路上,一辆无牌无照的摩托将他撞飞了,除了留下一摊血和再也喊不醒的父亲,肇事黑摩托始终没有找到。小米的母亲不堪打击,本来身体就瘦弱不堪,几个月后,抑郁而死,把陈小米孤零零留给了这个世界,留给了我。
再去那个无名山村,没有了班车,道路崎岖得无法想象,像一条绳子,抛在一座大山上,绕来绕去。有黑摩的过来问我去哪里,我没有回答。我对无牌照的摩托车今生已经恨极,怎么再会去坐呢?我决定走过去,那时候,每周一次,陈小米就是用双脚走下来的,我逆流而上,踩着小米向外挣扎的脚印,一直伸进去,回到小米出生的故乡。
那里,有一年,一个叫小米的孩子出生了,现在,村子的后面,还有小米的父母的坟墓,多年之后,一个和她发生密切关系的人从遥远的城市一路追过来,试图和这里的一山一水、一坟一村发生联系,他能如愿以偿吗?
那一个叫陆昊的人,真的爱屋及乌地爱着这一片贫瘠的土地吗?
4
天色暗下去,月亮升起来。在朦胧的月光下,我摸索着走一条隔世般陌生的山路。在此之前的三十年,我绝对不会想到我一个人在夜晚会落脚这里,更不会相信我胆子大到一个人在夜色里独行山中。
但现在,我浑身洋溢着幸福。小米有一次对我说,那时候她刚读初二,周末放假时因为有事回得晚了,还未到家天就黑了。她胆子不大,但那晚并未害怕。因为,月色很好,初夏的凉风吹拂着她,让她想到了爱情。
对,是爱情。她以前从未想到过爱情的样子,但那晚给她的感觉就是有生以来的美妙。从来没有那样惬意过,她哼着歌,脚步轻盈,走了十几里山路一点也不觉得累。微风吹过她的脸,抚摸着她的头发,让她浑身酥酥的,仿佛,仿佛恋人的手掌。
那一年,她十四岁。面如春杏,眉如弯月,身上的潮汐刚刚成了朋友,小桃子般的毛茸茸的小乳尖尖的,走起路来像一只跳跃的小鹿。
她第一次想到了一个男人,或者说是一个少年。少年面目不清,但是清瘦秀气,年纪和她相仿,会用一眨不眨的眼睛看她。走在山路上,她想象着他就在她的身边,和她牵着手,默默地陪她走路,那种感觉,直到后来恋爱才真的感受到。
这就是朦胧的初恋,或者懵懂。一切都来自于想象,形而上的虚构,至多拉一下手,再也不敢往下想,但就是美味甘怡,从来没那样好过。
我说,那就是你情窦初开的一刻。天时地利人和,皎洁月色,可以让你纯净无瑕;静静山路,给你想象空间;还有初夏的山风……我告诉她,我第一次想象女人,知道女人的好,是一个夏日的午后,我在被太阳晒得发热的裸石瀑布下冲水,那一刻,我看见一个从未见过的美好的少女的身体,笑靥如花,成为我多年来的向往。
你流氓。小米笑着说,打我。形而下。她说。
后来我知道,那个女神就是你。我告诉她。
骗人。油嘴滑舌。她点评我,她真的不知道,我说的是真的。要不我怎么会对小米一见钟情,如此深情?
那个月色之夜,你身边的男子是我吗?我痴人枉问。
不知道。她说。好像比你要年轻哦。她气我。
吼吼,我那时候也很年轻啦!我比小米略大几岁,只不过,她十四岁走夜路的时候,我已在木镇读高一,比她高两级,她是师妹。只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那个夜晚,我在干啥。我是不是也一个人在夜行回家呢?
那天,她手里提着一盒小小的蛋糕。蛋糕买给爸爸和妈妈的,那天是爸爸的生日,也是妈妈的生日。她就是因为去镇上蛋糕店里买蛋糕回来晚的,她说,那天真是个好日子,和她爸爸、妈妈同一天生日的人很多,足有六七个人在那里等着小蛋糕房做生日蛋糕,这是她第一次给爸爸和妈妈买蛋糕,也是她们家第一次吃蛋糕。
身边的那个人,跟着她回家给爸爸妈妈过生日,这样的图景美不美?小米就这样痴想着,走过了几里山路,直到前面,两个人影,一束灯光,轻轻呼喊着她的名字,她才知道那是爸爸和妈妈沿着路来接她的。
傻丫头。爸爸把她抱在怀里,就像他拥她入怀。好温暖。
臭妮子,吓死我!妈妈骂她,轻轻打她一巴掌,转眼高兴地亲她。
十四年前,小米以那种方式回到这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落;十四年之后,一个与他有瓜葛的男人,独自走过同样的路。月色皎洁,初夏的风吹拂着,他也同样想到了爱情。
只不过,他身边的那个她面目清晰,叫陈小米。
只不过,直到狗吠渐起,进了山村,也没有见到那一束灯光,两个人影。
只不过,他手里提的,不是小小蛋糕,是一束康乃馨和沿途采的野菊花。
5
当晚拍开小米叔父家的门,知道我的身份后,小米的叔叔坐在那里掉泪。我也跟着掉泪。一个陌生的男人,跋涉千里,来到一个陌生的山村,坐在一个和小米有着血缘关系的男人家里,我找到了小米的根。
小米和他的叔叔有点神似,只是小米更忧郁,叔叔更苍老。婶婶张罗着做饭,嫌小米不提前打电话给她准备菜蔬,又嫌小米多年不回家了,叔叔想她想得常半夜不眠,接下来又高兴起来,夸小米找到了男朋友。
小米的婶婶和我絮絮叨叨说着小时候的小米,那时候的小米活泼可爱,冰雪聪明,学习总是名列前茅。
他最喜欢的学生。婶婶努努嘴,对着叔叔。
叔叔当年是民办教师,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小米跟着叔叔写字,春节的时候就为村上挨家挨户写春联,叔叔写,小米贴。叔叔喜欢小米,叔叔只有一个儿子,叔叔更喜欢女儿。
叔叔不说话,坐在那里,昏黄的灯光下,暗暗地,眼睛里有泪水。
我喊,叔叔。我替小米喊他,但我知道我好想喊他一声爸爸。我起身看见,墙上的相框里,那个全家福,一个比叔叔略大几岁的男人挺拔俊俏地站在那里,那是小米的爸爸。
小米和爸爸也像,干净的眼神,尤其是那一点挂在腮上的笑意。这就是遗传,这就是血脉,这就是一代一代,如果爸爸活着,我千里奔波,来到这里,和小米一起喊他“爸爸”,那该是如何幸福?
婶婶煎了鸡蛋,炒了豆角,叔叔陪我喝酒。一杯又一杯,我很快就喝醉了。喝醉了缠着叔叔给我讲小米的故事,叔叔眼圈红红的,说,有一次,小米做错了作业,我用教杆打了她的头,小米说过没有?我摇头,叔叔吱一声把酒喝了。还有一次,小米上课迟到,我为了显示大义灭亲的公正,让小米在门口站了一节课;还有,哥哥嫂嫂去世后,小米去县城读高中,我没有给她凑够学费,她自己悄悄去了血站献血,我知道后,打了她,她抱着我哭,哭完了告诉我她要走了,走了就再也不想回来了,不是因为我打她,是因为她爬回来就再也走不出去了。那一次,她两年没有回来,高中毕业,考上了大学,临走前,小米回来给爸妈烧香,让我在坟前给她照相……小米有一张相片,后来叔叔寄给她的,藏在发黄相册的夹缝里,照片上一个倔强的冷艳的姑娘,眼睛望着渺茫的未来,身后是两个高高隆起的土堆。
叔叔起身,在墙上的相框后面找出这张照片,泪水已经打湿了泥土,变成了潺潺流水的瓦河。是的,小米的院落前面就是瓦河。第二天,我去小米家旧院落,叔叔拿出钥匙半天才打开生锈的锁,推开门吱呀一声,我一脚陷进了小米的故土和记忆里。
我把每一个角落都看遍了,在铺满灰尘的小床上,还找到了小米读中学时的课本,上面是小米隽秀的字迹。我欣喜若狂,仔细地搜寻着和小米有关的蛛丝马迹。一只旧的红色塑料凉鞋,小米穿过的;一只断了腿的矮板凳,小米也一定坐过;还有一个断裂印痕的木梳子,也是小米的。我用相机和DV拍遍了老房子的每一个角落,其实,每一下闪光灯中,我都看见一个少年时候的小米。
我央叔叔找来扫帚,将院子和屋子细细打扫了一遍,随着拂去一点一点的灰尘,带有小米和她父母体温的旧家具渐渐显示出了光滑的原貌。我偷偷把那些把手亲了又亲,不知道那个时候,小米生活在这里,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把挂在墙上的老式相框里的照片小心地取出来,因为受潮,年岁日久,照片已经模糊,但是,我还可以看到当年的小米扎着小马尾,带着红发卡,笑嘻嘻地看着镜头的傻样。
我很想在这里住一夜,就在当年小米宿过的小木床上,可叔叔坚决不同意,他说,这个房子已经废弃了,下雨时开始漏雨,墙也面临垮塌,成了危房。
我让叔叔回去,自己在院子里坐了半天,快中午的时候,我按照小米以前告诉我的方位和照片的参照,到后山小米父母的坟前去。那里不远,就在屋后,只是两个大土堆已经变得很小,没有墓碑,坟堆上干干净净的,没有野草,看来小米的叔叔也常来祭扫。
我把康乃馨和野菊花摆在坟前,又把从包里带来的小蛋糕、小点心和一只烧鸡、一瓶二锅头、一支香烟摆上,今天是小米父母的生日。小米的父亲和母亲的生日是同一天,我听说后觉得真是巧合,小米却说这才是奇缘。可惜我和小米的生日不是同一天,我的生日在二月,小米的生日是九月,我好想把自己的生日也改成九月某日,但我没这个本事。
叔叔和婶婶记得小米爸妈的忌日,却不记得他们的生日。我摆好生日祭品,跪下来,点着一支烟,倒上一杯酒,和小米的父母说话。
我那天说了好多,一边说一边喝,最后已经记不清胡说了什么,只记得我磕了三个响头,石子把额头都磕破了。一只鸟儿落在坟前的枝头上,冲我叫,我听懂了,那是小米父母告诉我的,他们说——
陆昊,陈小米就托付给你了,你可要一辈子对她好!
我激动地跳起来,陈小米,你的父母已经答应了。等我回去,宝贝,等我回去,我就向你正式求婚,用这个记录我和你点点滴滴的照片和视频,要求你嫁给我,你会答应吗?
夜色笼罩上来,我趁着夜色返回。月亮皎洁,比昨夜更亮,我一个人踏上陈小米当年走出大山的路,晚风习习,朝着十几里路外的瓦河湾镇走去。
我觉得小米就跟在我的身边,我牵着她的手,搂着她的腰,每走一段路,我们就停下来接吻。我亲她的额头,亲她的头发,亲她的眼睛,亲她的耳朵和脖子,亲她的微笑和鼻子,最后,我使劲吸她的舌头。她也吸着我,两个人就那样粘合在一起。
6
我想好了,回去之后,我就从医院里把陈小米接回来,对着那个在无名摩托车祸中受伤的丧失了记忆的微笑的姑娘说,我爱她,然后,我要娶她。
乔洪涛,1980年生于山东梁山,中国民盟盟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临沂市青年作协副主席。2001年起陆续在《人民文学》《十月》《中国作家》《青年文学》《文学港》《山东文学》《长城》《作品》《百花洲》《散文》《散文选刊》等文学期刊发表作品110万字,作品多次获奖,有作品被转载和收录到多种选本。曾获天涯社区2007年“全国80后作家人气榜”提名,入围2007年腾讯网评选的“山东十大青年作家”,入围“鲁彦周文学奖”,首届《昆嵛》非虚构散文大赛策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