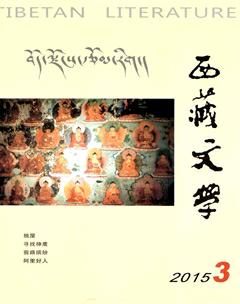独屋
金志国
我们到达旺麦村的那天,是藏历的三月十五日。那晚的月亮很圆很亮,除了月亮的基本形态外,还流溢着一股生命的气息,说不清是哀怨还是欢欣。以至过了好多年后,当我回忆起那一夜我的神秘体验时,我只能归结于那一轮巨大的、其光芒清丽无比的月亮。当时我置身在一个以往和后来的生活经验里都没有过的奇妙境地,之所以迟迟没有把它讲出来,是因为我一直在怀疑,那天晚上,在遥远的西藏东部的一座小山村里,是否真发生过这件奇特的事情。
一
我们是一支十余人组成的工作队,自认为背负着神圣的使命,从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坐着大轿车颠簸了好几天,才到了西藏东部这座小山村。
山地的白昼很短暂,刚安营扎寨完毕,夜幕就降临了。
旺麦村坐落在一条流注澜沧江的河的岸边,村舍全部拥挤在狭窄的河滩上。河的彼岸和村落所依临的山峦全被黑暗的密林覆盖着,山的顶端像刀锋般划出一道锯齿形的雪色。一轮皓洁无比的月亮正爬上东面的山巅,笼罩在村子上空的暮霭渐渐被月亮的清辉驱赶得荡然无存,深暗的蓝色天幕也显得有点儿灰朦。整座山村刹那间沉浸在一种迷朦的、似有似无的氛围之中,像是悬浮在冷森森的光影里。偶尔几声狗吠,仿佛荒野的狼嚎。碉楼形房舍黑洞洞的窗口像是怪兽的眼睛,竭力往月色里窥探。夜很静,静得使人肃然。我站在住地院门下的阴影里,视线被月亮、夜空、山林和村舍牵来牵去。随着月亮的游移,首先是山巅像刀刃般的雪峰变幻着形象,一会儿像弯刀,一会儿像长剑;山体的明暗面和房屋的明暗面也慢慢发生着交替,像是被一股神奇的力量在不断地制作。眼前的分分秒秒,旺麦村都呈现着不同的景象。我被这种奇异的情景深深地吸引着,很怕这一切刹那间会从我的视野里消失,我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月光给旺麦村造成的所有细微的变化,感到全部身心都在轻飘飘地流动,以致一个人影立在我面前我都没有发觉。直到他发出声音,我才回过神来。
月光在他周身镀了一层银白,掠去了身上的棱角,成了一个长长的影子,从他眉宇间一块闪亮的刀疤上,我认出他是把我们从县城引领到这座山村的生产队长。他谦恭地问我,我们工作队的队长在不在屋里,我说在,他感激地笑了笑,绕着我的身子进了院子。
我依旧立在院子的门楣下,我极想回到刚才那种感觉中去,我将目光再次投向眼前的景物,忽然发现变得毫无生气,如僵死了一般。耳膜里鼓荡着屋里生产队长和我们工作队长俩人十分礼貌的寒暄。过了一会儿,生产队长得知我们工作队长的老家就在这一带时,便改用当地土语讲话,工作队长也讲起方言,我听不大懂了。
当地方言语音的最大特点是雄浑,两个队长把这种特点发挥得都很好,他们雄浑的语调随着烛光的跳跃,穿透窗棂上的旧报纸,隆隆地滚进月色,然后钻进树林。我感觉到他们谈的并不是工作或者生产。生产队长似乎正在讲述一个故事,一个和这个月夜有关的故事,语调充满渴望和焦虑。他讲完之后,工作队长久久没有说话,屋里屋外一片寂静,月亮把它浓浓的光华堆在院子里,我感到旺麦村似乎陷进一种恐怖的期待,我抽身走进院子。院子里铺了一层月光,宽阔的屋檐下月光无法企及,但在月色的辉映下,依然轮廓清晰。我们当作卧室的那间生产队仓库的窗户上,烛光正在跳跃。
生产队长席地盘坐在粗砺的地板上,挂着泪花的双眼恳切地望着工作队长,工作队长坐在自己的地铺上,头埋在胸前。俩人的拇指盖上都堆着一堆黄色的鼻烟末。
“你去把尹玛叫来。”工作队长抬起脑袋对我说。
二
尹玛是我们工作队里唯一的女性,工作队组建之前我们互不相识。她看上去很年轻,对年轻姑娘的年龄不便过问,但我估计她在二十岁左右。据说她的第一职业是饲养动物,副业是唱歌,她的歌声一路上我们早已领略,的确非常动听,尤其是东部民歌,唱出来令人心醉神迷。我们工作队长曾问她怎么会唱那么多西藏东部的民歌?她说她天生就会,还会跳藏东地区传统的热芭舞。工作队长对她离谱的回答报以宽容的一笑。刚进村时,望着这个荒僻的山村,我对她说,你真不该来。她说她该来,她不愿一天到晚喂猴子,还喂狼。随后,她用异样的声音说,这个地方好熟悉,上辈子好像来过这里。我从她的眼神觉得她说的是真话,但这真话显然荒谬。
尹玛住在村子东头一个贫农女人家。我们刚到村里时,发现没有尹玛住的地方,我们工作队长临时决定让生产队长找一户可靠的人家,尹玛对于住在别处没有异议,但转了一圈发现那家没有厕所就皱起了眉头。队长当机立断,让我们马上专门在那家房后用树枝和木头为她搭建了一个厕所。厕所修得小巧玲珑,和尹玛十分相配。
我觉得穿过两条被月亮搞得半阴半阳的村巷之后就应该到尹玛的住地了,可当我从第二条村巷里钻出来时,我发现四周的环境很陌生,肯定没有来过。我听见潺潺的流水声,看见一条银色的水链从山腰黑乎乎的林木间向下舞动。水链的下端缠绕着一棵铺了一地黑影的大树。望着那片阴影,我突然觉得很不自在,因为我沐浴在月色里,对那片黑影来说,我暴露无遗。出于躲避,我毫不犹豫地走进了树下的阴影。树下阴湿,地面有许多被水冲刷得圆滚滚的卵石。树上的枝叶很浓密,月光竟然没能透下一星半点。树荫形成一个完整的黑圈,只是阴影的边缘有些凌乱,在风的摇动下,还在不停地凌乱。靠着粗大的树身,往外看裸露在月色中的物体,有种隐蔽的快意。忽然,月色中冒出一大片人影,无声无息地往这棵树下游来,难以断定是幽灵还是生命。对我的存在,他们视而不见,他们围在树荫外的月光下,所有的头颅向上扬起,望着空中的月亮,充满了期待。一个躬腰驼背的老者煨起了桑烟,一股浓烟腾空而起,悠悠地升往夜空。顷刻间,浓烈的芳香替代了春夜的清凉。我惶然地躲开,逃也似地钻进村巷。
我怎么也找不到尹玛居住的农舍,我没有发现房后有用松柏枝搭成的厕所,而这是我目前唯一能够区别这个村子里农舍与农舍的特征。我怀疑它是否消失。怀疑显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很容易引起恐惧,于是,不管所有院子里的狗怎么狂吠,我飞似地奔跑起来。
我没有有意寻找归途,但我回到了院子门口。生产队长站在我原来站立的位置,他对我的气喘嘘嘘表示了压抑的惊异。我刚要走进院子时,听见屋里传出了谈话声。男的声音显然是工作队长,女的正是尹玛,娓绵的语音带有中国南部的水味儿。我听见工作队长说派我去找她,如何等了很久。尹玛说她一直在房里就着月光看书但一直没见我的影子。我抽回迈进院门的脚,迈步向外走进月色。屋里的谈话被远处传来的一阵含混不清的嗡嗡声压倒,我向依然站在门楣下的生产队长招手,他走出阴暗,关切地站在我面前盯着我看。我告诉他刚才的事,他抬头看了看月亮,又侧耳听了听远处传来的声音,做了个手势就地坐下,他用皮袍的后摆垫着屁股,褪下袖子让给我当坐垫。
三
生产队长依然讲东部方言,但为了使我听懂,尽力将发音咬死,一句句讲得很慢。虽然我仍然听不大懂,但根据一些听懂的词汇,以及他的手势、神色,和在月光下异常丰沛的想象力的帮助,我在脑子里构成一个故事,我肯定我的构想和他所表述的相去并不太远,但我似乎难以将这个故事的精妙之处完全表达出来,我只能讲讲它的框架。
二十年前的一个月明之夜,旺麦村的村民们沉入了一个共同的梦境:远在西部草原的卓日山神的第九个女儿孜琼拉姆被当地的林妖设计掠来做了妻子。卓日山神追杀到此与林妖展开一场大战。旺麦村的全体村民帮助山神与林妖拼搏,最终打败了林妖,但也付出了血的代价(生产队长说他额间的疤痕就是那场战争留给他的标志)。虽然杀死了妖魔,但卓日山神并没就此息怒,他要女儿用自己的鲜血洗刷神圣家族的耻辱,经过旺麦村的全体村民们的苦苦哀求,卓日山神念及他们帮助自己战胜了仇敌,改变了将孜琼拉姆沉入地底的主意,但一定要改变她作为神圣家族一员的身份。他以神秘的咒语蜕去了孜琼拉姆身上的灵光,永远收回了她作为神女的万化之身。孜琼拉姆向卓日山的众神告别,众姐妹和她的眼泪流在卓日山下,成了一条蜿蜒的河流。最后,孜琼拉姆跨上自己的神骏,随着旺麦村的村民们离开了神山之宫……
嘎达带着女儿来到村子里的时候,像是被魔鬼驱赶着似的,他说他带着女儿走过了九十九座山,跨过了九十九条河,吃了九十九棵树上的果子,快走到了人间的尽头。他在村子里那棵大树下驻脚的那一刻,一轮明月恰好升起,前所未有的月色光华照着他的老脸,脸上布满了通往神界的梯子般的皱纹。随着他嘶哑的歌唱,他的女儿像只蝴蝶般地开始起舞,她时而跃上农舍平展的屋顶,时而飞身树梢。嘎达的歌喉似乎要撕裂月色,她女儿的舞姿像要捣碎月光。村民们被耳朵所听见的和眼睛所看见的带进了一个安恬的境界,他们忘记了夜晚的风寒,忘记了世间的苦难,进入了一种忘我的境地,世界也似乎消失了。
村民们为他们修起了一座木屋,嘎达每天晨出晚归,用各种奇异的食物养育自己的女儿。年轻的姑娘似乎很不愿意蜗居木屋,她总是攀上那棵大树高高的树梢,对着空中凝望,她说人间的路快走完了,她要寻找上天的路径。每一个月圆的夜晚来临,人们就可以听见姑娘的歌声,她的歌声就像春天的山林里布谷鸟的第一声鸣叫那样悦耳动听。村民们看到,每当这时,嘎达就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地坐在地上,脸上的皱纹被月色涂抹得如泣如诉,两只缺少光泽的眼眶里盈满水色。
时间过去了一年。这一年旺麦村诸事顺遂,瘟疫、冰雹、血光都像阳光下的露水一下子不见了,小伙子找到了倾心的姑娘,姑娘找到了如意的情郎。有四十九个新的生命诞生,死神始终没有降临。
村民们对这种难以置信的安乐吉祥景象万分惊讶。在人们带着欣喜的神色对这一切窃窃私语时,那个夜晚神秘的梦境再次生动地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于是,嘎达父女开始被人们的异样目光注视,这目光中有感激也有敬畏。人们心照不宣,以一种竭尽全力的虔诚默默地表达他们的感恩之情。每天清晨,木屋前总有姑娘们用木桶背来的清清的泉水;每天傍晚,木屋旁总有捆捆散发着香味儿的干透的碎米杜鹃枝;嘎达每次外出,总有骑马的汉子迎面走来,将坐骑奉让……总之,人人都注视着嘎达父女的一举一动,竭力满足他们哪怕最细微的需求,虽然嘎达父女从未向村民们要求过什么。
这种情景持续了半年多的时间。秋风开始在旺麦村的村巷里穿行,四野的庄稼和草木安恬地施放着馥郁的浓香。远近的人们开始传言:旺麦村是一座天堂。
丰收后的第一个月明之夜,人们抬出自酿的美酒,像每一个月圆之夜一样,齐齐地聚在嘎达父女木屋前的大树下,燃起火堆,喝着美酒,等待着嘎达女儿的歌舞。夜半时分,又大又圆的月亮缓缓西沉,村中一位年轻的猎手醉眼朦胧,他似乎看到一头长着羽毛的怪兽攀向树梢,他拿起弓箭向怪兽射去。一声撕裂夜空的惨叫在人们头顶炸响。正当人们惊疑不已时,木屋突然洞开,人们看到嘎达抱着女儿走进月色,她的胸前插着猎手的箭杆。刹时,女人们发出尖叫,男人们开始嘶吼。年轻猎手的脸色由血红变成惨白。一股夏天雨后的躁动气息在人群中弥漫开来,人们不约而同地逼视着年轻的猎手。年轻的猎手从腰间拔出长刀,在跪下的瞬间,刀尖穿透了他的后背。一道七色彩虹突然在暗蓝的夜空飞出,缓缓伸向大树,随着一声骏马的嘶鸣,人们看到一个娇艳无比的女人骑着白色的骏马,踏着彩虹直向浩渺的夜空飞驰而去。
月亮消失了。
四
嘎达父女的消失,在旺麦村留下了秋雨般绵长的惆怅。从那个不幸的夜晚之后,贫困、疾病和死亡再次降临到人们头上。人们感念嘎达父女驻足村庄那一年的幸福光景。他们深信,嘎达父女绝不会一去之后永不复返。总会有一个夜晚,一个月圆之夜,会有一个女人的歌声从村中那棵大树下传来,这歌声不仅能带来好运,还有对善良正直的旺麦村人的宽恕和抚慰。
五
我沉浸在关于这个故事的细节想象之中,生产队长何时离去我毫无察觉。直到大门里走出几个人影时,我才发觉我的全身都偎在生产队长暖乎乎的皮袍里。第一个从我面前走过去的是生产队长,他只穿了一件白色的贴身短褂,我站起身将皮袍还给他,他接过去转身披在身后的尹玛身上。尹玛满脸的兴奋,她低声问我,你找我了吗?我还没有回答,她便像风一样从我面前掠过。我刚想跟上去,一只宽大的手搭在我肩上,工作队长一脸严肃地对我说,睡觉去吧。我望着他们的身影在月色里晃动,许久,仍在我的视野里晃动。我看见孜琼拉姆骑着她那匹白色的骏马翻越千山万水正向旺麦村走来,看见她每走一步都在和各种妖魔搏斗,看见她焦虑的目光不时投向西沉的月亮。月亮眼看就要被西边雪山的锋刃切为两半,在这最后的时刻,月光以无与伦比的皎灿哗哗地泻下。雪峰、山林和房舍被铺天盖地的月光扑打得摇摇晃晃,远处探头探脑的几颗星星被月色逼进天穹。莫名的恐惧再次袭来,我冲进门楣下的暗影,隐隐约约的喧哗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逐渐高昂地传来,在这片喧哗声里,似乎有一个女人的歌喉,歌声散漫而凄婉,犹如孜琼拉姆在卓日山神殿的最后告别。喧哗随着月亮隐进西边雪峰的背后最终平息下来,我看见大树下聚集的人们脸上露出了二十年来没有过的欣慰的笑容,他们头碰头,互相深深地祝福,然后默默地走进各自黑暗的小屋,编织另一个神奇的梦境……
责任编辑:佘学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