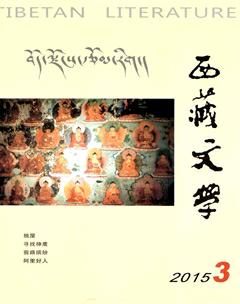作者说
赵若凡
你始终会在某一瞬间,蓦然发现自己变了。
这种变化深隐在灵魂之中,不易被发现。它透过灵魂支配你的行动,直到你终于发现,并感到难以形容的后怕与陌生。
从毫无意识地写下梦呓的语句,不断重复自己活在感觉之中,到现今的有些犹疑的用词,不能放下的涂改带,我深切而清晰地知道我变了。
那时毫无顾忌,无邪而透明地生长着,不断努力地以自己单纯的身躯去触碰和感知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顾忌,就是这样的坦然。可现在我的行动充满恐惧、疑惑,这是初次接触世事后的迷茫。于是在那一个时段我十分的决绝与固执。我说:这个世界没人可以了解我,而我也不愿了解谁。
在一些或多或少的经历中我开始惧怕伤害与背弃,并且开始寻觅一种自我保护的状态。这个状态使我变得孤独、凉薄,以及冷漠。
我相信这世间一定有和我一样包装自己的人。
即便只是那么一刻,他们脸上总是淡漠,没有泪水,并缓缓地吐出一个字:不。
可是在这冷漠的外表下是怎样的热切与绝望。你是看不到的,你看不到自一开始就隐匿在眼中的泪;你也一定是不会知道的,你不知道在那一刻他们是怎样地在逼自己,他们对自己说:不能哭。因而你只能看到一个极凉薄的人吐出讽刺的话,你厌恶地朝他说起最伤人的语言。他黯然地开始隐藏,却一丝都不予解释。你不会知道,这是他的高傲,也是他最后的尊严。
是的,我深信,总有些许人是这样的。即使仅仅存在于那个片刻。
而我,也必是这一类人中的一个。他们太敏感也太多情,将感官暴露在皮肤之外,被世界带来的一切不堪与邪恶灼伤。直到后来的麻木。伤害太多了,你是躲不及的。
正是因此,我知道我变了。不再为一些事掉泪,封闭内心。
有时候你觉得有的人突然变得很陌生。当你说出那句他变了的话时首先要知道,也许是你变了,也许是你们都变了。
变太奇妙了,我迫不及待地开始争取与躲避。还有寻觅。
当曾经必须要有华丽的语句,才会容忍这篇文章的出现,到如今甚至再写不出这些语句,也彻底地改变偏激的看法。在诗句中透彻地感到一种随意与无感时,我也开始陷入疯狂的惧怕。我惊恐地发现再无曾经的语言,也再无曾经的感觉。我开始退缩,也更加地不知所措。
可实际上这并没有什么。那一段年华已然风般飘过,会缅怀会不舍,只是正如诗里所言:前路缤纷。你又能如何呢?无法回头。也无需回头。
于是我就这样释怀地上路了,在自我保护的状态下开始准备忘却过去,那些所有的美好,所有的积怨。理所当然的,若过去可以轻易遗忘,它又怎么能叫过去呢?
怀着无尽孤寂,无尽恐惧,无尽自我安慰,以及三分缅怀,三分不舍,我就这样上路了。在一段这样的衔接空隙中,我写下了一个又一个幻想,来度尽这些情感。
在此之间,是诗盛载了我的情感,它一次又一次包容了我的幻想与决绝,也一次又一次安慰着我。它送来的不是颓然,是颓然过后的一种重生。寂灭与重生,怀念与恐惧,未知与幻想,在这些没有界定的模糊边界,我一点一点地汇集与积攒,用对前路的憧憬,冲破迷雾。也正是在那片没有界定的地方,我写下了这些诗。而那些冲突,不和谐的情感,也正是本书的缘起。
我真的应该感到庆幸。我在变的迷惑中与我的诗们一起逐渐走向清明。在大梦初醒的一刻,我的心很轻很轻。从前的重压已经在彻底地走向正确道路的最后一刻消逝了。我似乎又变成了从前那个明皓的人,不只是经历与心境变了,更重要的是走的也不是同一条路了。但无可否认,这些路都是向前的,虽然弯弯曲曲各不相同,抵达的却始终是同一个终点。
而对于诗中常常出现的那个意像“你”,都是不定的,虚飘的,而不是特定的一个人,只是我在变的过程中渴想的幻象。它也许是一只伸过来的手,冲破黑暗,可以将我从变的迷惑中拉出;也许是一个怀抱,可以驱散一切的恐惧与孤独;也许是一颗心,可以懂得我一切的情感。我甚至幻想它存在于现实。
然而这却是不可能的。这种幻像是不可能存在于现实之中的。它只能在一个迷茫的时段以一种救赎的形式出现,并且非常模糊,甚至连我都无以洞悉。它是适当的与温暖的,寄存着那些从前的梦,等待我在诗中放飞。
我想直到最后从“我幻想了无数种结尾/你却只是一个不存在的开始”中,我已渐渐醒悟了这美好的意像。我终于开始接受现实,开始迈向前路。
责任编辑:佘学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