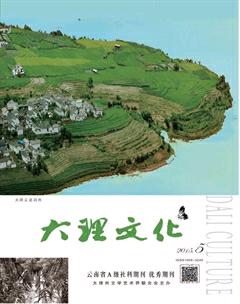李小麦的诗
李小麦
柿子树
“看,柿子”
我们把目光
一起转向村口的那株柿树
此时黄昏
阳光明媚矜持
万物飘浮在初冬的暖里
而柿树,被风褪下绿色的
大袍后
让红——
眩晕的红
耀眼的红
满满当当地,挂了一身
在清溪村
在柿树下
人们不止一次地感叹:
“真红啊!”
“红得好啊!”
“丰收啊!”
……
这缀满果实的柿树
多像我们这挣扎、隐忍、绽放
沉寂、消亡的一生
当所有的柿子落尽
当风中只剩柿树枯槁的身影
幸好
来年初春
你仍能从它身上
找到几枚嫩绿的
……
新芽
西街
那条脱了漆的长凳,恹然欲睡
这静寂的街,绝望如血
梧桐黄了,落叶似绸飘零
街角的咖啡屋里,寂寞已被香烟点燃
纤纤素手,搅动着一杯陈年的旧事
加了糖的咖啡,已经喝不出最初的味道
对面的陌生男人,请收起你虚弱的微笑
这西街,十里长亭连短亭
木槿树下,病后的相思灰飞烟灭
那支桃木手镯,还原封不动地装在锦缎盒里
转身,这清冷的夜,谁的影子
被街灯,拉得很长很长……
花事
梨花开了
白白的
我站在二月的门槛前
一瓣,两瓣,三瓣……
数梨花
你远游了
像一只放逐天空的鹰
我坐在那株梨树下
一秒,两秒,三秒……
等你回来
七夕
等一场雨
等一座虹
等一个
隔山隔水
隔天隔地的男人
等
三十多年来
我一直在麦城等
等一个赶马车的男人
这辆马车
来自遥远的麦盖提
里面,有一小袋饱满的麦种
赶马的车夫
有小麦色的皮肤
会唱《斯卡布罗集市》
不用下跪
只要跳下马车对我说:
“我找你找了三十四年零九天
我就放弃麦城
和他,亡命天涯
札记
喜欢花草。我种了一盆蝴蝶兰,两盆常青藤
一盆仙人球,三盆绿萝,一盆红掌
每天,给它们浇水,清洗叶子,观察它们的长
势
用微薄的薪水买花,买衣裙,买胭脂,买口红
买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
买艾略特的诗文
常骑上那辆永久牌的自行车,到郊外
看飞鸟,看流水,看彩云,看小麦,看水稻
看土豆,看大白菜
看田野里劳作的男人和女人
离别的车站
不喜欢车站
这里,总让我想起那方
被风吹远了的黄丝巾
想起那杯
已冷却的东瓜蜜
你笑我,只是短暂的离别
还会再见
谁知道呢
就像那株绿萝
开着开着,就枯萎了
就像那杯后谷咖啡
喝着喝着,就凉了
这些年来
喜欢上那种相依为命的感觉
比如,相牵而行的两只手
相偎而坐的两个身影
相拥而眠的两个人
这离别的车站
让我想起那些
在我心里走着走着
就走散了的故人
阿郎村
阿郎村
在阿郎山之巅
远远看去
像朵很大很大的蘑菇
它很小很小
全村九户人家
抬头是张三
低头是李四
回头是王五
只需六分钟
便能以网的方式
从起点回到终点
蓝花楹
“喏,蓝花楹——”
你指着那株花树说
注意她已良久
(是的,我用的是“她”)
在一幢青褐色的小楼背后
喜欢她满树的紫花
像一袭长裙穿在一个女人身上
——古典的、素雅的女人
蓝花楹——女人
多么老套的比喻!
可我,脱不了世俗
蓝花楹,美丽如此
依然逃不脱生的轮回与溃败
——盛放,枯萎,凋谢
这多么好!
像一个垂暮的女人
抚摸着松驰的皮肤
以及塌陷的脸庞、乳房和臀部
对盛放的蓝花楹说:
多美!
乌木村
乌木村的芫荽开花了
碎碎的
一坡坡,一凹凹
像策划良久的阴谋
在三月
铺天盖地的
大白于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