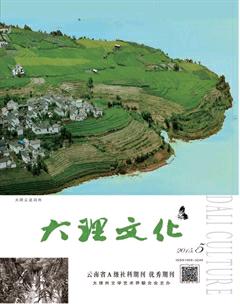幻想空间
铁栗+++杨友泉
一
船沉到湖底后,小镇陡然热闹起来。早年是一个铁匠铺,现在变成两个,叮当叮当赛着锤、抢着锤。镇上的人觉得怪,那声音响了几十年、几百年,咋就不一样了呢?又一想,人家是挣饭吃,锤声急迫一些,其实很白然。小镇上响着打铁的声音,古朴的样子依然存在,只是那份热闹太吵人了。除了铁匠铺和棉花坊,还有洗脚房、美容店、歌舞厅,以前都没见过。
阿呜德家对面就是棉花坊,店主老唐原本是贵州人,年轻时来这儿做了上门女婿。老唐脑子活泛,生意做得很火,铺子里总是有人出出进进。看到老唐挣了钱,江上鲛就想沾沾财气,也挨着老唐开了家棉花坊。江上鲛在水里可以呼风唤雨,开铺子却一点不行,生意冷清得厉害。他坐在自家店里,眼睛斜斜地看着对门的老唐,数他街天成交二十四起,空天五起。
镇上的人都忙着挣钱,阿呜德望着那份繁华,常常心惊肉跳。他感到那些外地人就像无枝可柄的鸟,忽然发现了这块净土,就一拨一拨地朝着这里飞。人一多就你争我夺,可他们争的到底是些什么,阿呜德却一点也看不明白。在这方面阿呜德是很笨的,他只知道眼下的日子不像从前那么闲适了,好像有种力量在拉着他,不参与到那些争夺的人群里也不行。
从阿呜德把船沉人海底,他就没去洱海里捕鱼了,只在镇上卖他的小船。小船摆在簸箕里,簸箕不是洱海,所以那些小船只能供人观赏,不能漂在水上。阿呜德从小在洱海边长大,洱海装在他心里,有利于他制做小船。小船不能打鱼,三十大几的傻儿子却总嚷着要吃鱼,他这才想起大船沉入水底已经好多年了。阿呜德觉得对不住儿子憨头,又拿不出憨头要吃的洱海鱼,只给他买了塘子里养的那种。憨头不吃,一直闹,在家里闹不出名堂就跑到街上闹。
憨头从小坏了脑子,说话做事总是出人意外,镇上的人没有不知道他的。茶余饭后,憨头就成了一道风景,只要他走到那棵大青树下,那些闲极了的人就开始逗他:
你有几条命?
憨头梗着脖子:
九条。
你爹有几条命?
憨头眯着眼:
一条。
你妈有几条命?
憨头苦着脸:
十八条。
对话永远都在继续,今天过了还有明天,像线,扯断了又重新接上,仿佛永远都不会到头。其实树下的人都晓得,憨头他妈早就不在人世了,他说的那十八条命不是他妈的,是他家那只花斑猫的。猫有九条命,它肚子里怀了儿,加在一起就是十八条命。这是憨头他妈在世时告诉他的,当时她告诉他这句话时不是和颜悦色,而是愤怒至极。
憨头有时是真憨,有时不是。他家的那只花斑猫怀了崽,嘴馋,老抢憨头的鱼。他终于急了,飞起一脚,把花斑猫从窗户踢出去。幸好它脚上有垫子,在地上弹了一弹,就势打了个滚,肚子里的崽儿没有掉。憨头他妈看得心惊肉跳,半天才缓过神来,她开始愤怒地训斥憨头:
猫有九条命,它肚里的儿也有九条。你一脚下去,十八条命呐!你下得了狠心?你狼心狗肺,你前世不遭天遣,这世成了人见人怕的混世魔王,你是地狱里放出的恶魔!背时鬼!贼杀的!烂肠瘟的!不得好死的……
憨头被吓懵了,就那么站着,怔怔地望着那张脸。他感到她突然变成了母老虎,已经不是自己的妈,是花斑猫的妈。她像是要把他吃掉的样子,目光里喷着火,爪子在他面前挥来挥去。憨头不得不一次次举起手臂,举起就不敢放下,严密地防范着那只利爪刺人他的脑颅。这是憨头他妈骂得最毒的一次,直到她把嗓子叫哑了,在他脑壳前一捣一捣的爪子才疲软下来。
事情终于过去了,憨头的眼里却掉出水来,而且越掉越多。他找到在院子里砍船板的爹,指指自己脸上的水,意思是问,这水是怎么回事?阿呜德说,你妈骂你不那样刻毒,你身上的过失就越背越多,你的寿命就越来越短。
本来憨头眼里的水一直在流,阻都阻不住,经阿呜德这么一说,那些水立刻就断了线。他摸了摸眼皮,又摸了摸眼皮,确实是干的。他突然跑出院子,一边跑一边喊,好了哩!好了哩!
就因为那次骂得太狠,憨头他妈的嗓子一直没有回过来,直到死,她的嗓子都是哑的。
二
憨头惹事是经常的,阿呜德稍没留神,他就会睡在双白的床上。
双白她爹就是老唐。老唐虽然是贵州人,但他一经倒插门插到这个小镇,开花、结籽、替叶,几个轮回,贵州的老唐就成了小镇的老唐。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说的就是当下的老唐。
当下的老唐说一口流利的白族话,除了尾音还有点贵州的残渣,你根本想不到他是外地人。以前憨头和双白都还小的时候,老唐就经常看到憨头睡在双白的床上,他觉得那纯粹是孩子的事。隔壁邻居的,大人们都出海啦,孩子们玩困了就睡在一起,这有什么?他们还都是娃娃,只要大人不朝复杂处想,事情就一点都不复杂。
可是现在,憨头和双白都已三十好几了,双白还这么容忍憨头,她男人看见总是不好。不过老唐就是老唐,他把憨头睡在双白床上的事看成风景,憨头的那份紧张让他感到很开心。这种事是人人都清楚的,双白再怎么闹也是双白,憨头再怎么睡也是憨头,是井水和河水的事。井水犯了河水还是在井里,河水犯了井水还要回河道,何况那哪里是犯?
双白也是这么想的,她晓得憨头还处在五六岁的年龄,他不可能有什么杂念。要说有杂念,那也是娃娃的杂念,双白就有过。她还很小的时候,看到憨头睡在她身边,就晓得这是除了她爹以外的第一个男人。但是她不觉得紧张,反而觉得很新奇。我的第一个男人会是他吗?双白努力地做着判断。明明晓得他是个傻子,却依然在想,他要是会收货就好了。她把憨头带到供销社仓库门口,自己站在板秤上,让憨头收购自己。憨头连放几个秤砣都不晓得,双白把秤砣给他放好,让憨头打秤。憨头不会打,更不会读,双白就不高兴:
废物啊!我不可能既在家里弹棉花,还要到外面去收棉花吧?
这些细节老唐是清楚的。他也出海,但有货就不出去。像憨头睡在双白床上这种事,他看到的就比别人多。
眨眼间老唐就老了,老眼昏花,看到憨头爬到双白的床上,做梦一样。憨头把手搭在双白的肩膀上,其实没睡,只是假装睡着了。老唐怕双白的男人回来看见,想把他弄醒,想想又没弄。双白的男人叫罗弦子,也是这镇上的,也是倒插门。现在他出去收货了,这小子脑子灵,把近处的棉花垄断了。老唐估计着罗弦子也快回来了,就决定去找阿呜德。
阿呜德来到老唐家时,看到憨头还在那儿睡着,那眼皮的抖动说明他并没睡着。眼前的情景让阿呜德愤怒不已,他顿时青筋凸显,举起木工尺就打。他觉得丢脸,前几天才被罗弦子打过,又来双白床上睡。更主要是阿呜德认为,憨头是一个月没有吃到鱼,故意让他丢丑。阿呜德出口就重,出手也重,有两下打到护住憨头的双白身上。双白大叫,打着我了!打着我了!阿呜德这才住了手。
把憨头整回家里,阿呜德拿着木工尺,在那块木板上面来画去。但他眼里蓄满了泪水,眼前一片糗糊,什么也看不清。阿呜德活了六十来年,除了打鱼和打船,再没别的本事。现在鱼不让打了,打了船也派不上用场,只能打些供人观赏的小船。对于不让出海打鱼,阿呜德完全理解。早些年他打了很多船,船一多鱼就少了,对此阿呜德没想太多。该打的打上来,该吃的吃掉,这没什么。不该打的鱼打上来,不该吃的吃掉,就有了罪孽。
阿呜德打鱼有节制,他只打养活他和家人的那份,这方面他没有罪孽。可是他打的船太多,那些船最终都驶向了洱海,最终都用来打鱼。有一阵他想,我不打这船,别人也会打。再说媳妇好不容易怀了孕,要闲一些日子,自己要照顾媳妇,也要闲。两张嘴等着吃,鱼鹰老黑也等着吃,不打船又咋办?这么想过阿呜德就有点镇不住自己,松了口,这一松口就不可收拾。船打得不结实,对船主歉疚,打得结实了,又对鱼歉疚。最后一条船是给老唐打的,老唐刚把船运走媳妇就把憨头生下来了,刚生下的憨头不会哭,只是笑,看着就不对。阿呜德忽然就意识到,这一准是罪孽堆多了,老天给了一个大大的惩罚。他故意看了看媳妇那个洞,比洱海还深,比洱海底还黑。
这么想着的时候,院子里就有了脚步声,是双白。双白长胖了,走进院子时她阴着脸,身上的肉随着她的脚步胡乱地颤动。她在憨头面前蹲下来,拿出一条创可贴,粘在憨头的手肘上。粘好了她便站起身来,冲阿呜德说,大爹,憨头心里纯净着呢,他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三
阿呜德当然晓得,憨头睡在双白的床上就是图好玩,他干不出那种出格的事。但他毕竟是三十老几的人了,而双白的男人又特别计较,这种事好说不好听。阿呜德必须要让憨头长记性,他不打他双白的男人也会打他,那样他会更惨。实际上阿呜德打憨头,他心里很疼,那滋味就像当年他把船沉到洱海里。
把船沉到水底那天,阿呜德心里很难受,比打憨头还要难受。可这船要是不沉,洱海就静不下来。这个洱海已经喧嚣起来了,从岸上往里一看,水面上到处都是人。水的本质就是静,人一多就热闹了,看上去反倒是一种荒疏。洱海毕竟不是海,是湖,有那么多船开进去,能受得了?这么想着的时候,实际上阿呜德也在洱海里,所以他听见天上,水里,总有一种不知所在的声音。
阿呜德晓得,岸上的人涌入洱海,其实是冲着那种个体很小的银鱼。打银鱼的网很细,要是洱海也像人似的有皮有肉,那一网下去,一定会感到刀刮一样地疼痛。人太狠了,为了打到银鱼就用那么细的网,其它的鱼类哪怕很小,也逃不脱被掠走的命运。政府当然不让这么干,洱海在白族人心里那就是母宗呢,哪有孩子这么刮削母亲的?但是习惯了,心里的欲望让人陷入实际,就这么无视规定地放纵妄为。
银鱼是日本人送的,说是好货,几百块、上千块一斤。当时市场确实也卖到了那个价,但是几年之后,几块钱一斤也没人要了,连日本人也不要了。那哪是鱼呀,一种寄生虫子,按照小学里陈老师的说法,那是剥削阶级,是地主,吸血鬼。日本人一不要,洱海里就全是那东西,海水的味道都不对。还叫它银鱼呢,整个洱海里的活物,它能比得上谁?出水几秒就没命,几分钟就发臭,中国人从不把这么龌龊的怪物叫鱼,是日本人想鱼想疯了。
价格高的那段时间,阿呜德也打那种鱼,一天十斤没有问题。那时憨头脑子还有些灵,阿呜德给他钱,他就窜出窜进打酒买烟。烟已抽到红塔山,这是从没有过的高度。后来就不行了,那种鱼一旦没人要,阿呜德就连带把的“春城”也抽不起了。他媳妇花儿把嘴撇到一边,摔屁股,句句都是难听话:作吧作吧,等你们把洱海作死了,你们也就死了。阿呜德说,我没有作啊,我一天挣一万,花十块钱买包烟,咋啦?
花儿又把嘴撇到一边,还是摔屁股,还是句句难听,作吧!作死去吧!
搞不好花儿那时就感到有什么不对了。
鱼就是那时候少下来的。有那么多的地主,那么多的黄世仁,这个洱海还能好得了?阿呜德又感到那种疼,却并不具体,是哪里疼,怎么疼,他有点说不清楚。或许那不是疼,是花儿天天骂他,让他有了死的前兆。那天黄昏,阿呜德把船驶回岸边,一回头,就看见一片紫红在洱海里粼粼闪动。他感到这个洱海像是在分娩,当这片紫红消失之后,洱海里会有更多的鱼。但是很快,他又觉得这个洱海是在咳血,好像很痛苦的样子。
其实仔细想想,生和死都是认识上的事,这种认识取决于距离的远近。外地人离洱海远,看到的洱海总是波光粼粼,他们会觉得这个洱海还处在很年轻的时光里。阿呜德离洱海近,他眼里的洱海正在咳血,已经无法展示从前的神奇。就这么呆愣了一会儿,阿呜德一狠心,把船沉到洱海里了。
四
船本来是用来活命的,自古以来,镇上的老辈子靠的就是船。但船多了也伤命,伤鱼的命,也会伤人的命。现在打不到鱼了,为什么?伤了鱼的命了!按说船就是用来打鱼的,打该打的,不伤命。打了不该打的,那就是伤命。老辈人都是这么讲的,年轻人不信,阿呜德年轻时也不信。现在他终于信了,可现在信了又顶哪样用?他再也看不到他的花儿了。
花儿为他生了憨头,这个憨头就像沉在梦里,怎么唤也唤不醒。后来花儿也瘫在床上了,她认定这是阿呜德作孽太多,遭了报应。她曾含着泪水告诫他,让他不要杀生,不要杀生,也唤不醒他。花儿心里越来越急,成千上万次地捶打着他的胸脯,边捶边骂:你的心是铁铸的!你的心是石雕的!你还打船,你要断子绝孙啊!她真的受不了啦,阿呜德打一条船,她就绝望一次。但她并没放弃,捶他一次就哭骂一次,直到阿呜德跪了下来:
没鱼了,我吃哪样?你吃哪样?憨头吃哪样?花儿!
我把船沉了,现在只有打船,花儿!
可是船太多,洱海也会死!花儿!
花儿!你给我指条路!
花儿!我给你磕响头!
咚咚咚,满额头的血。
花儿不让他打船,也不给他指路。花儿咒他是败家子,阿呜德晓得,不是说他把小家败了,是说他把洱海糟蹋了。海是大家,家是小家,大家糟蹋了,小家还守得住?花儿继续骂,左一个天打雷劈,右一个天打雷劈,都断子绝孙了还不住口。这一次花儿都骂在他的命脉上,疼得他牙都嚼碎了。这是明摆着的,一个憨头,靠他传宗接代不成,断了阿呜德的香火却是铁板钉钉的事。
闲下来时阿呜德也想,花儿的话也许是对的,这世上可能真的存在着因果报应。生了个傻子就够不幸了,现在连花儿也瘫在床上,这一连串的事也怪不得花儿要朝那方面联系。更奇怪的是,花儿本来好好的,说瘫就瘫了,不单是花儿想不通,阿呜德也想不通。那天他在院子里劈柴,一斧子下去,一块劈柴就白己飞过去了,正好砸在花儿的屁股上。当时花儿正端着簸箕往屋里走,那块劈柴飞过去她就倒下了,以后她就再也没有起来。
阿呜德晓得,花儿其实不是恨他,她那样咒他是要改他的过。只是他的过已经改不了啦,一条船就杀过很多命,他糊弄得了谁?花儿咒他,是为了让他的过失轻一点,轻那么一点也是轻。这些阿呜德是明白的,只是他想不通,那块劈柴怎么就白己飞出去了呢?再说,怎么会那么准,切在了花儿的股动脉上?
世世代代都靠打鱼,可这却是一条绝路。
虽然花儿已经瘫痪,但有一次她却自己爬到海边,而且是自己坐在那块石头上。她不想让阿呜德背了,以前她骂过他,现在他也把她整成了瘫痪,两人已经两清。那次花儿是去洗魂,她好像是感觉到了,自己离那个日子已经不远。如果她瘫在床上死了,凭着她的干净,她是不会下地狱的。
五
憨头还是忙出忙进,每次从外面回来,他都非常兴奋。他朝阿呜德比划,说房子盖得高,比大青树还高。又忙进来,说玉玑岛的玻璃大,比房子还大。又忙进来,说白莲花煮的鱼香,比阿呜德煮的还香。说到鱼他就向后闪了一下,好像那鱼正蒸腾着热气,不这么闪一下就会烫着。这之后他的口水就亮品品地淌了出来,好像那辣子鱼早被他吃了几条,那口水是被辣出来呛出来甜出来的。憨头就这么简单,水至清则无鱼,这是镇上的张老师给他的评价。
看到憨头的那副馋样儿,阿呜德感到很歉疚,他晓得憨头已经两个月没吃到鱼了。镇上的人不把吃鱼挂在嘴边,就像山上的彝人不把吃菌子挂在嘴边,因为那是经常的事。海边的人吃鱼是天生的,生下来还不满月,你喂他,他不吐,吃了还要。一两岁,你把一条鱼丢在他碗里,鱼刺左边进右边出,卡不着他。四五岁,他会从鱼头开始,吹口琴一样,从头到尾吹一遍;翻过来,又从头到尾地吹一遍,吃剩的骨架像小学里的鱼类标本,不带丝毫肉星。
憨头也一样,他只傻该傻的,吃鱼一点儿都不傻。刚满月时,他见阿呜德吃鱼,嘴就一翕一合的,眼睛还盯阿呜德的嘴。阿呜德把鱼咽进去,憨头的口水就咽一下,好像他也尝到了滋味。他还会把目光移向土锅,穿过土锅里红红的辣子和绿绿的大葱,死死盯着露出来的鱼腹。这时阿呜德才反应过来,喂他一口,他就等你第二口。和镇上所有的娃娃一样,一两岁,丢给他碗里一条巴掌大的整鱼,芒刺左边进右边出,卡不着他。四五岁时,他吃鱼也是从鱼头开始,吹口琴一样,从头到尾地吹一遍,一条鱼就只剩了骨架。
阿呜德觉得,还是得在船上作文章,没有别的选择。他已经是黄土埋到脖子的人了,就会做两件事,打鱼和打船。现在,鱼打不成了,船也不能打了。阿呜德很是苦闷,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屋子里的烟雾呛着了憨头。憨头并不抬头,他把阿呜德的烟灰撮在纸上,十多支烟灰竟然有他的半捧。他朝阿呜德笑着,又将手指朝阿呜德勾了一下,阿呜德就晓得他有什么事了。憨头走,阿呜德也走,他看出憨头领他去的方向是海边。阿呜德除了海边有两墒菜地,坡上有一块半亩多旱地,几乎没有什么事可做。这次是他跟着憨头走,走走停停,一时间竟产生了兴趣。有一阵他竞觉得,憨头不憨,是镇上的人憨,他们总是那么忙那么急。急什么哩,还不如就像憨头这样,该走就走,该停就停,就这个样子。
来到海边阿呜德才发现,憨头是冲着那块岩石来的,那正是花儿沉下去的地方。撇开花儿沉下去的事,洱海是漂亮的,那份宁静让他心里颤动。湖心像草甸子上开出的碎花,片片闪眼,片片剜心。那么好看的洱海呵,阿呜德见到它时,却感到一阵阵地疼。镇子上的人都那样,不那样疼,洱海还是海?但阿呜德的疼与他们不一样,除了洱海的美丽带给他的疼,还有花儿沉下去带给他的疼。这两种疼,让阿呜德见到洱海时,既剜心窝子又牵肠挂肚。
憨头拿出折好的纸船,放到水里,舱里的半捧烟灰把船体压得斜到一边。但是到了船沿就不再歪了,坚持着往海里漂。
阿呜德忽然想起来了,憨头小的时候,最喜欢折这样的纸船。他折的船很精致,舱、篷、桅杆,每一样都像是出自阿呜德的手。小学里的张老师在路上遇见他就说,阿呜德老爹,你不要给憨头折船了,他的书包里都是纸船。阿呜德说我没给他折,这小子,怕是哪个同学送他的。张老师断然否定,说不可能,这镇子上的人没有哪个会有这种手艺,那就是你折的。
阿呜德那天没有出海,在街上站了半天,又在院子里站了半天。等到憨头从学校回来,阿呜德翻开他的书包,果然就有半书包纸船。那些纸船材料不同,尺寸不同,但每一只都和阿呜德的渔船一模一样。阿呜德拿起柳树条子就打,劈头盖脸,打得憨头像跳神一样。花儿到井边洗衣服,老远听到憨头叫得不同,跑进院子时,憨头的脸都脱了形。花儿看到憨头被打成那样,愤怒了,一头撞到阿呜德的肋骨上。
阿呜德并不晓得疼,他鼓着牛劲说,他偷船!
偷船?偷谁的船?
他不说!
船在哪?
花儿迅速扫了一眼院子,除了船坞上架着半条没有成型的船骨,院子里什么也没有。再说,十多岁的娃娃偷得动船?给他他也弄不了。这么一想,花儿的毛病又犯了,她冲着阿呜德大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