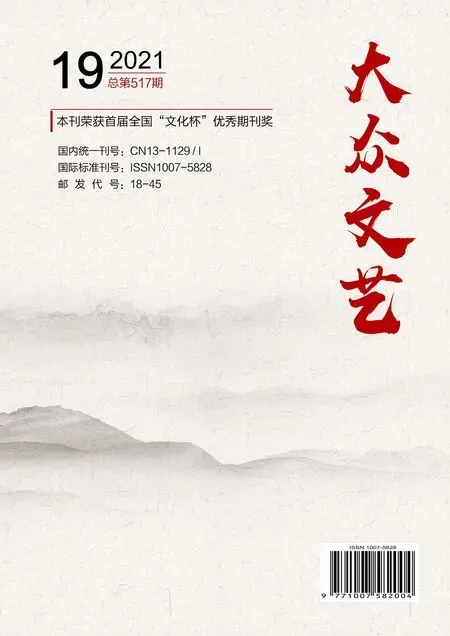博尔赫斯小说的“形而上幻想”
——由《虚构集》到《阿莱夫》的探求
李 静 孙云霏 (广西大学 530004)
博尔赫斯小说的“形而上幻想”
——由《虚构集》到《阿莱夫》的探求
李 静 孙云霏 (广西大学 530004)
博尔赫斯小说的语言以隐喻为基本手法,呈现出喻体超越本体属性的特点,并表现出本体论的姿态;其叙事由形而上意旨与特殊时间融合扩张成独特的心理场域;其形而上思考在吸纳前人精粹同时渗透别致的幻想。本文旨在通过《虚构集》与《阿莱夫》两部短篇小说集研究探求:建构在语言、叙事场和形而上学的叠加之上的“形而上幻想”——这是博尔赫斯小说的独特魅力所在。
博尔赫斯;叙事场;形而上幻想
一、博尔赫斯的叙事场建构
叙事场作为一种场域形态,是物质与能量的共生存在。主要涉猎人物、人物关系、背景、叙事时间以及在叙事过程中,读者与文本互动而产生的心理场时空容纳。
1.关于人物、人物关系、情节进展、背景——以《分岔小径的花园》为例
博尔赫斯的小说中,人物具有很强烈的形而上意旨性,而情节的故事性是弱化的,人物只是通过情节来进行发现和言说——如果说人物是一个活动的意象并具有隐喻性是完全成立的。不过作为小说传统的构成要素,我们还是对其进行单独分析,并指归于叙事层而非语言层。在《分岔小径的花园》中,“我”和“我”的祖先彭是两种时间观念的体现:我认为时间是循环的,但彭却否认。“小径分岔的花园是彭心目中宇宙的不完整,然而绝非虚假的形象。您的祖先和牛顿、叔本华不同的地方是他认为时间没有同一性和绝对性。他认为时间有无数系列,背离的、汇合的和平行的时间织成一张不断增长、错综复杂的网,由互相靠拢、分歧和交错或者永远互不干扰的时间织成的网络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1彭站在时间入口,以个体的姿态探望时间迷宫,并在时间中可到所有可能性的发生,看到不同个体的全部可能性相互编织的错综复杂的网;但“我”看到,“将来已经是眼前的事实”,在恍惚中窥见的将来会在现在发生,而“我”也是祖先彭的某种将来,也可以说“我”在彭的可能性中已经经历过并且在循环重复。“我”是一种当下的时间,但当下时间的存在等同于时间的永恒存在,所以“我”认为的时间循环与祖先彭认为的时间不循环形成悖论——但正如彭是“我”的祖先,这两种时间观是无法截然分清的,它们相互交织构成小说文本空间的无穷张力——这张力便是“心理场”的形成,也即常规心理的“歪曲”。
2.叙事时间的虚指张力与心理场形成
时间在博尔赫斯小说中出现频繁且带有浓厚的形而上趣味。博尔赫斯的迷宫是用划成宇宙天花板方格的时间构建的,种种意象安置其中:镜子、扎伊尔、图书馆、百科全书、花园……博尔赫斯的时间以两种不同的姿态出现,它们不是对立而是彼此互补的。时间的出场总是带有神秘的面纱——时间是形而上背景和宇宙底色;时间不止将读者置入叙事场内,其本身兼有形而上意味。时间在博尔赫斯小说中以渗入和无处不在的弥散铺成叙事和“形而上”场力,在叙事进行时又以透明的姿态退隐淡出,却保持始终在场并超于叙事。
传统的叙事时间通过与出现在言说对象中并形成言说对象自身的时间,而使人物和观看人物的读者进入时间叠加而成的张力空间,将时间本身进行虚化,而让其获得不确定性、无边界性和永恒性,突破了读者的阅读经验并形成“惊异”和“厌倦”,读者是通过对时间的直观感受来完成心理场建构的。
(1)小说叙事时间的两种形态与融合
时间在博尔赫斯小说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低位,或者说,时间便是博尔赫斯小说形而上质的体现。博尔赫斯的时间呈现出明显的悖论倾向,而又在鲜明的悖论中取得了形而上的张力——这悖论在于时间的无限与个体的有限之间。首先,在这种悖论下否认了过去和未来的存在。相对于无限延长的时间来说,个体生命无论长度何如,死亡不过是极短暂的对于过去的失去,而漫长的过去不知被存放于何处;未来则是无穷的延伸与未知。过去和未来的无限在个体的段在中丧失了意义,于是个体只剩下现在,自然,这现在对于个体来说便是窥探永恒时间的入口,或者说,时间对于个体在当下呈现出永恒状态。其次,博尔赫斯的时间大致可划分出两种:循环时间和无限不循环时间,但这两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无限不循环时间中人的命运是纷繁复杂、彼此交错、杂乱无章的,人的时间强烈突出了个体性,但从整体的人的时间进程来看,人的命运仍是循环的,只不过于个体来说并不是单一的循环,而是每次都面临着新的境遇和情况。
如果说博尔赫斯在《虚构集》中将时间与人的关系看作:从时间的角度看整体的人是循环的和从无限多的单一个体来说的时间是无限不循环的,那么在《阿莱夫》中个体与整体,当下与永恒的悖论便开始消解,时间变成一个巨大无比的混沌的包容体,含纳一切——由此人的身份也不再具有个体性,而是混杂的、难以言说的,“你”“我”神是一张面孔。将循环时间与无限不循环时间融合,将人物身份视为同一,由此对传统时间与人的定义进行了解构——时间是不朽的,也是当下的,世界与“我”同一的。于是叙事形成一种全方位、多可能的深入观察描述,世界纷繁混杂、不尽言说又充满神秘性。“宇宙是心理学的无限神性”,发现并进入于此,带给人的感受仍是惊奇和厌倦。由此叙事,时间和心理场完整的形成了形而上的叠加并形成镜面效果——无穷尽的反射和衍生,由此形成的悖论产生无限的张力。自然博尔赫斯在这反反复复的真实经历中也发出自己的感受:惊奇和厌倦。博尔赫斯是具有终级关怀精神的。在经历真实后人的精神状态是怎样的。我们惊奇,厌倦,然后呢?又张开无限的想象。
在《阿莱夫》中死去的女人代表了过去——逝去和静止,而“我”代表现在的变化的世界,“我”对贝亚特丽丝的单向的、不合情理的感情由于她的死亡而成为“我”任意想象的对象。女人的生命流动变成由照片和记忆拆成的段状,而开头便抛出“世界会变,但是我始终如一,我带着悲哀的自负想到”2由此“变”与“不变”形成互补悖论:“我”始终未变,变化的只是女人在记忆中改变;女人因死亡而未改变,改变的只是正在行进的世界。死亡以个体过去终结的姿态形成静止,但对于生存在当下的人来说却意味着对过去无穷无尽的回忆与言说,以及正在发生的无止境的变化和通向无知的未来。博尔赫斯用大量象征和隐喻来说明“阿莱夫”,而“我”与达内里同样看到“阿莱夫”却采取相反的姿态。达内里拒绝遗忘而是不住的言说,试图描绘阿莱夫中看到的难以理解的宇宙的一切;而“我”认识到阿莱夫的宿命性并借助遗忘重归宁静:阿莱夫、“我”、达内里的同时出现便邀请读者进入“我们”共同存在的时空,读者面对阿莱夫时会产生怎样的惊叹与做出怎样的选择,博尔赫斯微笑着让读者自行选择。
(2)博尔赫斯的心理场形成
博尔赫斯小说建立在隐喻上的叙事呈现出一种当代语言哲学上描述的“显露情景”,在这种情景之中,某一事件会敞露出它的整体关联和意义,事件内部即外部,显露自身并超越原本的属性与范畴。它不是被赋予主体的外在压力,而是一种主体的给予,阅读者将自我的全部给予事件(文本)并不惧于跌入无穷尽的深渊,感受其中变幻莫测的斑斓与黑洞般致命的陷阱。叙事与心理场是不可分的——建构心理场的过程便是叙事的过程。叙事亦有其本质的与生俱来的形而上的属性。
当我们进入真实的心理场,也即某种显露情景中,可以说我们就是永恒存在的——永恒存于静止。一切均向我们显露出自身的本质意义。而语言是匮乏无力的,语言无法描绘包容无限的哪怕最小的一部分。所以在心理场中,语言的叙事不是传达某种信息,而是一种见证,言说即存在。博尔赫斯精心制作的叙事便是一种用可言说的、极富暗示和启示性的场景,来言说过去、现在、将来和无限广阔的空间,言说永不停止的变化,言说永恒轮回和轮回中的身份,言说无边界的梦和梦的底层,言说神和宇宙——它们是整一性的,“人虽然是有限的存有,不能完全掌握什么是无限,但对无限却有一种直觉,例如,从所经历的一串串时间,人就直觉地意会到无限和永恒。但若要积极地表达这无限,总感到无能为力,除非这无限是自行向人显露出来。”3博尔赫斯的叙事是一种深邃而充满神力的邀请——经由叙事进入神秘的“心理场”,并感受其中的“惊奇”与“厌倦”。
(3)时间对叙事和心理场的沟通
那么时间是怎样沟通叙事与心理场的呢?时间作为叙事与心理场之间的媒介,既是叙事的背景又是叙事的对象,同时在叙事进程中形成了传统的所谓的叙事时间。但其在叙事过程中通过对时间本体(作为对象)的形而上发问和言说,无限延长了文本中的叙事时间(作为背景),从而超出承载时间的故事情节(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一个故事的叙事时间),达到叙事的虚指和形而上性。在叙事时间(同时作为背景的本文叙事时间和言说对象)及其对自身虚指化之间形成巨大的张力和感受空间,具有无穷的开敞性和蔓延性,这让我们对叙事时间(背景)的感受倍增无穷和对时间真实的思考模糊程度雪上加霜。读者在阅读时进入叙事场,碰撞张力并形成强烈的直观感受——惊奇和厌倦——博尔赫斯与读者既是在时间的流淌中经历感受又在探求作为真实的时间存在。
二、博尔赫斯小说的形而上幻想
博尔赫斯的隐喻手法在文章中滋生繁衍无穷尽的暗示性,而充满开敞的微笑着的邀请叙事是精心制作的,充满着互否、悖论、混沌、分裂、象征性意象等,从而于字里行间的裂隙中拉开无穷尽的张力,并产生“显露情景”的效果:“只要让对立的远近制造出瞬间交汇、时空合一,再怎样不可理喻的事物都可以变为可观的现实。”4这些都与叙事上的“心理场”形成相互撞击、相互渗透;在以时间为材料勾连起叙事和“心理场”、并渗入深厚的潜存的哲学思想,最终形成的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只属于博尔赫斯的形而上幻想——充满暗示,读者处于混沌、繁杂、无穷尽的宇宙中,读者的自我身份消失、连同自我在世界中的过去和未来,读者消弭一切与他人身份同一,时间的无线永恒和这一切存在的真实——属于博尔赫斯的独特的形而上的真实。
博尔赫斯的形而上是叠加的:隐喻、叙事、“心理场”均以形而上的姿态相互叠加渗透,形成镜面反射一般的无止境的扩张和繁杂,并通过时间的置入和探讨人与时间的悖论使形而上有所凝聚却又向四面八方开敞。这一切形成了一个无限包容的混沌的球,却又是宇宙中的黑洞深渊。博尔赫斯在这其中游历、游戏和幻想:“一个人要是过多地沉湎于幻想,沉湎于那些有宇宙的浩瀚和时间的无穷奥妙所组成的虚幻之境中,他本人亦很容易成为虚幻的一个部分。博尔赫斯认为,他所面对的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虚幻的,不堪一击,弱不禁风。它是由一个更高意志(智慧)的主宰(也许是上帝)所做的一个无关紧要的梦。另一个梦,是博尔赫斯和所有的人共同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日常生活。”5
博尔赫斯的幻想是有魔力的,充满形而上意味与终极关怀的;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无限可能性的叙事言说场,也为我们彼此共同进入“歪曲”的“心理场”提供了一种真实。这种幻想是无所不包的,是宇宙中无限存在的清晰的引力、射线和电波,是令人眼花缭乱又无限清明的、甚至是透明的;它不干涉任何粒子却让人眩晕,让人敬佩、恐惧、惊奇、厌倦。博尔赫斯的形而上幻想是一种整体的感受力,是博尔赫斯独有的“真”,带给我们以无限的惊奇和全身的、灵魂的震颤——我们对言说方式的、对于时间的颠覆和对于宇宙存在的可能,对我自身生存的过去、未来,对于我们如何对待命运、命运中的无限循环和我们与他人身份的趋同、我们无法论断绝对的是非善恶——我们的生存境遇究竟是怎样的,当跳出生活之外,我们触碰到了什么?那是永恒的冥想的宇宙,是无限的幻想,博尔赫斯发现了它。
注释:
1.(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全集》(小说卷),王永年、陈泉 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页.
2.(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全集》(小说卷),王永年、陈泉 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页.
3.(德)卡斯培,罗选民译.《现代语境中的上帝观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4.陈仲义.《现代诗:语言的张力论》,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页.
5.格非.《博尔赫斯的面孔》.上海: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84页.
[1](阿根廷)博尔赫斯。《博尔赫斯谈艺录》。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
[2](阿根廷)博尔赫斯,王永年等译.《博尔赫斯全集·散文卷(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3](阿根廷)博尔赫斯,林一安主编,黄志良、陈泉等译.《博尔赫斯全集 散文卷(下)》.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 .
[4](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王永年,陈泉译.《博尔赫斯全集》(小说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5](英)贝克莱,关琪桐译.《人类知识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6](德)康德,蓝公武译.《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
[7](德)卡斯培,罗选民译.《现代语境中的上帝观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8](德)卡斯培,罗选民译.《现代语境中的上帝观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9]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10]周燮藩等.《苏非之道——伊斯兰教神秘主义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1]陈仲义.《现代诗:语言的张力论》.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
[12]格非.《博尔赫斯的面孔》,上海:译林出版社,2014.
[13]龚丽萍.《解读纳博科夫和博尔赫斯作品中的无穷极限》.《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11(06).
李静(1989— ),女,汉族,河北沧州,广西大学14级公管学院,外国哲学方向,硕士研究生。
孙云霏(1994— ),女,汉族,辽宁海城人,广西大学12级文学院,汉语言文学方向,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