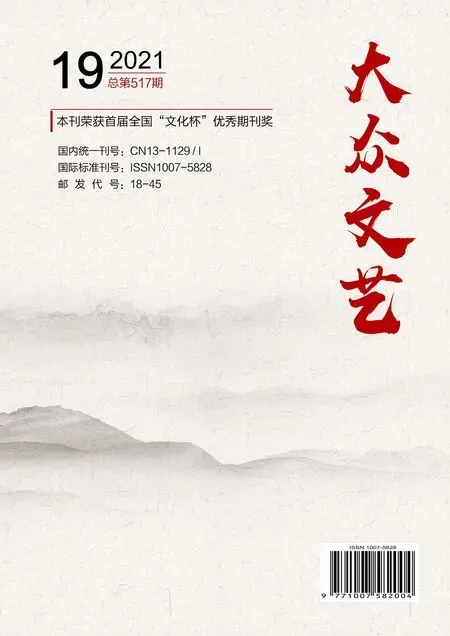从《聊斋志异》看中国古典男权文化下的女性角色塑造
郭钊玮 (成都理工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 610000)
从《聊斋志异》看中国古典男权文化下的女性角色塑造
郭钊玮 (成都理工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 610000)
从女娲造人的故事伊始,女性角色在中国的神话、小说或是传记中都有特殊的形象。她们不同于男性的刚列、粗糙和勇猛,更多体现了阴柔的一面,甚至在塑造过程中受男权文化的影响,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塑造了各式各样的女性角色。透过这些女性角色的性格特点,受众不难看出创作者的个人创作方式和思想,也可以体会到当时社会环境下男权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
聊斋志异;女性角色;男权文化
一、蒲松龄等悲苦文人的创作心态
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写到:“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栏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蒲松龄的创作心理印证了弗洛伊德曾谈到的观点:“艺术创作的奥秘,在于满足艺术家个人得不到满足的愿望。艺术作品本身是这些极不满足的愿望的代用品。”《聊斋志异》当中的女性形象蕴含着作者的情感思想,体现着男权文化下的女性特征,折射着现实生活中的苦闷。
1.对于搜心猎奇鬼狐故事的雅好、坐馆生活的慰藉
《聊斋志异》当中共有短片小说四百九十一篇,最吸引人便是其中仙狐妖怪与人之间真幻相生的故事。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谈到:“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明确点到自己虽无干宝之才,却痴迷于奇异之事,还将自己与苏轼类比,喜欢听人谈鬼怪的事情。作者将自己对于鬼狐奇异的雅好也灌注在其他作品当中,如“途中寂寞孤言鬼,舟上招摇意欲仙。”(《聊斋诗集》)
作者在坐馆设帐的生活中充分利用藏书资源,拓宽了自己的视野、提升了审美的高度。这种维持生计的方式看似惬意,但作者内心的苦闷是无法表述的。蒲松龄自认为怀才不遇,强烈渴望别人来肯定和认同自己的价值。与亲人的长期疏远让他的苦闷无以慰藉,只得通过笔下的人物来表达对亲情和爱情的理想。蒲松龄把这些人物设置的在科场上春风得意,而且身边都有深情相守的“知己”,例如《胡四娘》中的程孝思等。这些角色的塑造满足了男权文化下女性的理想模样,她们多少都带有温柔、妩媚、贤良,甘心为男性付出的特征。
2.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悲愤、科场失意的排解
蒲松龄生活的明末清初并不是太平的年代。这一时期,改朝换代,中华民族的融合进程和文化碰撞交融,战乱、动荡和爱恨情仇脚趾在一起,使人物活动的舞台精彩纷呈。这些都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宽广的社会视野。蒲松龄目睹了苏扬秀丽风光后的平民之苦,战争侵扰、苛捐杂税和水旱灾害。在《聊斋志异》中,作者对社会问题有许多反映和批判。《水灾》中“甲寅岁,三藩作反,南征之士,养马衮郡,鸡犬庐舍一空,妇女皆被淫污”,深刻揭示南征之士的罪恶行径。蒲松龄亲眼目睹了官员腐败给百姓带来的痛苦,也感受到土豪劣欺压百姓的蛮横。在蒲松龄的作品中,他塑造了不少贪官污吏和乡间豪坤,同时也有一批清官廉吏的正面形象与之形成对比,构建成作者对于未来的理想。
科场上的失意使得蒲松龄塑造了一批排遣内心苦闷的“儒生”形象。这些下层读书人渴望通过科举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无论现实多么困苦,他们仍然坚持不懈。这些着了魔的儒生也揭示了科举制度和思想的禁锢和弊端。但作者并未对科举制度产生怀疑,只是发出内心的苦闷,有一定的片面性。从《聊斋志异》中的故事可以看出,儒生与女妖的种种纠葛只不过是落魄文人的白日梦。
二、从男权文化下看《聊斋》中鲜明女妖角色
1.美丽清纯,才智超群
在《聊斋志异·婴宁》中,婴宁大胆活泼,亦憨亦黠,爱说爱笑。全文中仅描写婴宁“爱笑”这一特征的就有四十多处。“拈梅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表现出清新自然的脱俗之美。加之她“爱花成癖,物色遍戚党;窃典金钗,购佳种,数月,阶砌藩溷,无非花者”,并且自小就没有世俗礼教的侵染,性格中带天真无邪的野性。蒲松龄塑造的“婴宁”颠覆了才子佳人小说中淑女的笑不露齿,她爱笑,并且想笑就笑,具有真性情,身上有如同精灵一般的灵气。书中更有“纤腰盈掬,吹气如兰”的牡丹仙子,“笑弯秋月,羞晕朝霞,实天人也”的公孙九娘,“众情颠倒,品头题足,纷纷若狂”的阿宝等等光彩照人的角色。作者借这些品貌得兼的角色,表达着他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聊斋志异》中的女性角色不单有绝世的容颜,有些甚至被赋予了高雅的气质,才智超群。《聊斋志异·嘉平公子》中的温姬虽为鬼妓,身份低贱,但依然能文善歌,出口成章。仅是听窗外雨声不止,温姬便吟出“凄风冷雨满江城”来抒发内心的苦闷,并且求公子续之。公子不解,被温姬称为不知风雅,还劝公子习之。蒲松龄借温姬讽刺了当时胸无点墨的纨绔子弟,并告诫众人切忌以貌取人。更有 一些故事以下棋、吟诗为相聚机缘。“颇解文字”的白秋练与“执卷哦诗,音节铿锵”的慕生,“剪烛西窗”的连锁于杨于畏共谈诗文,“兰梅,辄以尺幅酬答,得者藏什袭以为荣”的聂小倩。
2.勤劳持家,情深意长
在封建社会中的男权文化下,女子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的继承权,在家庭中属于附属地位。但在《聊斋志异》中,她们辛苦经营,勤俭持家,正是家庭和睦的关键。《青梅》中的青梅慧眼识人,嫁给贫穷的张介受,辛勤劳作,以刺绣为业维持着家庭的供给。《鸦头》中的鸦头“做披肩,刺荷囊,日获赢余,顾瞻甚优。”《细柳》中的细柳自请当家,处理事情井井有条,“半载而家无废事”。《凤仙》中的刘赤水正是在凤仙的激励和督促下走上正业,“一举而捷”。
蒲松龄在作品中也刻画了许多忠贞不渝的形象,她们情深意长,视爱情如生命。《香玉》中的香玉为黄生死而复生,生而复死,憔悴而亡。《细侯》中的细侯明知道满生“薄田半顷”“破屋数椽”,也愿意“愿得同心而事之”。《连城》中连城对乔生的知己之情历经生死磨难,依然如初。王士祯评道:“雅是精神,不意牡丹亭后复有此人!”《宦娘》中的宦娘感叹人鬼殊途,便促成温如春与葛良工的婚姻。只得把自己的相思倾诉在《惜余春》中,令读者为她扼腕。《阿绣》以豁达之态直面刘子固的歧视和冷漠,帮助刘子固有情人终成眷属后,她消失了。她的不期而至和悄然离去都毫无勉强。阿绣以善意宽容的“成人之美”诠释着自己爱的哲学:“爱一个人就要让他跟所爱的人走到一起。”
3.个性解放,侠客风范
在翩翩和罗子浮的爱情故事里,翩翩遇到“又念败絮脓秽,无颜人里门,尚趑趄近邑间”的罗子浮,不仅说“我出家人,居有山洞,可以下榻”,还接受了罗子浮的以身为报。翩翩放弃了造作的男仙,与凡间男子“遂同卧处,大相欢爱”,明显看出仙子和普通人一样追求感情和幸福。蒲松龄笔下的女仙故事无不透露出对正当性爱的肯定,具有首创意义。“女仙们在不拘一格主动与凡间男子好合,尽情享受生之乐趣的行为中,在性情的自然流中,彻底背离了男尊女卑、鄙视性爱的封建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将人性发挥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与文学意义。”
《红玉》一文中,蒲松龄在刻画红玉的外貌时先写到“神情光艳”,再写到“女袅娜如随风欲飘去,而操作过农家妇,虽严冬自苦,而手腻如脂。自言二十八岁,人视之,常若二十许人”。先是给读者遐想的视觉和气质之美,再是具体的感官之美。由抽象再到形象,让读者遐想联翩,最终形成鲜活的形象。红玉最具光彩道德地方在于她具有独立色彩的爱情观念上。红玉追求爱情的方式属于不请自来,自荐枕席,透露出婚恋意识的解放。侠女的身份设计让红玉初入凡世就怀着救助弱者的大义,用女性温婉之爱给冯相如带来心灵慰藉。为爱隐退,甘心于隐处的大局精神更是侠客的美德体现。在相如危难之时,红玉挺身而出,重振冯氏门庭,更是大德之美。这些颇具侠女风范的角色以柔克刚,凭借自己的能力摆脱困境,把握人生,以强者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坚韧刚强和果敢为父雪冤的侠女;冷静和执着为自己赢得尊严的窦女;用个人智慧捍卫自己权利的深闺少女云翠仙;大难面前称沉着冷静、幸福人生的把握者庚娘。
三、男权文化下《聊斋》中“女妖”角色塑造
1.对于女性理想化的塑造,妖仙的区别
在《聊斋志异》的世界中,仙、妖和鬼都与人发生了故事,但从蒲松龄的笔下可以看出女妖才是书生的理想伴侣。首先从外貌来看,故事中的女性大多都有美丽的容颜。女妖虽美,但最多只有“美貌若仙”的赞叹。“楚楚若仙,心甚悦之。”(《双灯》)在创作者看来,仙的美丽乃是首位,女妖次之。但和寻常百姓家的女子比较而言,妖的美丽是娇艳的。“夫人窥其容,疑人世无此妖丽,非鬼必狐。”(《林四娘》)足以见女妖的鬼魅程度。
究其女仙没能成为普通人理想对象的原因,要在于当时“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仙女在阶级层面上来讲要高于普通男性,她的美丽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飘忽之美。仙女给人的感觉偏高傲,相处过程中处于强势地位。通常扮演者拯救者的角色,让男性书去了亲昵的情愫,多了份敬重。这让男子失去了对女性的征服欲和优越感。
女妖都是以动植物为原型变化而来,而人类自认为是万物灵长,不可能降格为物,自然女妖的地位在人类之下。故事中的女妖和人类生活在同一自然环境中,她们虽可幻化人形但改变不了原型的习性。对于普通人来说,女妖的原型不过是花、鸟、狐等,都是寻常之物,如若遇到献媚的女妖,在认知上较易接受。从说文解字的角度看,“妖”暗示了女性色彩和阴性特质。人和妖是对立的两个层面,在普通人的想象中,妖的存在就仰仗于吸取人间的阳气。这也是许多故事中妖魔“采阴采阳”来提升修行的重要方式。中国古典文化讲究阴阳平衡,文学创作者把妖怪和女性经常作为同一符号来表达,侧面暗示了男权文化为中心的社会环境下,女性和妖的生存困境。
这些女妖构成了一个男人心中的情爱乌托邦,世间万物都可幻化成人形向男人求爱。《嫦娥》当中的宗子美娶仙女为妻后纳狐女为妾,满足了男性的臆想。郑振铎所说“观于作者们大多为落拓失意之士,便知其所以欲于梦境中求快意之故。”《聊斋志异》中女性大多一出场就满足了男性的需求,补偿了男性生活的失意,甚至这些女性的出现就是为了男性而生。在这些书生放肆的行为下,闪现着长期被社会、科举制度等长期压抑下的释放。
2.人性解放思潮的折射,摆脱束缚
自周朝始,中国的婚姻关系极不自由,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成为主流。在当时的道德规范下,扼杀了追寻真爱的机会,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自由。蒲松龄所处的明代时期,思想领域出现了一批反对程朱理学的声音。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市民阶层的壮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肯定自己的正当需求,形成追求自由解放的社会潮流。
《聊斋志异》当中的女妖突破封建礼教之大防,处处可见自荐枕席、婚恋自由的情爱故事。人与妖之间只要是有至情至爱,双方可以跨越时空、突破物种的限制,肆意享受男欢女爱。《红玉》中,生动刻画了红玉为爱而动的处女形象。《鸦头》中的狐女不被重金所动,不被折磨所屈服,身居青楼却依然为爱执着,充满希望。蒲松龄的作品中洋溢着对婚恋自由的讴歌。他以女妖这一形象打破了自古以来的成规旧制,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完全背道而驰。作者对女妖的关怀还体现在他对于女妖形象的大量着墨,不少故事直接以女妖名字为名,可见作者对女妖形象的重视。
3.与人结合后的同化,丧失妖性
尽管《聊斋志异》中的女妖想摆脱自身的束缚,追寻自己所想的真爱,但作者在男权主义的创作思想下还是为女妖的行为做了约束。首先,狐女作为异类有很浓的世俗情节,他们很渴望被人类承认,担心自己的身份暴露。女妖的世俗情节和女仙是追求时截然不同的,《云萝公主》中的女仙虽重情重义,但她最终要离开凡世重返天界。女仙身上体现的是一种超凡脱俗的飘渺,和女妖对世俗的渴望形成鲜明对比。女妖和女鬼相比,女鬼生前是人,自然和人世间有着种种联系,她们眷恋的是人世间的情人,而非俗世。
女妖在蒲松龄的笔下向往着俗世,可又被束缚在种种条件下。人和妖的恋情在回归现实后,双方都默认社会的规范和准则,女妖也丧失了妖性。例如,婴宁在王子服家中不得不的收敛自己不受尘世羁绊的性格。在接触过程中,女妖表现出对凡尘俗事的依恋,但对自身充满质疑。莲香可以帮助人和鬼摆脱困境的,却无法改变自身的命运。女妖自荐枕席时总是想着对方不要因为特殊的身份而嫌弃自己,这也是向人类世界同化的一个标志。婴宁由最初的爱笑到最后的“不复笑”正是她对世俗环境的无言反抗,对这种压抑自然人性的社会风气的抵抗。“社会缺乏公正廉明,他的理想难以实现,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使他对人生,对世界充满了悲愤,在现实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他只能通过文字释放自己。”
《婴宁》借女妖的外衣,创造了一个当时社会女性形象的代表。她集女子所有的美好本性,但作者却意识到这样的人物只能活在“世外桃源”中,活在人的想象当中。如果走出桃源,她们所坚持的感情最终将困于枷锁之中,坠入凡世。婴宁如此,《聊斋志异》中的鬼怪世界亦是如此。
四、结语
蒲松龄站在当时的社会前沿,以新鲜独特的文化视角创造了具有革命性质的文学作品。《聊斋志异》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就体现了她们对真、善、美的追求。正是这类与传统格格不入的新型女性形象的出现,猛烈撞击着关闭几千年之久的封建礼教的闸门,从而使《聊斋》保持着永不衰竭的生命力。蒲松龄塑造的女性形象,是中国古代小说人物画廊的空前收获。
[1]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冯川,苏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
[2]马瑞芳.论聊斋人物命名规律[J].文史哲,1992.
[3]马瑞芳.为精神美照亮的聊斋女性[J].东岳论丛,2002(5):91.
[4]袁行霈.中国文学吏(第四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5]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6]张德瑞.论"聊斋志异的悲剧美[J]. 蒲松龄研究,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