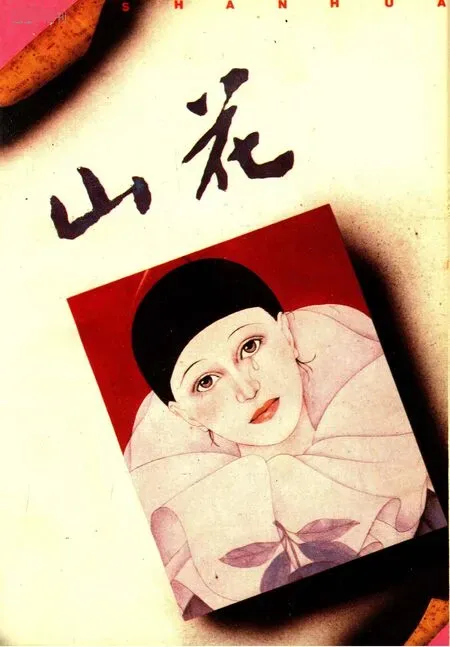虚与实的感知(创作谈)
清 寒
虚与实的感知(创作谈)
清 寒
三十好几的时候,我提笔上路。我的自不量力表明了一个中年妇女妄图从文字奴仆翻身为文字主人的野心。这颗野心,为肉体之外的另一个生命——写作生命——的存在提供了可能。它源源不断地输注热血,滋养着那个幼稚的、写作孩童的成长。
血液质量决定生命质量,氨基酸、葡萄糖、甘油、脂肪酸、维生素、水、无机盐……缺一不可,而血液质量的维持又反向依靠生命主体的自觉进补。这个循环的完成,再现了阅读(为了表意,暂时将生活体验束之高阁)与写作、输入与输出的互为推动。应该说在写作之初,我更多地享受到了写作的自由、轻松和快意。
随着进补范围的扩大,确切地说是阅读精度的提高,尤其是专业性追问的增多,我出现了消化不良。所幸,对象征主义、达达主义、表现主义、存在主义、意识流、新小说、元小说、黑色幽默、零度写作……这些对传统现实主义有所继承或完全背离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追问造成的只是消化不良,不是神经性厌食症。不挑食,注重质量,允许自己有偏好。这样的进补更利于个人文学成长。我欣赏阿波利奈尔的态度,兼收并蓄,立足于优秀传统,并富于实验精神。
说得似乎过于笼统了,这是一篇创作谈,多少应该对两篇小说有所介绍、交代、分析、阐释?我不知道哪种说法更贴切。我始终认为作者对自己的文本进行分析、阐释是件残忍的事。
作家不是评论家。他们更像病人。我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低作家的意思。任何时代的作家都是社会群体中的敏感人群,对常人觉察不到的、肉眼不可见的细小的浮动于空气中的微粒,有着异乎寻常的感知力。这些感知以症状、体征即文学文本的方式呈现,起到了弥补认知空白的作用。当然,呈现不等于真理的确立,作家的责任在于感知、体验、呈现,而不是分析、整合、判断,最后给出一言以蔽之的论断。
如果一定要说点什么,我打算投机取巧,套用一段关于镜像原理的现成解释:当一个声源靠近刚性壁面,由于壁面影响,辐射情况与在自由空间不同,按镜像原理,此时的辐射可看成该声源和一个在对称位置上的“虚声源”(即镜像)所产生的合成声场。
我们所处的生活空间,壁面无所不在,大的社会、小的个体,形而上的道、形而下的器都可以称之为壁面。《虚声源》中的方有德(实声源),在现实壁面(由工作、生活、前妻、朋友、邻居等构成)的影响下,和对称位置上的顺毛驴(虚声源)产生了“做熟悉的事,见熟悉的人,出入熟悉的场所,吃熟悉的食物,打熟悉的呼噜”的合成声场。方有德安心于装聋作哑、装疯卖傻,游荡在安全范围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直到另一个壁面的出现。虚声源不再依附于真声源,他微妙、独立,以神秘的方式抗拒真声源,甚至喧宾夺主,反作用于真声源,合成声场因此发生变化。如果说《虚声源》中的壁面是外置的、明确的,那么《与狼共舞》中的壁面则是内置的、含糊的。真声源与虚声源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抗拒?妥协?主动?被动?不,不是这些词汇独立起来表达的单向性。我预想的是双向、交错,是真正的合成声场的效果。我做到了吗?肯定没有。截止到目前,还没有哪个文本在我回看的时候敢对自己说,没错,就是它。
如果再要说点什么,我忍不住想到了阿多尼斯的那首诗“当我把眼睛沉入你的眼睛/我瞥见幽深的黎明/我看到古老的昨天/看到我不能领悟的一切/我感到宇宙正在流动/在你的眼睛和我之间”。
感谢杨打铁老师和《山花》杂志。想念时,你说我在,一直在。——这就是我理解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