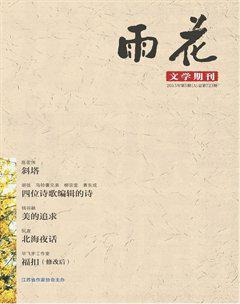马铃薯兄弟的诗
2015-07-17 22:21马铃薯兄弟
雨花 2015年5期
马铃薯兄弟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更不是三个人。“这个人”本名于奎潮。
向前,向前
我站在生命的中段
看生命
生的生了
去的要去了
这个板块的移动
—直在进行
有时我们视而不见
生命,欢迎
可去的人
不必说永诀
这生命的传递带
一直在向前
深渊里
最后的归宿
你们看不见
我已看得见
欢乐的秋天
不必慌乱
同志们
让我们唱起歌曲
挺起胸膛
爱
欲
跨步
向前
一个往返于南京和法兰克福的女人
法兰克福已经熟悉得像你的家
雕塑,地铁
金黄的树叶
美因河中的天鹅
歌德家的小院
还有日光下的吸毒者
红灯区窗口蓝色的小灯
你往返
额头上欧洲的日光已经擦拭不净
而长江水的浑浊
已经在漫长的旅途澄清
三十年代的淑女
她们似乎很喜欢坐在地上
让隔着布匹的玉臀
感受大地的凉
与热
有人喜欢斜倚椅背
这肢体的语言
绝对不会无意义的
因为,多年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看到那样的
参差、安静与含蓄
淡然与希冀
一缕躲在额发里的用心
一丝羞怯中的热忱
乃至初醒的惺忪
一九四九,以它为界
从前的影子被扫除了
连房子
也与昨日告别
设计房子的人
省略了
任何一点的装饰
致罗杰
你把欲望的空画尽了
糜烂人性的场所
每个赔笑的女人
眼中
不易觉察的光
也被你画尽了
她们的身体是真实的
真实到每个隐秘的衣褶
可她们一律是有缺憾的
就像命运的痕迹
罗杰,你是谁
你的眼光永远固定在这些纸上
你把机器用人体的形态呈现
你把寂灭用欲望的形态排列
不幸她们还有肉
还有心
虽然萎缩若无
可一点点的存在
就画出了他们的不甘
厌倦
和深不见底的灰暗
那些极尽风情的身体
那些极尽厌倦的眼
那些乳头
若最新来自土下的花生的果粒子
那种粉艳
可你为什么却把相对的目光
打入不复的深渊
罗杰
什么样的痛
使你把欲望
换算成了绝望
第一缕秋天
第一缕秋天的新毛
从涵洞那端袭来
从女人乱了的头发
微开的嘴唇
白色的牙和
齿间的果肉
吹来
这就是秋天了么?
是的
这正是秋天
猜你喜欢
歌海(2022年1期)2022-03-29
奥秘(2021年6期)2021-09-10
数学大王·低年级(2021年12期)2021-01-01
东坡赤壁诗词(2020年2期)2020-06-04
七彩语文·画刊(2020年2期)2020-03-24
环球时报(2018-08-27)2018-08-27
作文大王·低年级(2018年4期)2018-05-24
环球时报(2018-02-07)2018-02-07
环球时报(2016-03-01)2016-03-01
环球时报(2009-09-10)2009-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