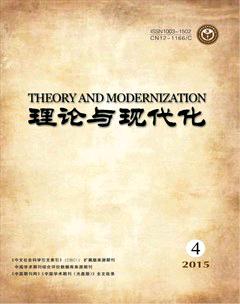从《朗园》到“朗园”:文学空间的文化意义
李进超
《朗园》是天津作家赵玫的小说代表作之一,小说跨越了近百年的历史,通过女主人公覃的生活经历和对母亲的生活的追忆,写出了在朗园这座别墅中生活的几代不同人物的命运,由此也写出了朗园由盛而衰的命运。朗园的主人是覃的母亲,一位最后的女贵族;美丽又忧伤的覃则是现代社会中一个公司的女经理。小说以“朗园”这个城市地点来命名,自然也是将故事情节与矛盾冲突围绕着这个空间而展开的。而且,作为一位在天津成长的作家,赵玫对天津的熟悉与情感是可想而知的,因此,通过小说中的文学空间,总是能寻找到现实的城市空间的影子,这其实也是文学空间与城市空间的对照,以及对空间的文化意义的一种解读。
一、《朗园》构筑的文学空间
小说首先对朗园进行了空间与时间的定位。在一座滨海城市的麦达林道上,“有一片殖民地时期留下来的洋房”(赵玫:《朗园》,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6页。下面出自《朗园》的引文只标注页码),在这条街道上“有一个美丽的别墅叫朗园”,“朗园是一处很多年前由一个有钱的中国老爷在租界区仿照欧洲风格建造的房子”(6)。老爷去世后,覃的母亲就成了朗园唯一的主人。
空间不是割裂的、孤立存在的,而是相对的、关系性存在的。因此,小说以朗园为中心,通过社会关系、人类活动和时间流变,细致入微的构筑出了一个多重关系交结的空间结构,形成了以朗园为中心的辐射状的城市空间构型。小说中,与朗园形成对应关系的城市空间主要有三种类型。
首先,在社会阶层与阶级层面,与朗园形成鲜明对立的空间是建国巷。
朗园所在的一边是在麦达林道上的洋房里居住的贵族们,而建国巷所在的另一边则是在东区的平房里住的平民。建国巷的人们生活贫困,“世世代代是专门为马场道那边麦达林道上的老爷太太和租界区的洋人服务的”。“东区的建国巷是解放后政府为这片城市贫民的集聚地起的名字”(28)。马场道如同一道天堑,把贫民和贵族的居住地分隔开了,也隔开了建国巷和朗园。
后来在朗园居住的,还有萧东方一家。萧东方早年跟着共产党打天下而不断升迁,新中国成立后,他功成名就,在机关里做了很大的官。当他的发妻去世后,他娶了来自建国巷的殷。殷对麦达林道上的洋房无比迷恋,然而,当她胆战心惊的走进朗园的时候,她的建国巷身份却被萧东方的女儿萧思鄙视为“小市民”,而殷所生的女儿也被叫作“建国巷的穷女孩”(32)。
“文革”中搬进朗园生活了十年之后又搬走的还有宇建一家,他们也来自建国巷。宇建的父母都是“工人阶级”,当时的宇建是全市红卫兵总团的领袖,他调查过,住在朗园的“不是资本家的遗老遗少,就是走资派的孝子贤孙”(59)。而萧思依然对建国巷的人充满了敌视和轻蔑,她骂宇建是“建国巷的臭小子”(112)。
朗园与建国巷在物质空间这一维度上的对立,其实是社会阶层与阶级的对立。殖民地时期,朗园里住的是有钱的老爷和太太们,是贵族;而建国巷里住的则是为老爷太太和洋人服务的仆人,是贫民。建国后,朗园里住进了“官僚幕府中的要人”(29),而建国巷中住的则是庸俗贫穷的“小市民”。“文革”中,朗园里的人成为了资本家和走资派的后代,而建国巷的人则是伟大的工人阶级。社会阶层与阶级的对立,本质上也是权力在借助于空间的构型来发挥作用。空间是公共生活的前提,也是权力运作的基础。因此,掌权者总是改造空间,把物质空间作为其权力实施与分布的空间,来实现规训人的身体和控制人的思想的目的。
其次,在人类活动层面,与朗园形成对应关系的空间是维多利亚公园和瑟堡。
“离朗园不远的地方,顺着一条叫马场道的街道向前”(1),有一个维多利亚公园,幽深而宁静,那里曾经是英国人的俱乐部,有钱的英国人每个周末都会来这里。覃的母亲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到过这里。马场道是英国人赛马的跑道,周末他们常常会赛马,也会有很多人观看。
到了覃的时代,朗园的很多故事也与一家叫瑟堡的大饭店有关,瑟堡“非常幽雅而又豪华”,“紧临着维多利亚公园”(11),二者形成了过去与现在的对照。瑟堡里有豪华的套间,有餐厅,有酒吧,也有很大的展厅,覃和萧家子女和宇建的很多时间也是在这个空间里度过的。
朗园是覃的母亲、覃和萧家人的“家”,相对于朗园的私人空间特性,维多利亚公园和瑟堡是有着相似的“公共空间”特性的。维多利亚公园是在租界区建造的,它以异国文化为表达方式,以此来满足洋人和在租界中的华人对娱乐的需要。瑟堡紧临维多利亚公园,其实也暗示了瑟堡的娱乐性的空间特征。因此,此二者都是以娱乐性为主要特征的公共空间。私人空间要具有私密性和封闭性,正如萧家搬进朗园时,覃哭着大喊:“这是我们家,你们出去,你们到我们家来干吗?”(18)其实,在没有外人闯入的时候,私人空间的私密性和封闭性还不甚明显,而一旦有外人进入,这种特性就会明显。与之相对,公共空间则是可以向所有人开放的,公共娱乐空间的繁盛,源于人们对娱乐需求的滋长,这就为人们的社交活动提供了舞台,使人走出封闭的私人空间,拓展其活动领域。
再次,在时间流变层面,与朗园形成空间对应关系的是新建的国际金融大厦。
朗园见证了这个城市近百年的历史变迁,它的命运也走向了衰落。“为了重新规划城市,政府决定将朗园拆除,在此建成一个50层高的国际金融大厦。”(329)无论人们反对与否,朗园还是倒塌成了碎石瓦砾,“新的国际金融大厦在朗园的基址上拔地而起,气势非凡。”(332)富有戏剧性的是,建造朗园的老爷当初的生意就是与美国人合作开办银行,在他去世之后,覃的母亲接下了银行的生意,挽救了银行的败局,成为了叱咤风云的金融皇后。
同样都是与跨国的国际金融有关,随着时间的流变,古旧的朗园成为了消失的历史,而它所在的空间则被新的国际金融大厦所取代。在这里,空间与时间形成了一种戏剧化的叠合。
二、作为城市空间的“朗园”
“城市不但是一个拥有街道、建筑等物理意义的空间和社会性呈现,也是一种文学或文化的结构体。”(张鸿声:《文学中的城市与城市想象研究》,《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这就道出了城市与文学不可分隔的联系。因此,文学必然要投身于城市空间之中, 本身成为多元开放的城市空间的一个有机部分。同样,城市空间也并非一个静止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流变的社会概念。列斐伏尔特别提出空间的社会内涵,“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看起来其纯粹形式好像完全客观的,然而一旦我们探知它,它其实是一个社会产物。”(列斐伏尔:《空间政治学的反思》,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2页)
在《朗园》中,赵玫提到了很多具体的天津城市空间,有些一直存在,有些随着时间的流逝,或改变或消失。马场道至今还在,也成为了天津的一个标志性的城市空间;戈登堂、维斯理教堂则成为了历史的记忆;而五大道上某个曾经辉煌、现在已经破败的小洋楼,就是“朗园”的原型。文学空间大部分是来自城市空间,城市空间不光是故事和情节展开的一个场景,同时也表现了社会和历史的变迁。在小说中,与“朗园”形成对应关系的三组空间,其实都能在现实中寻找到踪影。建国巷,就其空间特性,可以类比于老城厢一带以及各种工人新村,这里居住的也是贫民和工人阶级,他们的生活空间与五大道上的小洋楼也是阶级和阶层对立的体现。维多利亚公园和瑟堡,从空间位置来看,可以与小白楼附近的各种娱乐场所相类比,如,俱乐部、咖啡馆、饭店、酒吧,在这里,人们走出私密的个人空间,进入开放的公共空间,进行各种娱乐活动。新的国际金融大厦,就是小白楼CBD商圈的代表,高耸的大厦标志着城市的现代化和国际化。
就文学空间与城市空间的关系而言。文学空间不只是指文学作品中所再现的城市空间,也包括由文学想象的事物所建构的文化空间。虽然文学空间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城市空间,但更重要的是,文学本身也会成为城市空间建构的重要组成。因此,文学空间不仅仅是城市空间的反映,也是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更是对城市空间的意义再生产。文学空间的生产、文学空间自身以及文学空间的阐释等都是多元的、异质性的、互文性的,对文学的阐释和研究本身就可以成为文学空间介入现实、批判现实的一种空间结构。文学空间不是举着一面镜子来反映城市空间,而是加入了更多内容,把城市空间结成一张纷繁复杂的意义之网。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