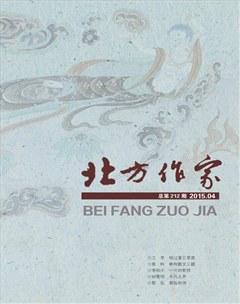吾吉买买提诗歌中的死亡意象
阿卜杜外力·艾萨
摘要:乌鲁木齐市文联主办的《天尔塔格》杂志是研究维吾尔朦胧诗歌的明亮窗口,从此进来的外来影响和从而挖掘的民族内心沉淀是维吾尔朦胧诗歌创作的内外动力。我在此主要探讨研究维吾尔朦胧诗人吾吉买买提诗歌中的死亡意象。
关键词:吾吉买买提;朦胧诗;死亡;意象
当代维吾尔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必不或缺的一部分,也展现了自己辉煌的发展成绩,同时以优秀的现代文学作品迎接了新时期,走向了思想解放和改革创新的新道路。维吾尔朦胧诗歌的独创新颖,正是新时期维吾尔文学变革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对于以严格规范和规则为主的维吾尔传统诗来说,像朦胧诗这样,以独特的形式、深奥的内涵和隐喻的表达为特征的诗歌创作,绝对是绝无仅有的新现象。
1986年,乌鲁木齐市文联主办的维吾尔文杂志——《天尔塔格》试探性地刊登了朦胧诗歌。维吾尔文学《天尔塔格》杂志是以支持青年、支持新颖文艺思潮为其主要口号。此后三十多以年,维吾尔朦胧诗歌逐渐增多,越来越成熟。可以说《天尔塔格》杂志是研究维吾尔朦胧诗歌的明亮窗口,从此进来的外来影响和从而挖掘的民族内心沉淀是维吾尔朦胧诗歌创作的内外动力。我在此主要探讨研究维吾尔朦胧诗人吾吉买买提诗歌中的死亡意象。
一、 死亡意象的基本含义
意象是文学中灵感的产物。意象是诗歌当中组成艺术形象的主要因素之一,大部分诗歌都以意象为审美创作方式。诗人的目的是利用意象,把自己的精神世界表现给读者。也就是说“意象是诗人精神世界和外部世界的交叉点,是意义和形式的完整结合,是精神化的外部世界与物质化的精神世界的统一。”①意象是一首诗歌最重要的艺术媒介。因此,要享受诗歌的词句,我们要进入诗人的精神世界,要感知诗人所运用的诗歌的意象。“要找出文学形式和情感的最重要途径是去发现合适的意象物。换言之,用一系列事物,情景和事件来表达感情;最重要是达到表达内心世界的目的,唤醒内部世界”。②可知,诗人是用意象来给我们表达自己的精神世界。死亡是生命的必然结局,是启迪诗歌想象的永恒的话题。死亡意象是诗人以对死亡的想象和体会为审美空间创造的手法。
二、 吾吉买买提诗歌中的死亡意象
吾吉买买提·买买提是维吾尔族新世纪诗歌的重要代表诗人之一,在1971年,他出生于新疆和田皮山县,目前在和田地区长途客运站工作。1990年他在第三期“新玉文艺”上发表了《我的天堂》一诗后,便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此后,他在各期刊上发表的诗歌作品2000多篇,一些诗歌获得自治区级文艺奖,其中20多篇诗歌翻译成汉语并发表。在他的“诗歌中机械和人,城市和自然,人性的本质和伦理之间是一种不可理喻的甜蜜的矛盾。人类城市化过程中的得失,漫无目的恩爱的火焰和没有爱情的自我破裂作为主要结构因素。”③而且“女人”,“死亡”等意象在他的诗句中的语言应用风格来得以表现。
死亡意象创造的倾向比较多见的吾吉买买提诗歌是我观察维吾尔朦胧诗歌当中表现的死亡意象的一个观察点。比较多见的,常用的“死亡”一词在他的诗歌当中获得神秘色彩的表现,作为人类对生命结局的神秘思考,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出一种神话意识的意象。
(一) 死亡与孤独
作为生活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绿洲”④的人民的一员,他习惯于“用美妙的语言来安慰自己的内心世界,用一种倾向于大海的干旱心理生存下来”⑤的生命。因而,我们会不知不觉的随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孤独和诗人的内心孤单进入无际的诗境。在此,我们会想起这么一句话:“人是感悟深刻而孤单的生物,来到世界的孤独会持续到死亡才能结束。”⑥例如:“我的孤独是孤独,比荆棘⑦还孤独/我的双唇浸入酒里,却觉得是误入/我的悲伤上升到高峰,上升到高峰/没有情人的消息,我要用死亡来得到拯救。”在维吾尔语言当中荆棘是孤单的象征,是个真正的孤单的标志。但是我们看到,诗人却在赞扬比荆棘还孤单的自我。但我们还是感受到了美丽的诗境,甜蜜的孤单,纯洁的诗人的内心。他为了情人而饮酒,情人双唇的甜蜜选择了孤单,走上了为孤单而得到安慰的道路,他的孤独最后引领到死亡,以死亡而创造审美空间得以实现。他写到:“别因我在盼望情人的到来,而嘲笑我/我的情人捉弄了我,别为此说我哭丧/行尸从我的眼前走过,眼盈眶里充满悲伤/我跟着他的棺材,别让我走到他的跟前/我的内心有个杀手,他会随时把我杀掉/我是她的一个奴隶,不要说我胆小/主啊,来了,吾吉⑧来了,他是为了燃烧来的/别让我在地狱的天国里做个无依无靠的孤魂。”他的情人是他的梦想,他在梦想里寻求情人的脸庞、情人的美貌。他想在孤独的沙漠(塔克拉玛干)里面哭泣,以眼泪为安慰自己的情欲。他的灵魂也是他的安慰也是他的杀手,他为了灵魂的安慰选择死亡,因此创造一种又苦涩又伤痛的情歌,内心世界的呐喊。
(二) 死亡为回归大自然
大自然是文艺创作的刺激来源,永不平淡的文艺体裁。从古至今,不管国内还是国外很多文艺创作家都以独特的眼光来观察大自然,从而创造出外在世界和内心空间的契合,给读者带来感悟别样的审美感染力的艺术特色。
从吾吉买买提的很多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为了情人返回土壤,用眼睛来赞扬人间的真情,他在情人的脚下融入土壤那刻,才能看到死亡的花朵。死亡满足他的心灵世界,进而安慰他的苦梦。我们随着甜蜜的苦梦,走入了诗人折磨自己的道路。在我们眼前浮现的是,跟随棺架的一群尸体,跟随这些尸体的是吾吉买买提。这就是他奢望走入的死亡之园,他对死亡的渴望不断升华,不断地涌入他的心田。最终对真主的盼望达到高潮。例如他写到:“我是为了生命,在这条路上遇到悲伤/为了悲伤我在拿笔,对痛苦做了个赞扬/笔下记载的是无边的沙漠,尘土在荒唐的飘扬/沙漠之中嘴唇苦涩,美人为了美酒上场/美人手里拿着都塔尔,弹着没有结尾之歌/她的歌声吸引着着我心,心中涌现着无线的欣赏/情感在不停地死亡,美人注定了我的命运/我是情人,我在孤独,我在哭诉,我在歌唱。”在这些诗句里,诗人说为了死亡而来世,为了悲伤而爱恋。无边沙漠之际,诗人看到情人的身影,情人在唱歌的情景。可是,用较强洞察力的眼光来看,我们很容易会发现,诗人不是在看到情人的美貌,他在梦想里创造出情人的形象,也可能是现实的、具体的,也可能是抽象的、梦造出来的。他为了听到美人的歌声,选择走到无极限的道路(死亡的道路;毁灭自己的道路)。从而得到乐意,从而感悟到生命的伤痛和快感。
生命哲学是痛苦的哲学。诗人为了避免生命的痛苦,赞扬悲伤,赞颂为难自己的现实。他在情人手里无边的沙漠当中渴望恋爱的源泉,渴望跟情人一起拿起都塔尔,唱起木卡姆,情人是他的命运管理,他的命运以情人的歌声、嘴唇来注定。他在歌唱,在审美的空间里面赞扬着孤单,赞扬着死亡的到来。从而给读者创造一片深刻的审美空间,联想动机。
(三) 死亡的审美意义
没有审美意识的诗歌,不仅不是好的诗歌,而且是失败的诗歌。虽然他的诗歌是一种非理性的表现,不过他的诗歌还是为我们的审美欣赏创造出一种悲剧之美。当我们读到诗人在诗歌当中美丽地死去以后,才能感觉到艺术的优美,诗歌的魅力。例如:“我在狂欢,我在设想,我想杀掉我的死亡/生命在狂,花在盛装,为此欢乐是个梦想/日夜都在想念情人,日夜都行走在这条路上/这是兴旺,我要情感都在心中燃烧光/我的陵墓在美人怀里,我也别无所求/她的怀里,她的心里,吾吉要的永恒天堂。”在如此美好的诗句中,我们会意识到诗人的悲痛达到了高潮,因而刺激到我们心灵深处的艺术之美。他在情人黑黝黝的头发中,眼睛里发出火焰般的光芒,他日夜不停的唱着情歌。他迷醉的身体和灵魂,是我们对诗歌陶醉。
“死亡”首先呈现的是生物学意义。个体生命的死亡,可以看做宇宙有机体能量衰竭或终结的微缩的象征。反过来,个体生命的短暂存在形式又启发了人类对于宇宙周期命运的担忧。在这一大一小所形成的张力中间,死亡成了生命存在最美的奥秘,或者说,它是一切生命哲学由此诞生的源点。
当我准备探讨“死亡”的时候,影响我思考的另一个重大因素是时间。我想说,时间的本质就是死亡,或者说,时间是由无数个出生和死亡原子构成的直线。在这里,我直接把诞生与死亡画上了等号,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一回事。然而奇妙的是,这条直线迅速地被死亡所具有的美学力量所打破,它不再是直线,而成了千回百折的密网;它不再是滑的一根棍子,而是纷乱如麻的一团黑发。只说在死亡的运作时间的枝杈发生了逆转是不够的,事实上,时间线上的每一个原子间的缝隙都在发生爆破,并画出一幅幅生命图像。
就最直观的形式看,死亡却是一种结束,它的宣告是为了给别的生命的存在腾出空间。那些流芳百世的人们,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一种文化,而不是生命。但我们也不能说,一个人死了之后,他的生命证据就立即消失。大多数情况下,他的遗物、他的精神,以及别人关于他的回忆还要留存很久。文学提供了最佳的载体。在文学里,时间是非线性的,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当我们想起作品中某个过去的人物时,我可能想起的是他生命中的任何一个点,这取决于我对他的认识和理解。在此意义上,出生和死亡一样,随时都能发生。在这里,形式逻辑完全失效。
三、 结语
总之,诗人吾吉买买提以孤独、土壤和情人等意象概念将死亡描写得淋漓尽致,以抒情死亡的方式表达了对人生、世界和生命的意义和含义,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一个哲理问题。“在认真地解读他诗文之时,我们发现除了死亡之外,对死亡的淡然和对幸福的追求渗透在他优美的诗行之中。他诗歌创作体现了所有朦胧诗普遍具有的未确定性、含蓄型和神秘性以及跳跃性等基本特点。”⑨因此,他诗歌内含丰富,意义深奥,如果想要真正地体会和理解他诗歌中的未确定性意义,我们需要从哲学和美学的视野对其加以客观而科学地观察和研究。
参考文献
[1] 艾洛特:《诗歌论文集》,中国国际文化书局,1989年13页
[2] 吾吉买买提·买买提:《心醉的木卡姆》(诗集),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2月(维文版)序言
[3] 艾塞提·苏莱曼:《被埋在塔克拉玛刊的精神》,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维文版)23页
[4] 同上,58页
[5] 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读本》,商务印书馆,1981年(汉文版),48页
[6] 孙世军:《解读现代诗歌当中的意象》,《深圳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4期
[7] 阿迪力·图尼亚孜:《圣人之地的夜晚》,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125页
① 艾洛特:《诗歌论文集》,中国国际文化书局,1989年11页
② 艾洛特:《诗歌论文集》,中国国际文化书局,1989年13页
③ 吾吉买买提·买买提:《心醉的木卡姆》(诗集),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2月(维文版)序言
④ 艾塞提·苏莱曼:《被埋在塔克拉玛刊的精神》,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维文版)23页
⑤ 艾塞提·苏莱曼:《被埋在塔克拉玛刊的精神》,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维文版)23页
⑥ 艾塞提·苏莱曼:《被埋在塔克拉玛刊的精神》,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维文版)23页
⑦ 荆棘 —— 维吾尔语里是孤单的、孤独的象征。
⑧ 格则里 —— 维吾尔文学的一种诗歌创作模式,格则里的最后一段诗人会提起自己的名字或者笔名。
⑨ 阿迪力·图尼亚孜:《圣人之地的夜晚》,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