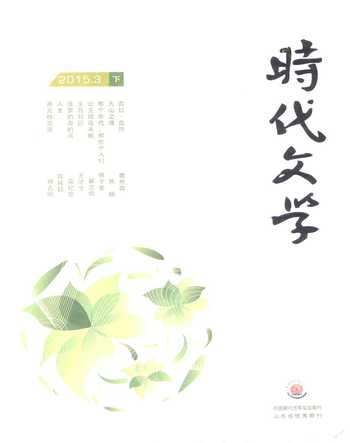家
魏礼庆
甲午大寒之日,回到山东老家,探望卧床的母亲。一进家门便听见母亲的呼唤,悲凉中带着惊喜,惊喜中又带些嘶哑,似乎还有些半信半疑。一声乳名的呼唤暖遍全身,多少岁月往事涌上心头,让数十载漂泊的心有些难以自持。几个月不见,一直身体康健的母亲怎会卧榻?可见秋叶怕风霜啊。
母亲并无大碍,只是受了点风寒,看到我归来,病情好了三分,兴奋地跟我聊起家常,邻里亲朋,世事变迁,唠里唠叨之中溢满对儿子的慈爱,嘱托叮咛之中浸透对未来的憧憬期盼,也让我感到老母亲看透人间世事的练达和光环下的寂寥。对村里的人和发生的事我点头答应着、附和着,有时插上几句,离家五十载,一些后生如院里院外的小树,长出一茬又一茬,让我难以辨认榆和槐,而我熟悉的那些大树大多已成记忆,少数的几棵也是老树枯枝了,让我感到岁月的无情。
正房和院落依然是文革前离家时的模样,只是围墙和门口略作些翻修,水磨和石磨已经搁置多年,但也完好无缺,满身的纹理显现出石匠的技艺。我曾多次提议,将房子推倒重盖或者进行大的翻修,让父母住得宽敞一些、舒服一些,父母没有同意,说还是老房子好,接地气,住着舒坦,也留点念想和回忆。我有时在想,新房好盖,旧房难留,也许是父母为我着想,让我和远在他乡的孙子永远记住家的模样,就像她特意为我保留的儿时的用具和衣裤,每一件都是一段难忘的回忆。母亲不识字,这是她书写日记和记录历史的一种独特方式。
每当目光触摸到那些水磨、石磨,走不完的圈圈路,使我想起童年,想起故去的奶奶、姑姑、婶子大娘和弟弟妹妹,想起发生在院子里的人和事,想起那艰难困苦的岁月。特别是到了腊月,为了能让一家八口能吃上年糕和馒头,母亲的裹脚曾经让大地颤抖,让冬雪消融,让星光落泪。走不完的圈圈路,燃不尽的寒冬夜,推出个母子情深,推出个志坚梦圆,磨出一道道生活的金光灿灿。为了我们兄妹能够穿上件像样的衣服,窗内的油灯,从早亮到晚,从晚亮到鸡叫,偶尔在睡梦中能够听到母亲锥刺股的哀叹。那盏小油灯啊,照亮天涯海角的小油灯啊,竟然还静静地躺在水磨底下,我悄悄地把它带回了京城,时常点亮在心灵深处。
家,虽然不大,却寄托着几代人的情感,承载着几代人的期盼,也记述着多少次离合悲欢。每当出门在外,特别是常驻国外的那些年月,它就是温馨的港湾,就是空中加油站,就是游子的梦萦魂牵。每当银鹰飞过泰晤士河,每当依偎在驻澳大利亚使馆的“望北亭”边,一想到大洋彼岸的家就感到亲人与我同在,祖国与我同行;每当在康桥边的驻美使馆大院里加班加点,每当在墨西哥湾畔的那座军营里(驻休斯敦总领使馆)迎来国庆新年,一想到山东半岛的家就感到热血奔涌,温暖无限。每当跟海外友人讲起,幸福和激动总是闪烁于眉宇之间,因为父母健在,我是一个有家的人。
家,西方人讲“East, west, home the best”(金窩银窝不如草窝),也讲“where?I am where is my home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我家),其实这两句并不矛盾,而是上下关连,以自我为中心。而印度哲人帕当巴·桑杰在《修行百颂》中把家视为牧民的放牧地,哪里有牧草那里就是家园。而我们中华民族往往把父母的所在地当作家,那是源于爱,源于孝悌,源于对“忠孝难全”的补偿,因此有了春运,举国大串联。前年一位美国休斯敦大学的女生在我家过春节,她不无感慨地对我说,“魏先生,我有三件事想不明白,一是中国的春运,几亿中国人不顾千里劳顿回家过年,二是十几亿中国人在同一时间吃饺子放烟花,三是北京的庙会,几个公园同时开放,人山人海,气象万千。”何怀宏在《梭罗和他的湖》中把故乡比作树叶,透过它可以看出春夏秋冬;席慕容则把家园描绘成“魂魄夜夜归来,微风拂过化作满园郁香”;而我则认为家是一粒种子,根植在心灵深处,家是游子对故土的依恋和承诺,家是链接几代人情感的纽带。
年少时从这里扬帆起航,上下求索,架设桥梁,出航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而锚地停留的时间越来越短暂。母亲的期盼压完了庭院的砖石路,母亲的伫望磨光了村口的桥墩,忠孝难全也让我泪洒征程。现在呼唤自己乳名的亲人中就只剩老母亲一人了,回想起来,人过甲子,依然有人直唤自己的乳名是多么幸福啊!
我也曾几次许诺,下次省亲一定多住几日,可心里明白即便多住几日也不过是多几日应酬,人在旅途,舟行大海,顾不上身边的风景,只能全力审慎而行。而母亲总是笑着说,咱们潍坊是风筝的故乡,风筝人喜欢风筝翻飞云天,咱家附近有条白浪河,浪花翻滚腾跃,如雪、如棉、如练,那是河水穿越岩石时奏响的生命赞歌。放心吧,儿行千里万里,永远走不出娘的视线。
几年前父亲故去了,但是母亲还在,家还在。兄弟姊妹还是照样无数次回来,几个小家聚成一个大家,母亲乐,大家跟着乐,母亲流泪,大家一起流泪。如果有那么一天,母亲也仙逝了,我还经常回来吗,这里还是我的家么?想到此,心被扎了一下,泪水夺眶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