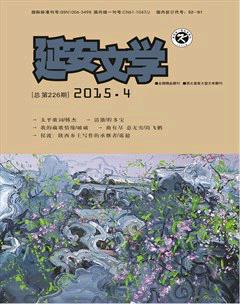刘成章的精神世界
刘江
为什么要等到下辈子?与刘成章先生见面后这话一直萦绕在心头。
认识刘成章先生先于他那掏心掏肺热腾腾的文字,后于他那从心底渗出的浓墨重彩的画卷,真正见面是他从大洋彼岸归来在西安举办《故土情节“三页瓦”画展》期间约定的一场电视采访。走出电梯先生已手拄拐杖等在门口,一脸慈祥,一口乡音,像是在老家村口的大槐树下见到久违的一位长辈,拘谨、陌生荡然无存。
因了眼前的画展首先就谈到了画,因为许多人都好奇先生由“文学陕北”到“水墨陕北”转换的缘由,为什么想起要在晚年突进另外一个艺术世界?他满脸含笑地回答:我是七十四岁才开始学画画的,我原来没有画画的底子,遇到一些难以用文字表达的东西,就想要是能当一个画家那该多好,就给老伴说我下辈子要学画画,说了几次有一天突然就灵醒了,我说为什么要等下辈子,下辈子是一个很虚幻的东西,我不如现在就开始。就那么一闪念,我马上就买笔买墨,开始就学画画。我们陕北人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爷不叫自寻死。活过七十三到了七十四就等于到了下辈子了,就应该活出另一种模样,我把我的下辈子拽过来了。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活出两辈子。
为什么要等到下辈子?这一问让我沉思良久,像是专向我发出的当头一喝。懒惰之人想的是过了四十不学艺,告别朝九晚五,迈过花甲之年,总觉得这一生已是盖棺论定,偶拾些零碎文字,也多是为了散淡与消遣,毫无志向之说。听先生的一席话,耳红脸热,手心里悄悄渗出了一层虚汗。
采访是在曲江亮宝楼的展室里举行的。站在刘成章先生身后欣赏他的一幅幅画作,就像跟随一位秉烛的智者走进一座宝库,他手中的明烛不仅使我看到了宝物的绚丽璀璨,而且照亮了我的懵懂愚钝。他文字中气势磅礴的排比成了浓墨重彩的高天厚土、成了五彩泼就的母亲河,波涛翻滚,颠山倒海;那灵动的诗眼则成了一处处工笔巧点,真是“散文与诗皆成画”!欣赏的愉悦唤起我强烈的共鸣和表达欲望,但这欲望又使我深深地感到感觉和表达之间有着无法拉近的距离,而我的汗颜不仅有时光的虚度更有自己的弱处和欠缺在先生面前无法遮掩的窘迫。
静静地听先生的讲述犹如欣赏一部人物传记片,从画屏首先走来的是一位吹着柳笛的童子,他在那“腾跃过老虎的土地”上步步生风。先生的父亲刘作新是载入史册的革命先驱,1925年加入共青团,一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支部和延安区委负责人,领导了当时的“非基运动”和“农运”工作,被选为肤施县农民自救会负责人,赴西安中山学院农民运动班学习并出席了陕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为此遭伪县政府逮捕关押。出狱后,经刘志丹提议由组织派往位于永宁山的保安县(今志丹县)永宁高小担任校长和支部负责人。1931年支部遭受破坏后重回延安亲自创立第一完小并任校长,以延安教育局督学、民教馆馆长等身份为掩护,担任地下党支部书记。党中央和毛主席进驻延安时,他亲自带领党团员、学生和群众出城迎接,并在欢迎大会上代表地方党组织和延安各界发表了发自肺腑的演讲。1937年7月国共合作期间受党派遣到庐山受训半月,返延后受到无端怀疑和猜忌,被边区保安处以“对市委不作主动汇报,读起古书来了”为由拘留审查,冤死狱中,年仅28岁(《延安市志》)。当时先生尚处襁褓之中,母子俩颠沛流离相依为命,经受着炮火硝烟和世事艰难的双重煎熬,后来在父亲战友的呼吁和组织的关心下得以进入延安保育小学,接受教育。先生在他后来的散文《老虎鞋》中满怀深情地写道:我过满月的当儿,志丹伯伯牺牲不久,同妈妈忍着巨大的悲痛,伴着窗前黯淡的麻油灯,一针针,一线线,为我赶做了满月礼物……这老虎鞋穿在我的脚上,虎耳高竖,虎须颤动,虎牙闪光,挟带着永宁山的雄风,播扬着永宁山的正气,仿佛只要长啸一声,就能掀起人们的衣襟。我这块只会哭叫的嫩肉疙瘩儿,仿佛立时长大了,威武了;我的一双嫩得像小萝卜一般的小脚片儿,仿佛立时变得能踢能咬了……我今天把这件事情写出来,还有一点想法,是为了自勉。我应该时时记起,我的一双脚,是穿过同妈妈亲手做下的老虎鞋的。那是我此生穿的第一双鞋,山高水长的老虎鞋。
他说,母亲生下我,割断了脐带,但把胞衣埋在了黄土里;和母亲连接的脐带虽然割断了,但和黄土地的连接又生成了,生成了另外一种脐带,我永远是这片黄土地的孩子。延安的新文化感染着他。延安满城的歌声笑声感染着他。延安昂扬向上的社会风气感染着他。他从小就有了自己的志向:长大要当作家!
童年的磨难造就了一颗善良敏感的心。坚定的志向激励着一颗向上的心。先生中学时期创作的九首新诗被选入《陕西省青年诗选》,1957年他顶着诗人的桂冠步入大学校门,到延安歌舞团工作后他又由诗而词、而剧,创作出了《圪梁梁》《三十里铺》等一批高扬远播的作品,进入新时期他“中年变法”开始散文创作。《老黄风记》《高跟鞋,响过绥德街头》《安塞腰鼓》《山峁》《扛椽树》……写陕北的山雄浑辽远野性大气,写陕北的人率真豪爽重情义敢担当,“摹写之物与胸中之情密切渗透,感情的抒发几近物我两忘”评论家赞美他的作品“具有醉倒人的力量”,他们惊呼:写陕北,谁也写不过刘成章了!1998年,先生的散文集《羊想云彩》一举夺得首届鲁迅文学奖。
评论家说,刘成章的散文有诗意的“土”。他说,如果说我的散文中有诗意,就是陕北民歌影响的结果。这与我在延安长大的经历有关。我追求的“土”是开着花长着树的“土”。我的画和散文有共同点,追求别样的面貌,尽量和别人不一样,走的是“野”路子,从“师”的是自己的心。
他是一位歌者!他是一位陕北的歌者!
读刘成章先生移居海外后的文章和画作,跃然纸上的是那浓得化不开的对故乡母土的思念,你完全可以想见那夜不能寐的披衣疾书、那词不尽意时的泼墨长啸!面对洋山洋水时时处处都能勾起他对家乡母土的牵挂和感念,一转眼那天上的云就化作了家乡的羊,美国的山也化作了家乡的山,那小路、山村、鸡鸣、狗吠、乡音、热语、如滚滚热浪扑面而来……我突然明白我现在其实是一个漂泊者,流浪汉,可悲游子。我想恐怕只有像我这样的人,才能体会到家山对于一个人生命的无可比拟的分量。因为那上面寄托着你全部的情意和思念。因为超量的乡愁使你痛楚得难以自持。啊!瓜连着蔓蔓连着瓜,不想家山再想哪?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为儿为女起身难!马茹子峁峁糜谷坡,快刀子也砍不断你的我!天上无云星星稠,多会儿能踏上回乡路?(《家山迷茫》)
所以,先生说:出国,出国是很痛苦的事情,起初感觉就像死了一样。虽然网上、电视上能看到陕西、能看到延安,但不能够沟通交流,就像在天堂或者地狱看人世,但我已不在那里。非常痛苦!
今年春节前,我们延安电视台收到了刘成章先生特意从海外托人传来的电视散文《天天看日落》:当我又看到家乡落日的时候,我忽然一惊,我忽然听到了母亲的声音。我忽然意识到:母亲,母亲,我的母亲我的亲娘,你就是这轮落日这轮落日。可是母亲!原谅孩儿吧原谅你的不孝之子,不孝之子晚回来一步,你已经落去了!你已经深深地埋在黄土之中,你过得好不寂寞!好不凄楚!但我看见你的光芒已把黄土烧透,你的坟头已开了一簇红艳艳的花朵。我知道母亲,我的朝思夜梦的母亲我的太阳,我知道你总有一天会重新升起来的,只是你一辈子操劳不息,你实在太累了,你现在也应该歇息歇息,在歇息中重新积攒你的光芒,然后有一天重新出现在我的眼前,照暖我的周身。母亲母亲,母亲啊!我是唱给你的一首其声哀哀的信天游,面对你,我是一首永世也唱不完的信天游啊,我将在你的坟头边飞旋飞旋飞旋飞旋,只要你不重新升起,我就声声迸血,八百年不绝。这和泪泣血的肺腑之言一经播出,便在观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采访中一提及此事,先生又是泣不成声。
这是儿子对母亲的思念!这是游子对母土的眷恋!
为什么要等到下辈子?“天地转,光阴迫”这是鞭策,也是忧患,是知识分子的担当!
采访中,先生回忆说,1947年党中央毛主席撤离延安,国民党占领了一座空城,但他们还要庆祝,蒋介石还要来视察。他们便组织小学生去欢迎,把《东方红》改成蒋介石的颂歌,本来凑巧可以押韵的,但又不让直呼其名,让孩子们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蒋主席。”弄虚作假又不顺口,结果娃娃们一开口就仍然唱成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成了极大的讽刺和政治笑话。他说,你看他们腐败无能到何种地步,连自己的一首歌、一部剧都没有。一个政权的腐败首先是文化的腐败。
那一刻,我脑子里浮现出的是先生的《读碑》,那三五九旅大生产运动时在南泥湾九龙泉立下的烈士纪念碑,他说我在想:要是把每一个名字都复活为一个血肉之躯,那么,他们足足可以把多半条川道站满!要是他们又像开誓师会那样高呼,那么,这条川道将震响着一片多么恢宏的声音!
这声音,应该像警钟长鸣!
为什么要等到下辈子?这是刘成章先生对自己的鞭策,也是对所有人发出的倡议。
先生的创作由诗歌起步,由散文走向世界,移居海外后在74岁时又突入画坛,他的作品“多取材于给他的生命打下深刻烙印的黄土地,构思脱俗,着色大胆,看上去斑斓多姿,有夺目逸神之感,让人眼前一亮”,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光明日报》《文艺报》《西安日报》等多家报刊纷纷刊载,美国洛杉矶的华文文学期刊《洛城作家》每期都以他的画作封面,他的画集《画一画山河雁影》由英国一家出版社出版,并被十余家图书馆收藏。先生曾说过,一个人的突出才华到底在哪儿?常常连自己都认识不清。没法子,只好多尝试几种艺术形式(尝试的过程就是认识和发现的过程),才能最后摸清自己艺术细胞之所在。不过,他从前写诗、写歌词、写剧本的功夫,也没有白费,它们在散文中全都派上了用场。如果说,他的散文是从他原先的诗、词、戏的精神沃野上茂腾腾地“再生”起来的,那么他的画则“是从心底泛出的,是本真性情的流露”,“他的画笔和人们的经验拉开了距离,发现和携满了浪漫气息,使陕北美得和她的民歌一样”。
画展结束北京出港,先生发来消息:我把我的散文集《家山迷茫》给你发来200本,托你转赠给家乡的图书馆和爱好文学的朋友。我接到书,先生已在大洋彼岸,开卷在手,一行热腾腾的文字赫然入目——我想向一切辛勤写作的文友们遥致一句心里话:让我们怀着对中国文学的赤诚比赛比赛吧,让我们内心深处的茫茫山峦中都能蒸腾出一派浩荡云气吧——那就是,看看二百年后或五百年后,谁的至少一篇作品或者一句话还鲜活于世上!
办好赠书手续,把家乡图书馆的收藏证照片发给先生,他说“一种强烈的归宿感和幸福感笼罩着我了”。我分明看到了大洋彼岸凭栏远望的目光!
我的眼睛潮湿了。我被先生的赤子心故土情所感动。这种敬意发自心底,它使精神走向纯洁,它使生命走向神圣!
责任编辑:侯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