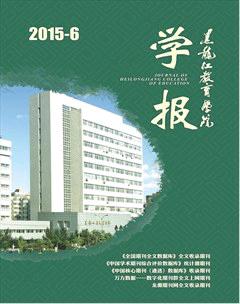以张三影的“影词”为例谈王国维的“出入说”
马玥+周天来+马沙木嘎
摘要:王国维先生的“出入说”包含三个层次的含义,张先的“影词”典型地体现了“出入说”。张先词的独特之处便是虚实之境的创造,而这种审美境界在直观上突出表现为物影的描绘(入),在此基础上形成词境的朦胧清幽之美(出),以此表现了宋人本质上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审美标准。
关键词:张先;宋词;王国维;出入说
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7836(2015)06010702
王国维先生的“出入说”包含了三个层次的意思:
其一:“入乎其内”,强调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体验的深刻性。不仅从大自然和日常生活获取生动新颖的素材,而且能与日常生活和自然万物打成一片,这是创造艺术境界的基础。即所谓的“重视外物之意”从而达到“与花鸟同忧乐”。
其二:“出乎其外”,即“反观”,在先前所创造的艺术境界当中寓含作者通脱的胸怀和哲理性的思考,以及超越功利目的的审美艺术感情。从而创造出艺术的虚实之境,而虚实结合是中国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即所谓的“轻视外物之意”从而达到“以奴仆命风月”。
其三:无论是“出”还是“入”都要紧紧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它既是艺术创作的出发点也是艺术创作的归宿。
张先(990—1078),是北宋年寿最高的著名词人,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他善于通过物影来表现景物的动态美和朦胧美,并因善写“影”而得“张三影”的美名。当然,他这样的成就也与他的另一个身份有关,因为他同时也是北宋一位杰出的画家,他在绘画方面的技巧再融合文人和艺术家的感性,从而为词创造出独特的美学意境。他的词典型地体现了王国维先生的“出入说”。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影”的描摹和审美空间的创造
张先注重从大自然和日常生活中获取生动新颖的素材,而且能与日常生活和自然万物打成一片,即王国维所说的“入”。如果说其他词人所做的词中的审美意境是通过审美距离来实现,张先的词便是从审美空间中挖掘。他的“入”更具有深刻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用物理上的术语来讲,其他词人的意境产生对于读者来说是一个直射的过程。例如:苏轼的《浣溪沙》“惭愧今年二麦丰,千畦细浪舞晴空”,我们在脑海里会立刻联想到一望无际的麦田在风的吹拂下随风起浪,自然清新的乡村景色。再如柳永的《望海潮》“烟柳华侨,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我们眼前马上会联想到杭州繁华富裕的都市生活和丰富多彩的市井风情。张先的词,对于读者来说却是一个反射的过程。“中庭夜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木兰花》),“那堪更被明月,隔墙送过秋千影”(《青门引·春思》),“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天仙子·水调》),读者的联想逻辑,则是由地上的影“扬花影”“秋千影”“花影”“絮影”然后再到形成物影的物本身。这样便延长了联想、想象的心理时间,增强了联想、想象的空间感,扩大了审美空间。
另一方面,作者在构图上匠心独运,善于图像的构思和色彩的搭配。“其间折高折远,自有妙理。”这就是说必须符合艺术上的构图原理。正如宗白华指出的那样,中国人的空间意识是节奏化和音乐化的,“空间在这里成为一个布置景物的虚空框架,而它自己也参加进全幅的节奏”[1]。作者在塑造意境时总是先给这些物象置一个容器,可以是“池馆”或是“庭轩”或是“楼头”,然后在这个有限的空间内布放一些细小的物件,比如秋千、花、阑干、柳絮、门。在大的背景下,这些个物件不会给人狭小逼仄、密集拥挤之感,反而让人觉得很松散。这样的构图法实则与绘画中的留白有异曲同工之妙。清人笪重光在《画筌》中谈到:“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画处定多属赘疣,无画处皆成妙境。”在结合了绘画的构图原理后,即做好了空间的处理。在时间的处理上,作者一般限定在晚上。在月亮的照拂下,万物染上了一层朦胧的色彩,物影与物交错呼应,虚实相交,整个画面更加美丽动人。
二、空明的心境,造就兴象玲珑之美
在北宋中期禅宗对文人的影响越来越大,文人禅宗化和释道文人化成为当时的风气。此时文人禅宗由外显而内转,即通过内在的顿悟与超越而轻视甚至否定外在的形式,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词人更加注重心性学养,以空明超然的心态看待世俗人生和自然外物。同样,对文学创作而言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即促进词人审美视野的纯熟。
通过此种视野的关注世间外物便能超脱世俗实用方面的考虑和功利化目的。取而代之的是用艺术的眼光和纯自然的心境看待眼中的事物,即王国维先生所说的“出”,进而达到“以奴仆命风月”。通过五官体验到的声、色、味、形而生发开来,创造一个审美的艺术境界。在这个艺术境界当中,物象的朦胧塑造并将它们如盐入水般地巧妙组合,形成虚实相生的艺术境界。张先创造的这个艺术境界既真实又虚幻,我们仿佛置身其中,似曾相识。但作者置笔的朦胧与虚幻又使我们产生了陌生感和一定的距离。在这种或虚或实的氛围当中,读者的心里也存在着远近感受的变化,在这种变化当中产生了美感,此种美感直接为心灵所感受。他的《系腰裙》(惜霜残照夜云天。朦胧影,画勾阑。)上片为空蒙之景,在景物上涉及到了“霜蟾”“勾栏影”“东池”“荷”联想到的景“叶字”“藕”“莲”,秋月当空,栏杆投影,东池一片幼荷初放,荷叶在月光下闪动着碧玉般的色彩`。整体感觉清新、自然、明净,意象空灵、玲珑。在这样的氛围下词人感叹“欲寄西江题叶字,流不到,玉亭前”。接着,由此景又产生“问何日藕,几时莲”,将人生有限与明月的阴晴圆缺相连,表达了词人期盼团圆的心情,也揭示了人生聚少离多的悲剧处境。
张先在景物描绘上为了突出神清骨冷,朦胧清幽,将白描作为景物刻画的主要手段。所以我们通过文字也许并不会看到任何颜色,但是文字背后所指涉的事物却极富色彩感染力。他的《青门引·春思》便是采用了白描的手法。“风雨”“庭轩”“残花中酒”“楼头画角”“重门”“明月”“秋千影”,看似无色无情但句句着色,处处含情。读者在读到这些景物时便会产生联想,物形的再现是伴有色彩的,这便是其高超之处,在色彩运用上,真可谓是不琢一字而尽得风流。这首感春怀人的词作所体现的离怀春愁正是由这些清冷之物表现出来。夜深、酒醒、重门深寂、秋千影更是令人忆及荡秋千的伊人倩影。正如宗白华所说:“文艺不只是一面镜子,映现着世界,而且是一个独立的自足的形象创造。它凭借着韵律、节奏、形式的和谐,色彩的配合,成立一个自己的有情有像的小宇宙;这宇宙是圆满的自足的,而内部一切是必然的,因此是美的。”[2]正因为这样,联想和想象力便十分重要了。又因为在作品中没有色彩浓淡的强调,因而每一位读者所想到的画面皆具有唯一性。兴象玲珑的审美形象的创造,极希微睿渺之致,并带给读者洗净铅华的快感。
三、人与自然的完美契合
人与自然的关系,引入到文学创作活动当中实则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是情与景的关系。化景物为情思是虚实结合的正确定义。中国古典美学的中和范畴,将天人合一,物我一体作为最高的审美标准。物亦我,我亦物,使主体和客体浑融一体。这样的浑融实则在背后暗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独立自由的关系,即王国维先生所说的“出”“入”。道家提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唯一”,儒家提出“万物皆备于我”“与天地参”。意境的创造是在突出人与自然和谐的一面,寻求人与自然的“不隔”之感。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对“隔”与“不隔”做了精湛的阐述。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惟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云《少年游》‘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形色苦愁人话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3]从中可以发现,王国维注重的是自然之境的描绘,形象思维的创造,而非典故、哲理的借用。
张先《木兰花》(龙头蚱蜢吴儿竞。)这首词描绘了江南寒食节的风俗。上片主要是白昼的描写,以动景为主。包括赛龙舟的男儿,荡秋千的女郎,在郊外踏青、探花,一直游乐到夜晚才散去,表现欢乐、开朗的心境。下片入夜,主要描写静景。词人的视野由远收回到池院,中庭月光,树下杨花,一派清明。此时,更多的是流露一种沉思和忧伤之情。日间的喧闹到夜深的清寂,一动一静,一人一物,一情一景。在自然与人的交互中实现了内在与外在精神气质的平衡。此时的外界自然已经活了,它听懂了抒情主人公的言语,词人与杨花、与飞影、与月光等自然景物脉脉相对,感情随着自然物景的转化而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四、结语
综上可知,张先词的独特之处便是虚实之境的创造,而这种审美境界在直观上突出表现为物影的描绘(入),在此基础上形成词境的朦胧清幽之美(出),以此表现了宋人本质上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审美标准。对于日益忙碌和快节奏的现代都市生活而言,张先词无疑为现代人逃离城市喧嚣嘈杂、返璞归真、回归心灵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途径。
参考文献:
[1]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2]宗白华.美学与意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王国维.人间词话[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