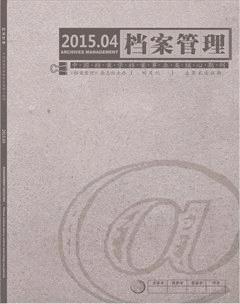档案与文学的发展关系
卫巧丽
自古以来我国的档案工作,就是和当时文化学术的发展密切相连的。档案与文学作为两种文字传递信息的不同方式,看上去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却在各自发展过程中,呈现直接或间接对历史的总结,对现况的总结和对未来的预测。在上古时期中国开始出现文字并被大量用于记录时事之时,随之而来出现的也是文学创作和档案记录的萌芽时期,从这一层面而言,二者可以说是出自同源。但在二者各自发展时,分别着重于各自特色的重点:档案一直沿袭了记叙的真实性,而文学则与历史记录分离,逐渐加大了文人的个人情感比重,开始进入了文学的自觉时期。
一般地,档案是指人们在各项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各种形式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记录。我国古代的档案,在各个朝代有着不同的称谓。商代称为“册”,周代叫做“中”,秦汉称作“典籍”,汉魏以后谓之“文书”、“文案”、“案牍”、“案卷”、“簿书”,清代以后多用“档案”,现统一称作“档案”。
档案作为最真实的原始记录,涵盖了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的内容,而文学从艺术加工的角度反映形形色色的社会百态,多样人生。因此,基于档案史料的文学作品为数众多。可以说,在二者各自的发展历程中,源出同根,生而分枝,而最后所达到的反映社会的目的方面,又是殊途同归。
关于档案与文学二者在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影响,本文将对这方面的研究做一个综述,以及对目前的研究状况进行相应的参考意义。
1 档案与文学的同源
从上古时期开始,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大量丰富、珍贵的原始文字材料,这些材料中历史最久远的那部分,因其最体现人类进程中的智慧精髓,文学家称之为“文学”,史学家视之为“档案”。显然,档案与文学的源流是不易理清的,作为人类最珍贵的文化遗产,档案与文学的关系则是密切而深远的。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最古老的档案就是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文字虽然不多,但涉及内容极为广泛:记载祭祀、战争、狩猎、农事、气象、灾害等。几乎包括了当时民生的所有内容。甲骨卜辞的最初作用是用于对事件的占卜。殷商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对天象等一系列自然现象有着天然的敬畏之情,对各种自然现象以及个人的生老病死寄托于神灵的启示。将占卜询问的事情刻于龟甲兽骨之上,然后用火焰灼烧钻凿之处,根据甲骨背面的裂纹来判断和解释吉凶之兆,最后把占卜的事项、内容和事后的结果刻在上面。一块完整的甲骨卜辞,上面大体上包括叙辞(前辞)、命辞(问辞)、占辞、验辞等几个部分。在无形之中,这种甲骨卜辞开始形成我国最早的一种文书档案形式。而这些卜辞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叙述都较为详细,所以这些卜辞又可以看作是先秦叙事散文的萌芽。
周王朝中央所保存的档案,主要有图版、盟约、谱牒以及史官保管的诰、誓、政典和记注。部分被编纂在《尚书》中。《尚书》文字古奥典雅,就语言技巧而言,已超过了甲骨卜辞和同时代的铜器铭文,具有完整的结构。
在这个时期内,资料集合都表现出“文史不分家”的特点,所谓“文史不分家”,其中包括了档案、历史、文学在内的研究创作活动。他们的创作者也具备档案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等多重社会角色,作品也具有文学的随性和档案的严谨等多重特色。这一时期我们很难将档案编修和文学创作强行分而论之。
2 档案与文学的分流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档案工作基本上还是沿袭西周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各国经济、政治的不断发展,这一时期的档案和档案工作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孔子依据鲁国史官的记录编纂《春秋》,为我国古代的档案利用开拓了新领域,也开拓了我国历史上私人利用档案修史的先例。《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创作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出现了有意的文学性倾向。
随着各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特别是由于新兴地主阶级政治变革要求的日益高涨,那些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记录旧制度的典册,就成了各诸侯国发展的障碍,他们不但不再愿意保存这些典册,反而要将它们毁弃。而至秦始皇时更是焚书坑儒,我国古代长期积累起来的档案、经书被大量焚毁,对我国历史文化财富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自秦汉时期重新建立起的档案随着真正意义上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也开始逐渐从私人编纂的零散的断代诸国文献资料,转向由统治阶级对前朝与当世各项的文献资料有意进行的编修整合,便于后世人进行书案间的参考。
司马迁,汉代的史学家和档案工作者,他是把档案工作与历史研究、编纂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的创始人之一。他认为,档案工作者必须把编写历史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任务。而在其作品《史记》的编纂中,司马迁将过去的档案、野史以及部分杂书进行了系统的整合和裁剪,使这一时期之前庞杂的文字资料熔化为文体一致、形式整齐的历史巨著。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这种实录精神,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后世的许多史学著作,特别是如“二十四史”这些所谓的正史,就不只是在体制上受到《史记》的影响,而且在写作态度上,也受到司马迁实录精神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下,档案编纂和文学创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三国志》与《三国志演义》:《三国志》表现出了档案整合编纂的严谨性,编修过程中不具有作者的个人感情色彩,忠于当时当世的原始情况;而《三国志演义》则用文学色彩重新“演绎”了三国历史,字里行间充满了作者的个人价值判断取向,甚至以戏说的笔法来对历史人物进行二次创作,可以美化或丑化人物。可以看出,档案编纂过程中因受“实录精神”而体现了强大的历史严谨性和理性的分析,而文学创作中更侧重于感性的个人情感的宣泄。这一分歧使得两者在发展道路上呈现出分道扬镳之势。
3 档案与文学的殊途同归
我们仍要意识到,档案与文学的关系不只是一种共生且简单利用的承接关系,也不是各自发展分庭抗礼的姿态,而是一种极富理论探讨意义的实践归纳与总结。档案已经介入了文学创作的一方领地,构筑了另一种自然色调的生活图景,成为无法替代的“第二生活源”。档案与文学通过利用实践“相约”,更应通过理论的垦荒达到“相知”。
档案在文学的“眼里”是生活,如若概以理论言之便是文学的意蕴。实际上档案已经是一颗种子,只待文学来浇灌、来培育,这种“成长”的过程,不也是文学繁荣和发展之希望吗?但凡与档案有过一面之缘的作家,大概都不能不看到这一点,档案的量化转移是暂时的,而档案对创作的推助乃至赋予文学生命却是永恒的。作家叶永烈说得更形象,称档案是他创作的“一翼”,这“一翼”的动力当然也是无穷尽的。
故此现代人总结出了“档案文学”这一概念:“档案文学”是档案工作者和关心支持档案工作的作家、作者依据自己的审美意识创作的反映档案工作、档案工作者、档案事业与其他事业、档案与社会关系的文学作品。档案文学具有档案和文学两方面特征:一方面是档案特征,包括讴歌档案事业的发展成就,揭露、批判阻碍档案事业发展的丑恶现象,歌颂档案工作者辛勤耕耘、无私奉献的精神,体现了档案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为主要内容;另一方面为文学特征,运用形象思维、文学语言和文学写作手法,以反映档案人员的工作、生活、心态为主,关注社会、剖析社会现象次之而创作的作品。二者的特征差异主要是在感性和理性精神层面的笔法表现。
可以说,在二者的发展中,档案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纵观历史,不同时代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利用档案,选择素材或吸取继承前人的文学精华,创作出曲折生动、流芳百世的文学作品,使得作品经久不衰。而例如《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书,其目的都是为记录真实的历史,为了能够更好地记载史实,文学性被放置于后。但其中的部分叙事散文,例如《曹刿论战》、《邹忌讽齐王纳谏》等名篇,表现出了文史结合后所催生而出的强大的文学价值,丝毫不弱于其史学价值。文附史而生,史因文而名,二者相辅相成,互不可缺。现今的档案作为珍贵的国家历史财富,依旧发挥着它曾经的作用和价值,而究其本体内容性质与发展历程,可谓之是一系列对于现代的《资治通鉴》,对现今的档案学发展具有强大的借鉴与影响。
(作者单位:郑州市水产技术推广站 来稿日期:2015-0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