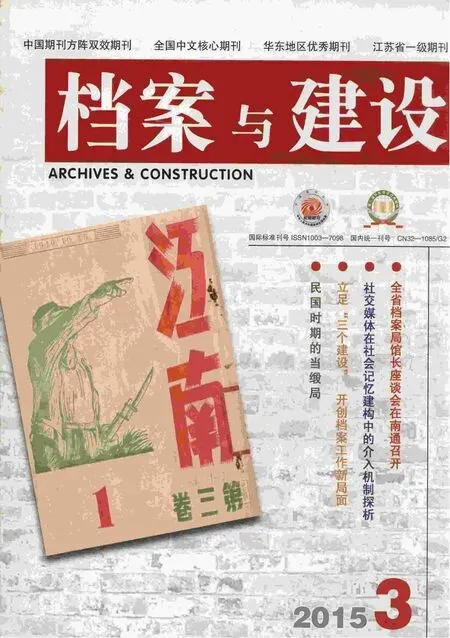民国中央大学党化教育研究
张守涛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江苏南京,210044)
今人谈起民国大学,多宣称其思想之自由、氛围之宽松、学是成为党化教育的重要基地。术之独立。实际上,国民党自民国时代取得政权起,便不遗余力地推行党化教育,力图将教育纳入“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之下,控制教育和青年,确保国民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中央大学作为国民政府的最高学府,更
一、党化教育的提出及概况
“党化教育”最早是广州国民政府为推进国民革命运动而确立的宣传方针,具体表现在时任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许崇清所拟定的《党化教育之方针、教育方针草案》中,其主要目的和作用是动员民众支持北伐。
国民党执政后,党化教育成为国民党宣传重点,成为国民党对教育和国民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但党化教育因为太过露骨、空泛,引起社会各界不满,如吴稚晖认为:“党化教育四字,说来太觉空泛,共产党也是党,国民党也是党,未免弄不清此党化之党,应为共产党或为国民党也。依余之意,最好改为‘三民教育’乃能妥贴明显,而不致为人所假借利用。”1928年5月在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党化教育”一词被正式取消,确定为“三民主义教育”,即以“实现三民主义为目的”的教育。但“三民主义教育”与“党化教育”实质相同,皆“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教育。
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指出“中华民国今后之教育,应为三民主义之国民教育,已无疑义”。4月,国民政府正式颁行《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提出“各级学校之三民主义教育,应与全体课程和课外作业相贯连”,三民主义教育成为国民政府教育的基本形式。
党化教育具体内容,如任鸿隽所言,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把党的主义和主张融合在教课(学)中间,使它渐渐地浸灌到学生的头脑中去;二是教育的事业由党的机关或人才去主持,使它完全受党指挥。[1]1929年8月,教育部颁发详细的课程计划,规定党义是高等及初、中等学校全体学生的必修课。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4434号训令,责令包括国立师范学校在内的国内中小学教师一律入党,严格要求公民课教师、训育主任、训导主任,并大量吸收国民党党员为教师,加强党对中小学教育的全面控制。后来,国民政府还要求各大学校长和院长必须由国民党党员担任。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促进宪政实施之各种必要措施案》,其中提出“各级学校以内不设党部”,被认为是国民党在大陆终止党化教育的开始。
二、中央大学党化教育主要措施及内容

南京中央大学校门
国民党定都南京后,对位于首都南京的最高学府中央大学寄予厚望,力图使其成为党化教育的重要基地。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在中央大学首任校长张乃燕就职典礼上强调:“今后很希望张校长,本总理精神,努力于党化教育”。中央大学成为党化教育的试验田和示范区,“民国时期以南京为核心的高等教育体系,可以看做党国文化的产品,与北京的悠久传统以及上海的新锐专业知识对比较交错,共同形成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的图谱。”[2]
中央大学党化教育的主要措施和内容有:
1.首先是对学生专门设立党义课程,聘任专门的党义教授讲授,要求教职员尤其是行政人员研究党义。中央大学的校长、副校长亲自担任研究会会长、副会长,并制定专门的指导员来指导全体人员进行党义研究。党义研究分四期进行,分别为“孙文学说”、“建国大纲”、“实业计划”(分二期进行),规定每天学习时间不得少于两个小时,每周至少集体研究一次。党义课则是学生必修课程,国民党严格地规定了具体的教学内容、授课时数和学分,要求学生必须参加专门考试,学生得不到学分就拿不到毕业证书。为加强对中央大学的思想控制,国民党还将三民主义理论权威戴季陶派往中央大学兼任党义教授。
2.利用“总理纪念周”,进行各种形式的补充教育。“总理纪念周”是1926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孙中山,而规定国民党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各部队,一律于每周一上午9时至12时举行纪念周一次。国民党对中央大学的“总理纪念周”活动程序和内容作出严格规定,如纪念周一切事宜由训育委员会主持,演说内容分为党务、国际政治、国内政治和校务报告,要求全体学生参加。
3.跟当时其他高校一样,中央大学的学生们必须熟读“三民主义”,要唱国歌和党歌,礼堂和办公室要悬挂国旗、党旗和孙中山肖像,革命标语贴满校园,军训是所有学生的必修课,中山装成为大学生的制服。国民政府还要求各大学推行“训导制”,在中等以上学校设训导处或训导组,由经过挑选的国民党党员担任训育主任和生活指导员,严密监控学生的学业和生活,加强三民主义与传统伦理道德的灌输。《训导概况》写得清楚:“各导师应充分利用个别谈话计划,及随时随地观察学生以注意其思想与礼貌,为训导之中心工作”。
对于与党化教育相对立的思想言行,国民政府则严厉镇压。如1929年5月,国民政府就以宣扬共产主义为由,封闭了华南大学、大陆大学。当年9月,胡适因指责党义教育为“党八股”而遭到国民党中训部训诫,中训部为此还通令全国各大学校长:“切实督率教职员,详细精研本党党义,以免再有类似之谬误发生”。
三、中央大学党化教育效果及失败原因
党化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大学校园风貌,使学校成为国民党的教育基地,使部分青年成为国民党的后备军。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纷纷开进大学,学校大多数团体负责人须由三青团团员担任,吸引了部分青年学生。国民党干部也在多数大学获得重要权力,对大学教育施加各种影响。
但总体而言,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效果并不理想。国民党的中央党报《中央日报》在其学术专刊“学风”一篇署名编者的文中,对学校的党化教育有名无实现象披露道:“自民国十六年以来,实行党化教育之声,遍于国内,大势所趋无有敢瞥议者;然而反动之势力潜在,破坏之阴谋尚存,学校虽有党义一科,训育虽有党员专任,而事实上,因勉强而结怨毒,重形式而忽实际,以致阳奉阴违,敷衍塞责,流弊多方,功效全无。”[3]大学中,党义教师严重不足且地位低下,党义课程经常被一些专业课程挤占。1932年,全国在校学生总计26719人,而党义教师仅有26人。而且,党义教师倍受师生轻视,薪金也在普通教师水准之下。
师生们对党化教育都非常不满、抵制,认为其目的在于整治思想、压制学术自由。任鸿隽甚至认为:“有了‘党化’,必定是没了‘教育’;反过来说,要有‘教育’,必定要去除‘党化’”[4]。号称“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大更是不把党化教育放在眼里,几乎从不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训导长查良钊很少公开过问学生思想,更多地是关心学生生活;有位党义教师每次上课前必向学生鞠躬,说这门课是“兄弟奉送的”。
中央大学的党化教育效果也很不理想。如有学生在1928年向大学院呈文:“而党义一课,乃本校上学期仅开三小时,且非必修”。党义教授端木恺1930年9月在致教务长信函中描述党义课情况:“党义课程现在各系集处人数逾百,教材不易分配,秩序亦难维持……缺课者因乏时间可以点名,亦后无法稽考补救之道”。总理纪念周越来越形式化,很多讲座都与党化教育无关。如中央大学1929年9月到12月,中央大学的总理纪念周没有一次直接对党义的宣传,更多的是学术题材的演讲[5]。
为什么党化教育效果不太理想,甚至被认为“完全失败”呢?“一、从历史发展来看,国民党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后,其先前所宣传的党义与其执政的内容出现了严重的背离,造成‘一般人皆视党义为一种官样文章,不能求得党义之真正精神。’二、国民党在大学中所推行的‘党化’教育的失败,其根本的原因在于现代大学本身所要求的学术自由和‘党化’教育是无法兼容的。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它不只是社会对言论自由作出承诺的一种反映,而且也是捍卫大学目的和教职员工利益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国民党在大学推行的‘党化’教育,自然受到各级师生的抵制,其失败是必然的。”[6]
对于中央大学而言更直接的原因在于,中央大学历任校长大多数对党化教育都不太积极。如信仰学术自治的中央大学首任校长张乃燕对党化教育一直消极应对。对于国民党大佬戴季陶“屈就”中央大学党义教师,张乃燕还专门呈文于中央党部,询问是否需要检定其党义教师资格。张乃燕与国民党地方党部的关系更不融洽,地方党部一直试图控制中央大学,而张乃燕以中央大学直属教育部、地方无权管辖为由,进行各种形式的抵制。如1928年,国民党中央大学支部直接上级第八区党部要求学校停课以让党员学生参加选举,却没有得到学校许可,致使该区选举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流产两次。国民党南京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再次致函张乃燕要求停课,张乃燕仍不理会,在来函的处理意见上签署“可以不复”。1928年国民党对全国党员重新登记考核,张乃燕以身体不适为由,“未甚注意答案,草率交卷”。
1945年上任的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更是深受西方高等教育影响,提出“教育独立”的大学理念,主张“一切党派退出学校”,非常反感于党化教育。他取消了学校原来规定的每周“精神训话”等官僚形式,允许学生自由组织社团,废除了过去由训导处包办的间接选举办法,改为学生直接选举。蒋介石爱将、执掌中大十年的罗家伦对党化教育也不太上心,更多地强调“诚朴雄伟”的大学精神及“有机体的民族文化”的大学使命,更多地注重学生“体格”和“人格”的培养。
四、结语
国民政府通过开设党义课、举办总理纪念周、创建训导制等措施,大力推行党化教育,试图确保国民党对教育和青年的控制。但由于党化教育与学术自由的矛盾,遭到大部分师生乃至部分校长的强烈反对,无可避免地走向了失败。中央大学是国民政府党化教育的重要示范区,备受国民党重视,但最终也是效果很不理想。
[1]任鸿隽:《党化教育有可能吗》[J],载《独立评论》,1932(3)。
[2]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第189页。
[3]《吾国教育之基本问题》[N],《中央日报》.1932-8-22。
[4]任鸿隽:《党化教育有可能吗》[J],载《独立评论》,1932,(3)。
[5]许小青:《政局与学府》[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82页。
[6]许小青:《政局与学府》[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1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