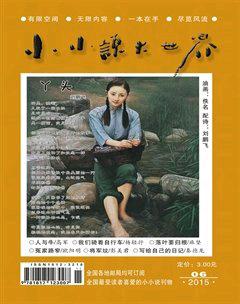我们骑着自行车
杨轻抒
从家里到乡上,八公里。我一直希望能够驮春春去,但是当春春看到文峰后改变了主意。
准确地说,是看到文峰崭新的山地车后改变主意的。那时候,山地车还是新玩意儿,是文峰的叔从很远的大城市带回来的。为了能驮春春,文峰特意找人焊了个宽大的后座,虽然看起来怪怪的。
我的,是我父亲的28圈加重,车把上还生着锈。
我们一前一后往乡上骑。文峰在前边,我在后边。
春春穿着花棉袄,斜坐在文峰的车座后边,风吹起春春长长的辫子,像要飞起来一样。
是春春要飞起来一样。
文峰很卖力。我也很卖力。文峰卖力是因为后座上驮着春春,我卖力是我想看到春春。
我只顾着看春春了,没留意轮子下的石头,结果一头扎进了路边的干草垛里,把一群麻雀吓得满天乱飞。
等我爬起来,文峰已经不见了人影,风中只飘荡着春春云雀般的笑声。
那天在乡上电影院看的是什么电影我忘了。
等我也有辆山地车,已经是十年后了。
十年后,从家里到乡上,还是八公里。
我还是希望能够驮春春,但是春春看到文峰的奥拓后改变了主意。
春春要坐奥拓。春春说坐汽车舒服。
我知道汽车坐着舒服。所以我无话可说。
文峰的车是他叔送他的,那时候不说乡下,就是城里人,有台车,也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文峰的奥拓比我的自行车跑得快,我气喘吁吁地追着文峰的奥拓,但是越追距离越远,后来终于看不见了。那一天早上,天空深蓝得像无边无际的大海,我一个人在空旷的天底下奋力向前,初春的寒意打在我的脸上,我觉得自己像一条孤独的鱼。
到了乡上,文峰早已经到了,文峰正和一群年青人掐架。我知道那一些人,都是乡里的混混,他们不能忍受文峰那么张扬地开着汽车。
我当然帮着文峰,结果我被打得头破血流。从乡上一路回来,我感觉血一直挂在我脸上。
那天电影没看成。我看见春春的花棉袄溅上了泥。
再后来,我们都长大了。长大后我们都离开了村子。春春也嫁人了,当然不是嫁给文峰。
有一天,我又碰到了文峰,是快过年的时候,文峰也回来了。
我和文峰躺在后坡上,冬日的太阳晒着我们的脸,一地荒草从坡下爬上来,那一刻有点天荒地老的感觉。
春春穿着花棉袄,从坡上走下来,问我们,要不要去乡上看电影?
我看看文峰,文峰也转过头来看我,我们一起说,去吧。
我们都骑着自行车。
都是山地车。
文峰的山地车虽然很旧了,但是那个后座还结实,我的山地车新一些,也安一个后座,但是春春还是选择了文峰的车。
我们一前一后往乡上骑。
路已经修过了,很平坦。文峰依然骑得很卖力,我也很卖力。
文峰卖力是因为后座上驮着春春。我卖力是因为我要追着春春看。
春春已经有些发福了,但是我喜欢发福的春春,发福的春春的背影给人很温暖的感觉,温暖得我一直想哭。
我光顾着看春春了,结果,我的车链条断了。
我大声叫文峰等等,文峰已经骑得远了,风把我的声音吹得七零八落。我站在路边,看着还没泛青的原野上一群白鸟飞过。
再再后来,我跟文峰在网上聊天,说起我们骑自行车的事情,抢着驮春春的事情。文峰说,那时候我驮着春春,可我总觉得不真实,总觉得春春其实是坐在你后座上的。这是啥原因呢?
我说我不知道,这事你要问春春。我只记得我们曾经骑过自行车,一路撞撞跌跌,从少年骑到青春,穿过青春一直到现在。
文峰说是啊,其实现在开着奔驰,我还是怀念那时候骑自行车。
我说我也怀念。
我和文峰聊天的时候,穿着花棉袄的春春就站在我背后,她的手指穿过我的头发,很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