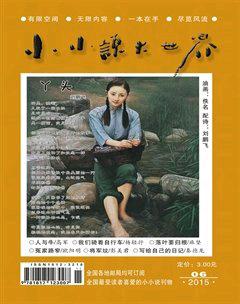人与牛
高军
天亮了,为东家扛了一辈子长工的丕田背起昨晚就已包好的行李包准备回家,他最后看了一眼自己生活了多年的这个院落,然后慢慢走到墙根,从墙上轻轻地拿下挂在那里的大鞭子,挂上了自己的脖颈,甩开步子走出了东家的大门。
临出门的那一瞬间,他似乎听到后院牛圈里的黄趴牯正在喘着粗气,四蹄一下下跺着地面,挣着拴它的缰绳,丕田嘴角轻轻撇了撇,拉拉大鞭子那光滑的木把,稳步向前走去。
昨晚东家隆重为他送行,摆了满满一桌子酒菜,除了结好的工钱,另外赠送了一大包盘缠,酒酣耳热之际,东家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就提出了想要大鞭子,东家大度地摆摆手:“没问题,你带走就是。”
这根大鞭子已经跟了他五年了,他已经使得很是顺手。
当年黄趴牯刚进东家门时甚是桀骜不驯,他就专门制作了这根鞭子来对付它。他到集上买来一根厚厚的牛皮条,选取了一段牛腿上的筋条系在鞭稍部位,鞭杆是一根鸡蛋粗细的腊条。制成后人们看到比一般的鞭子粗长,就习惯地叫成了大鞭子。当时他挂着这根大鞭子拉着黄趴牯去耕地时,黄趴牯仍然不是很听话,东挣西歪的。他就从脖子里拿下大鞭子狠狠地抽了过去,脊背上出现了一道鲜红的血印子,鞭稍打到牛腿上那腿上的皮肉翻了起来。黄趴牯浑身一阵抽搐,回头看了他一眼,才温顺地干起活来。第二次对黄趴牯使用大鞭子是大半年之后,它在拉犁时又犯了倔,向一边斜歪了一下。这次丕田把大鞭子的鞭稍抽向了它的右耳朵后边,除了打出一道鞭印,耳边也被抽去了一块缺口。黄趴牯低头向后踅了一眼,老老实实干起活来。
此后,丕田再也没有使用过这根大鞭子。耕作过程中,他只要叫一声“牯儿”,黄趴牯就会照着他的吩咐听话地干活,再也没有反抗过。黄趴牯乖巧地在干活,他的大鞭子成了摆设。五年过去,鞭杆显得光滑了点,大鞭子陈旧了一些。
黄趴牯尽管听话了,但他也能偶尔看到牛眼中射出来的炯炯目光。他知道那是它桀骜本性的自然显露,他的右手就会攥住大鞭子的鞭杆什么也不说地看着黄趴牯,黄趴牯那眼神会迅速黯淡下去,本本分分地干起活来。
和黄趴牯相处了五年,四年多的时间里一次鞭子也不用,让他感到一种很大成就感,这是几十年中他遇到的第一头这么听话的牛。所以在喂养的过程中,他经常偏爱它一下,多抓几把豆粕,多添几勺玉米糁子都是顺手就做的。每当这时,黄趴牯会抬头看他一眼,眼中好似有一丝感激。但丕田感到里面绝对不是其它牛对人们的那种温热眼光,而是还隐忍着一股冷森森的东西。他轻轻拍几下牛的脖子,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滋味来。
太阳逐渐明亮起来,有些刺眼了。丕田向四下的田野看了一圈,临近年关的山野里,除种植小麦的田块里有些陈灰色的绿颜色外,其它地块里均是枯黄庄稼的根茬。寒风刮过,发出一种瑟瑟的抖动声。年后这些地块就要开始耕动了,到那时生机才会回来的。
丕田又习惯地攥了攥大鞭子的鞭杆。
“嗒嗒嗒……”一阵急促的蹄声,粗重的喘气声也越来越近。
丕田稳步走着的脚步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又向前走了几步,他才慢慢转过身来。
黄趴牯也随即停下了急急的脚步。丕田看到,它的脖子里还挂着缰绳的圈套,圈套下边耷拉着一段绳头,被挣断的茬口非常新鲜,还散发着一股新苘的浓郁味道。黄趴牯的大眼睛亮亮地瞪视着他,平时的那种温顺神情一扫而光,被压制了多年的野性暴露出来,充满着挑战和复仇的神色,它的头慢慢向左后方拧去,粗大锋利的牛角直指着丕田所在的方向,口中的气息也越喘越粗,身上的肌肉在慢慢收缩,四蹄使劲向地上抓着,随时要开始进攻的样子。
丕田轻声唤了一声:“牯儿。”
黄趴牯迟疑了一下,还是慢慢抬起了头,看向丕田。
丕田的左腿略略向后退了半步,右手抓住腊条鞭杆向下拉了一点,挂在身前的粗厚皮条和牛筋鞭稍向上滑动了一下。黄趴牯清清楚楚地看到后猛地愣住了,目光也开始散淡起来,接着头部开始往下低,身上的肌肉渐渐地变回到了平滑状态。
丕田的右手离开鞭杆,向黄趴牯身后指了指,轻轻说道:“牯儿,回去吧。”
黄趴牯转过头去,慢吞吞地向来路走去。
丕田拿下大鞭子,轻轻顺溜了一下,又重新挂回了自己的脖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