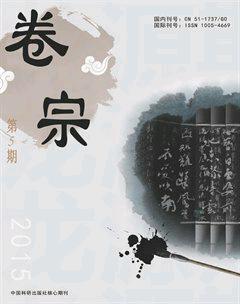论韩儒张显光的性理学思想
俞英兰
摘 要:高丽末期,中国的朱子学传入韩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韩国性理学。韩国性理学作为中国朱子学的延展,在诸多方面都表现出了其与朱子学的联系与差别。其中,朝鲜朝后期的性理学家张显光所提出的理气论上的理气经纬说、心性论上的四端七情一条说,充分展现了其强调道德的理论特色。可以说,张显光的性理学思想起到了连接16世纪性理学和17世纪乃至18世纪性理学和实学的桥梁作用。
关键词:张显光;性理学;儒学;韩国
高丽末期,中国的朱子学传入韩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韩国性理学。韩国性理学作为中国朱子学的延展,在诸多方面都表现出了其与朱子学的联系与差别。对此,我国学者曾以李退溪、李栗谷、奇高峰、宋时烈等人为突破口进行了有益的研究和探讨。然在此方面,朝鲜朝后期的张显光是一位个非常重要,而我们却又缺乏了解的性理学家。
张显光(1554~1637),字德晦,号旅轩,为韩国岭南士林派的重要人物。张显光生活在朝鲜王朝的衰退时期,这是一个经济贫穷,政治局势混乱不堪,漂泊不定的年代。在那时,朝鲜王朝开国以来所积累的社会矛盾逐步深化,道德伦理意识已到达了崩溃的边缘。虽然,张显光在这种现实下流离失所地度过了一生,但是他却表现出了强烈的道德理想,坚定的信念和坚忍不拔的生活态度。即使是在生活漂泊不定的情况下,他也不忘通过道德和义理来践行自己的道德理想,试图重新在具体的人生中加以实现。具体来说,张显光的性理学思想主要表现为理气论上的理气经纬说、心性论上的四端七情一条说和修养论上的主经治纬与治纬准经说。
1 理气经纬说
关于理气,朱熹曾做了完整而周密的论述,主张理先气后、理生气说。对此,韩国性理学者却出现了不同的理解和争论。退溪李滉提出并承认理的“能动性”,认为理为气之帅、气为理之卒、理有动静故气亦有动静。与此相反,栗谷李珥却不同意理的“能动性”,认为理和气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进而提出理气妙合的理通气局说。对此,张显光在承认理生气的同时,却否认了理有动静之说,进而提出了理气经纬说。
盖生虽一字而义有精粗,如以气而相递,以形而相禅者,虽谓之生矣,而乃生之粗者也。或以彼生此,以此生彼,其生也有迹。若以理而为气者,虽亦可谓生焉,而乃生之精者也无迹。今苟以太极之生两仪有动静,视为气递形禅者,而同认之,则一可谓之知得太极之妙哉。所谓太极之生两仪于是乎生也,有动静之理,故动静于是乎分也。果是同于气递形禅之生焉,则是太极亦一物尔,岂可为之理乎?
由此来看,张显光把“理生气”中的“生”分为形而上的“生”和形而下的“生”。形而上的为“精”,形而下的为“粗”。他认为,形而上的“生”如同理生两仪一样,“若理之生气也,则元分为会,是元生会也。会分为运,是会生运也。运分为世,是运生世也。至于岁月日辰之自大至细、自一至万,气所谓生之者,与的得生者,有先后、有彼此者也。至于五行之相生,则以先有后,以此有彼,不如此生彼者之有先有后也。”也就是说,由于形而上的“生”是以“理”的存在为前提的,因此,并不会像“生”个体那样有先后关系。与此相对,张显光用气递和形禅来说明形而下的生。他认为“气递”就如同春木生夏火,夏火生中央土,中央土生秋金,秋金生冬水,冬水生春木,而“形禅”就如同水生水族,陆生陆族,土生植物。简单地说,五行相生是气递,生物繁殖是形禅。虽然气递和形禅都是“生之殖”,但是有迹可见。因此,在张显光看来,一个“个体”生其他“个体”是“形而下”的“生”。
如此看来,张显光把形而上的“生”与形而下的“生”,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区分。第一,当在形而上的“生”与“理生气”相同的情况下,一是无痕迹,二是以理的存在而生,三是具有可分性;第二,在形而下的“生”与“气递”和“形禅”相同的情况下,一是有痕迹,二是有因果关系的具体物的生,三是具有“形”的可变性。简言之,张显光认为,形而下者之生是个别存在的“生”,而形而上者之“生”则是根据其原理而“分”出的“生”,同时新“生”的对象中又包含着“生”的内在原理。
张显光把其所谓之“理”比喻成“经”,把其所谓之“气”比喻成“纬”,认为“纬”只能通过“经”才能运行。对于理气的经纬关系,张显光通过其著《分合篇》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理即气之本也,主也”,且“气即出乎理,行乎理。”也就是说,理即气之本,气即理之用。理为“气之本”的认识是本体论的理解,而气为“理之用”的认识是体用论的理解;气出乎理的认识是本末论的理解,气行乎理的理论是介入本末论和体用论的观点。事实上,张显光在《经纬说》里也多次主张理气关系是体用关系,同时也是经纬关系,相比而言,经纬关系可以克服体用、本末、源流、纲目关系所具有的局限性,且能够统合这些关系。
2 四端七情一条说
四端与七情问题是韩国性理学的重要内容。韩儒大家退溪主张四端和七情不同,而栗谷则主张七情包含四端。此后,许多学者都对四端与七情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张显光认为,四端与七情都为理发,七情包含四端的一条说。
首先,张显光认为,性之发为情,其言:
窃当思之七情,亦出于五常。喜爱仁之发也;怒恶义之发也;哀乐礼之发也;喜与怒对,哀与乐对,爱与恶对。而喜乐爱三者,感于顺境也;怒恶哀三者,应于逆境也。随其顺逆境,而有其感应之别者,智之发也。可喜可爱可乐而必欲之,可怒可恶可哀而必不欲之者,信之发也。
可以看出,张显光认为仁之发为喜爱,义之发为怒恶,礼之发为哀乐,智之发为“喜与怒、哀与乐、爱与恶”相对感应的顺逆境,信之发为喜爱乐必欲之、怒恶哀必不欲之。可以看出,张显光正是根据理与气的经纬、体用关系,把性与情相对应的。不过在此,张显光并未探讨七情中的欲的归属问题。在他看来,在人心之外顺事与逆事相接近时,人心就会从顺境和逆境两个境界发情。从而,张显光把欲看成是顺逆的,其依据是“阳自下而上为顺,阴在阳中逆行。
其次,对于四端的端,张显光跟朱子多少有些不同。朱子把端解释为绪,称其为发自于内心存在的仁之本体的性,这种性就是所谓的恻隐之心。但张显光则主张端为始,称其为性最初之发。张显光所主张的从性到四端,再到情的一条说完全不同于把四端与七情分开的二元论观点。为此,他既不同意退溪的四端与七情互发说,也不同意栗谷的理属性、气属心之说,在他看来,把性看作理、心看作气,用理气体用来理解性和心的时候,便会产生从性到情、从性到心两条通路,这无法确保张显光的从性到四端、再到情的一条说。
3 结语
张显光作为韩国16~17世纪著名的思想家,其思想不仅体现了对退溪和栗谷思想乃至宋明理学家思想的吸收与继承,而且也体现了自己的独创性。张显光哲学思想的首要目标在于理气一原论的定立,其优点是把这一点引向了道德论。无论是理气经纬说,还是四端七情一条说,或是“主经治纬”和“治纬准经”的修养论,对道德的强调展现了旅轩张显光哲学思想的独特世界。故此,他成为了韩国性理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哲学家,被评为拥有自己独特领域的性理学者。如此看来,张显光的哲学思想起到了连接16世纪性理学和17世纪乃至18世纪性理学和实学的桥梁作用。
注释
1.张显光:《旅轩先生全书》下,第73页。
2.张显光:《旅轩先生全书》下,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