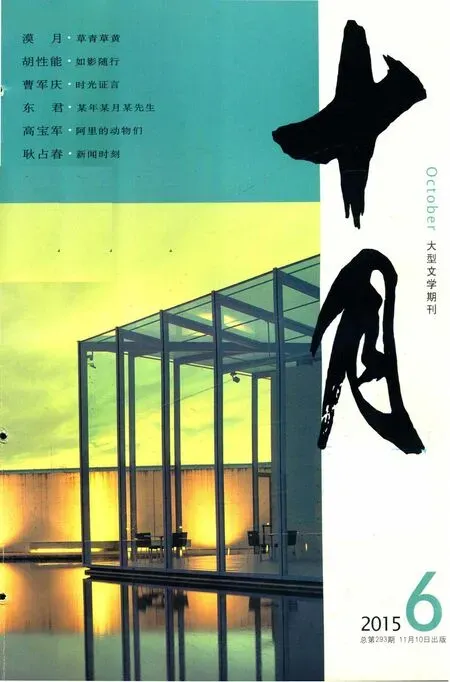飞越太平洋
周京
香港
01.送别,如果恰巧在星期天,便像点了蜡烛的晚餐,多了氛围和点缀。然而,被送别的人是不会感受到和其他的日子有什么不同的。因为他只是个过客,对这里的一切都是新鲜的,自然也都是一样的,哪里像一个常住的人,从早晨的空气里都可以嗅出这个城市的慵懒和别样的忙碌来。
02.晌午,阳光高照,是明朗的一天。院子里稀落的行人,背着自己的身影,落寞地走出琐碎的步伐。同样的日头,在中环,可能是高楼的阴影夹杂着缕缕阳光洒在人潮涌动的十字街头,中间穿梭的是摩登而纤细的女郎和精干装束的西装男人。而这里,走来走去,手里牵着小孩子或者拎着菜篮子的,大多是菲律宾女佣。她们脸上写着淡然而忙于琐碎的劳碌,身上总是草草地披上外套,会安静地等你进电梯,然后微微一笑。昨晚的电视新闻里,那个被她的女雇主打落牙齿、百般欺凌和虐待的印尼女佣从高等法庭出来后即刻祷告下跪。外佣,这个奇特的风景,像在你面前摆满包装华丽的果盒,打开来一看,你心里却只有牢骚满腹,而又只能忍气吞声。你有了用人帮忙,但连语言都无法沟通;她们有了薪水,可到了星期天,只能躺在香港的大街上,在往来行人的侧目下,完成一个完全是皇帝的新装式的放松的休息日。
的确,这是个奇特的城市。生活状态如同驾着一辆高级轿车上路,表面光鲜,但你却需要边开车边要在这架车上完成你的洗漱,化妆,哄孩子,再做个漂亮的三明治。一旦交通状况不良,立时,每辆车上便会传来怒吼,连个酝酿的过程都不需要。人从车上下来,路上全是服装店,世界服装的牌子之所以是牌子,就因为它们曾经驻足过这里,这里就是大都会,它只属于大都会世界华丽缤纷的浮夸和闪耀。但小心的人们不要走进它的后巷,因为那里太赤裸。
当然,赤裸也可以是风景。比如你见到一些年纪趋大的老男人,千万不要遵循任何文化传统本能地去尊重他。因为众所周知,香港许多女人过分的警觉甚至可以在街上破口大骂就是一些这样的男人培养出来的。香港,从历史上,是由四次移民浪潮组成的。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文革”期间,改革开放。许多逃难的人在枪林弹雨下,九死一生,没有知识没有文化,但偏偏赶上香港的腾飞起步。报上说一个女人经过在公屋凉亭下乘凉的老人,老人大声叫,好大的奶子啊!这在许多女人的生活经验中,都可谓是震撼的。上两个月,游泳池来了一个白发老翁,花白的头发整整齐齐。我如常在自己的水道里游来游去,但突然,他出现在我的前方,他回身,我抬头慢了下来,希望他躲开就是了。但不料,他往回正了正身,对准我要去的位置,等我扑向他。我即刻站起来,像撞了鬼,心里真希望可以有大骂的勇气。但我回过身,游向另一个方向了。从此我才观察到,这个从来不游泳,只在水中做健美操的白发翁,像中了魔似的,出现在许多女人游泳的水道中间,等待相撞。她们每个人都与我反应类似:突然停住,掉头或绕过他。真没想到,这几乎只有在黑社会电影中见到的画面,天天在我身边上演!
罢了,日头渐高,此时每个城市的天空上,会不会都没有一丝的阴云呢?我涂上防晒霜,开始了如常的一天的生活。
03.听到《天空之城》,知道世界上可以有一种人生,悠扬悲切却不会让你淌下一颗泪珠。日本的民族性,永远悲凉,但蓬勃理性,说不出的淡然的味道。他们的道理和中国人好似来自一个世界,却又不知何时分道扬镳;我们的道理常常有痛骂他们的彪悍,但掩不住,总是会回身顾盼。
美丽的夜晚,像灰姑娘,怕听预示黎明的钟声。
北京
01.雨终于被逼得下起来了,但是是毛毛雨。我暗暗想:这不像是北京的风格啊。毛毛雨,风雅地飘在我们的菜上和脸上。但周围没人提这事儿。只有我的声音在胡同里飘:“下雨了!”老板从胡同对面的餐厅门脸儿里钻出来,举把大的撑伞,笑盈盈地过来。我又道:“太好了!”老板边在旁边几个抽着烟的男人的餐桌中间找插伞的洞,边把声音递过来:“慢慢来,按顺序啊。”透着和气和有规矩。胡同边坐着五桌人,都是中年男人。桌上都摆着各种啤酒。年轻的女孩不时从对面屋子钻出来,手里是形状各异的盘子。朋友大平喝了一口扎啤,道:“德国的。”旁边的老板自豪地搭过来:“没错!”朋友夹了一块炖牛筋放在口里,道:“味道醇厚!”我笑道:“大平,这是法源寺街的味道吧!”旁边的晓伟連忙凑过身来,眼睛从近视镜上面把一个深意直接传到我的眼:“我特意把咱们聚的地方定在这儿,因为上次我经过这儿,看到这老板是我们小时候小卖部的售货员。我觉得特亲切,因为记得小时候他老是穿着蓝大褂儿,卖油盐酱醋,冬天骑着三轮车在胡同里卖大白菜。”我把他眼里的深情接过来,道:“这几桌都是咱们这年纪的,我估计都像你这样怀旧吧。”“没错!”晓伟总是这么感性。想起大平刚刚在酒店接我,提起晓伟:“上次宏林、大江带着小蜜一起卡拉OK,晓伟回来的路上和我说,他还是觉得他老婆不错。他说他最近被他老婆感动了,因为她诚心诚意地伺候生病的老爸。”大平接着把自己逗笑,“我还以为是晓伟的爸呢,原来是她自己的爸。”他的笑带着合理性,就像他早前和我说大家都有小蜜一样,带着些似是而非的合理。老板终于把五桌的伞都撑了起来。灰色的胡同像长出了盛大的花。男人们声音都不大,举止也都文静,似乎怕打扰到周围的邻居。我问晓伟:“你们牛街这儿信伊斯兰教的人多吗?”他道:“真不知道,我虽然信一些,可谁有时间每天祈祷五次呀。”雨下得还是那么有节制,伞下的男人们一轮一轮地叫着扎啤。我不时拍打着从路边草丛飞到腿上的蚊子,把大家叫的羊肉串一串串放到自己的肚子里。夜阑人静了,谈兴似乎更浓。大平还是老样子,要把聚会无限地延长:“咱们换个地方,接着喝?!”晓伟正要附和,大平又道:“要不咱们周末再聚一次,我找个地方?!”晓伟附和:“也成!”话音未落,雨突然哗地一下,倾盆落下。“一块儿打车走吧!”晓伟连忙说:“你们走,我骑着小摩托呢。”大平道:“从牛街到劲松,太远了,还是过两天来取吧。你这不是有罩子吗!”晓伟镇定地说,“没事,我带雨衣了。”双方执拗了几句,晓伟坚持并打保票给大家。坐在出租车的路上,外面雨更大,大平要给晓伟打电话,我劝道:“算了吧,他骑车接电话多危险呀,到家再说吧!”大平转头看看我,道:“也是,一会儿打吧!哎,过两天,咱们去一家泰国菜馆儿,味道非常不错!”“好!”我在哗哗的雨声中,心不在焉地应着……
02.坐在旁边沙发上的老年女人声音越来越高,在书店宽敞的咖啡厅里吸引到年轻的目光。和她在一起的中年男人也在交流,但声音和缓,像个中提琴在和一个小提琴合奏,各司其职。我匀速地吃着三明治,伴着冲到耳中的谈话内容,慢慢理清了隔墙的脉络。中提琴是个日本记者,小提琴是诉讼三菱集团非法使用中国劳工的中方知情者。知情,知道历史,往往会给人力量,揪出烦琐中真理的力量。几个日本人名和中国各地劳工联谊会的名字在咖啡厅里穿梭,据老年女人讲,是阻碍三菱赔偿的飞在蛋糕上的苍蝇。我用余光看日本男人,粉色衬衫干净清新,胡子刮得脸上发光,整齐谨慎的气质只有日本国产。我的情绪随着老女人的声浪起伏着,在她描绘的纷乱中勾勒着日本人的阴险。她的声音终于在接听电话时低了下来。我又向他们的沙发望过去。老女人强势得像个子弹,日本人谦和得像个温暖的蛋糕。两个人好像两个民族相片的底片,反差得让人只能集中起精神,逆向地慢慢说服自己。
03.北京夏日的晨光,是厚道的,骄阳虽已微露,但夜凉不着急离开,款款相送。北京的地铁是四通八达的,但计算了一下在地铁之间上上下下的时间和清晨的人潮,我还是决定从酒店坐出租车去海淀的老年大学,去听朋友给老年大学的学生讲摄影课。教室里都是电脑,电脑后都是头发灰白的学生。上课了,老师把两百七十张照片做了归类,原来是同学们刚从新疆上实地摄影课回来的作业。老师又从摄影协会请来两个专家,把其中五十多张照片做了评价和意见。我开始只是漫无目的地听着,但渐渐地,眼前电脑里翻动的照片终于把我带到了那遥远的南疆。辽阔的天山脚下,肥沃的草原上,悠闲的羊群和牧马与阳光、远山相映成趣。老师在远处的讲台上,讲色彩和光圈,讲构图和情节,讲后期制作的重要。照片在电脑上是有属性分析的,老师便像打开谜底一样,一张张地进行点评和分析。不一会儿,黑板上便堆满了专业术语和测光对焦的方法归类和总结。下面的同学中也像所有课堂一样有喜欢嘀嘀咕咕做小动作说话的,但我猜测,这样专业和严格的摄影课程,学生每次摄影作业的难度也不是可以轻松完成的。但可幸的是,老师强调的构图意识、情节把握、艺术感觉,是这些有着丰富人生经验的人可以深切体会,一点即破的。三个多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我环顾了一下教室,同学们安静而认真地倾听着老师的讲解,眼里流露着饥渴得如同海绵一样的热情。从老师讲的摄影器材猜测,这样的课程应该算是老年人比较高端的课程了。课间休息时,我站在聊天的同学们中间,听着他们谈论去英国、南非、美国的种种。看来,这些老人,也是我们大中国精力充沛、朝气蓬勃的一代人啊。
古巴
01.天色渐亮,回头瞥一眼天边,不知道被谁泼了盆亮彩,鲜橙地铺陈出黎明的朝霞。公路上的车渐多,当然不是熟悉的街景,颜色再也不是黑白银这些见惯的当下的流行,而是五十年代美国流行的老爷车款。古雅线条的小轿车的色彩像从老画中走出来似的,带着尘,却姗姗地一辆辆从对面驶来,像在宣示那个时代的繁华。而这个时代的古巴,在广阔而沧桑的海边,在翠绿而林立的椰树林旁,奏着令人心动的桑巴,让游人常常忘记一种物质的匮乏,只想眺望,体会一种时光倒流的玄妙。
02.住在专门为外国游客设的大面积的海滨,大多皮肤黝黑的古巴服务员都有样貌姣好的丽质,大多讲英文,但没有媚态,只是审慎地看定你,要求小费时也一本正经。你问她问题,她常常转身和朋友用西班牙文认真地聊天,全然忘记了你。但这里,却是钻到西方人的心里让人放松和快乐的好地方。它完全按照西方人传统的家庭度假定义去操作:躺在阳光海滩上晒得黝黑,流连在迷幻的酒吧中和美女搭讪,驾上快艇在海面狂奔,静静地看一看当地人然后回到自己熟悉的圈地,洁净而美好……这种和许多度假村雷同的模式,让人心安,让人觉得生活中的这个休止符是安逸生活的延续。
03.汽车卷起的尘,让农场远处如画的风景由清晰变得朦胧。此时的温度大约有四十摄氏度,同车的人刚刚喂了拴在树边的羊整瓶的水,周围的小动物们都坚强地在炎热中奔走找着食物。我们终于可以从颠簸的车中下来,在农场的深处看下古巴农场的风景了。不时有吉普车开进农场,都是些参加驾车团的游客。炎热中,充满着及时行乐的快感,和无须精打细算的盲从。一个女人让一只牛不停地舔她的手臂,看得我直起鸡皮疙瘩。
04.在我与他们的相逢的这个瞬间,有关他们的故事,例如社会主义制度,免费医疗和大学,物质的匮乏,革命的彻底,殖民的过去,沦为奴隶的悲惨,来自非洲的历史,皮肤的颜色,混种的分别,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重要的是,他们在他们熟悉的历史中,在五彩的小房子里,在似乎失去岸的海滨,自在地活着,当此时我的眼光和他们相遇,我不由感叹,生命是由这许多的瞬间构成的。
05.站在吧台边,手臂搭在高高的黑木台上,等里面有西班牙血统的老练的兑酒老男人忙完。度假村酒吧总是最拥挤的,没有桑巴的音乐,没有狂欢的氣氛,但有似醉的人们,满脸写着假期,写着忘记。旁边来了一个男人,和我一起等,轮到我时,我的要求是椰子汁。酒吧里示意往椰子汁里加酒,我说,不加酒,只要少少的冰。两个男人一起笑。都说旅游是抹去太多自我的过程。出发的那一天,就是把心交给那段旅程的时刻。再也不可以固执,再也不可以停滞,路走到哪里,心就要从哪里启程。因为你到的地方,永远有一段你全然不知道的历史紧紧地拴住那里的人们,而你浅薄的经验,不过是骄阳下的一粒沙……
06.清晨不到七点,太阳懒得进行日出仪式了,躲在漫天的蓝云里,像个赖床的小孩,只露出几丝彩霞,转个身,彩霞丝丝闪烁,洒在白绿色的海面上。度假村的一边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此时,没有强光照耀的海面,荡着微波,缓缓从远方蔓延过来,在白色的沙滩上掀起一层层薄薄的浪波。静悄悄的早晨只有它的声响,淡淡的,似乎就要远去,又知道它会再来,像相爱已久的恋人,好难分开。古巴的海微波荡漾,海色渐变,由湛蓝到浅,由淡绿到沙面上的淡黄。白天,大大的日头照耀着海面上,远处闪着白光,总以为是跳动的海豚,而实际上不过是跃起的小浪尖,星星点点,呼应着日头。四月,一天天地开始热了,然而甘蔗地、香蕉园、芒果林还没有丰收的长势。路边遛弯的牛是国家严格限制不准私人宰杀的,据解释,是为了保证紧缺的牛奶供给的。如果哪个不小心的司机撞死了这些无精打采的路霸,最高刑罚可以是八年的监禁。然而这些可以长寿的牛看起来反而活得无精打采的,个个瘦骨嶙峋。如果哪天它们知道了自己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牛多了张免死金牌,会不会多出份感念之心,活蹦乱跳起来呢?或者它们已经像这个地方的人一样了,懒懒洋洋,连做饭吃饭好像都没有什么兴趣似的。哪像我们中国人,勤劳地生活着,享受着麻烦烹饪出的美食,而且乐此不疲,坚信可以通过美食煨出一份生活的快乐来。没待太阳从云后醒来,我们便不舍地离开了海边,登上了开往机场的专巴。到了机场,本是心寂寂离开的时刻,但机场里布满了让人心痒痒的挽留。眼前到处是贩卖雪茄的商铺。候机室里奏着迷人的Salsa歌曲。我钻进一家小书店,买下了一张满是古巴音乐的CD,又捎上几天前翻阅的那本关于老古巴的随笔。本来几天前不想去读的古巴的沉重的历史,此时却因为即将离去,便不由得想换一个角度,去了解更多的,关于它的故事。
台北
01.冬天的台北,有清云,没细雨,是个艳阳敞亮的下午。光照如旧,总是宽宽厚厚,光顾到陆地的每个角落。当然,如果你心存不轨,和它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生了顾忌,怕它加害于你而生斑变丑,你可能会和我一样,总是躲东避西,遮遮掩掩,像刚刚做完难言的愧心事儿。但这样的小气心思,往往在人到中年之后才会酸溜溜地泛起的。不过也正好,沉淀完雀斑之后的女人,心思也终于少了些轻浮。看台北,不再是大餐而是卤肉拌饭;不再是高耸的101,而是小街道里人们在二楼橱窗做着各种营生的世态;也不再是西门町,而是惨壮的日据时代。唯一还不由得驻足偷拍的,便是博物馆门前石柱下的帅哥了。他目光四射,戏码十足,但我满脸欣赏,一点都不觉得他矫揉造作。甚至,在心中还升起了正中下怀的小窃喜,你看,这就是我记忆中的,有着一群“小确幸”的台北呦!
02.透过民康街上的一间咖啡厅二楼的窗,可以看到一幢老气而精致的三层洋楼上,一个老女人手里撕着什么向楼下的树枝上撒去。那棵树枝叶繁茂,可以想象情侣们偎依在树下的情景。我目光流连于她与树顶之间,嗔怒着她的举动。但我的视野只限于此,望不到树下的情形。味道极佳的摩卡终于在我的赞誉下完成。出了咖啡厅,我连忙找到那棵树,一棵蛮秀气的树,衬着小洋房的雅。树下没有任情侣偎依的座椅,而是一片空地,地上的一群鸽子在忙碌,看来住在楼上的老女人,刚刚在随性地喂食这群小朋友呢。
总是这样,随时遇见的台北人,愿意把自己扮成一种温暖,一份随性。你的急躁和刻意几乎可以成为这里的一个流浪汉的笑柄。吃完鼎泰丰后临时决定去找梁实秋的故居。这本来是个小任意吧,但有趣的是,它似乎正中了台北人的下怀。不近的这段路程,居然受到一路上人们的“宠溺”。我向梁实秋曾经任教的师范大学渐行渐近,时而驻足,喝台中起家的春水堂的珍珠奶茶,照师大美术系学生的画作,买小玩意儿,吃台湾小吃。我满心欢喜,满肚美食,穿过有好多日本人的民康街,走过全是台北当地人的青田街,当我举着珍珠奶茶抵达师大路,背向师大时,终于因兴趣过浓而迷路了。问穿着文雅些的本地人吧,我决定,毕竟梁实秋是大师呀!被问到的人们纷纷停下来,满脸关切伴随着真性情。但遗憾的是,没有人知道这个故居的所在。最后,我不经意地停在了一个炸鸡店门前,向老板娘迟疑地张了口。旁边忙碌的老板回头笑对我,道:“对面沿街走,第二个巷口拐进去就是了。”他没待回身,又挠挠头,手在天上又数了幾下,道:“不是第二个,是第三个啦!”我忙不迭道谢,兴致高涨起来,瞧瞧,这藏在民间的文化啊。
就这样,我在师大文化圈兴高采烈地完成了我在香港无法实现的许多事:譬如永远会回答你问题而且满脸耐人寻味的友善,譬如到处的看似无心实则有意的文艺创作,譬如青春无敌而且浑身书卷气,譬如缓慢的节奏伴随着专心和温暖。
03.在台北因为住二二八纪念馆旁边,所以便这么偶然地知道了一段历史。今天是纪念日,电视上播放马英九给二二八死难者鞠躬后,柯文哲在纪念碑前哭诉他一家三代是这个事件的受害者。那天我在纪念馆里徜徉,到处都是让我糊涂的前因后果。当我最后扯出一条线索并且与今天的时政联系起来后,才算明白。上网再论证,原来台湾人自己目前仍然对这段历史遮遮掩掩,看来是个敏感话题呢。总之,应该仍然同香港目前的殖民情结一样吧:殖民地的子民无法归依中国大陆。1947年时,台湾当地人讲了一辈子日语,文化上很多归依了日本。二战中台湾人报名参军的有六十万人。战争失败后,国民党接手了,外省人来了,台湾本土的日本武士遍街斩杀不讲日文的人,台湾本地人与外省人发生起惨烈的种族冲突时国民党派军队镇压,死伤无数。如今特此建碑立地以作悼念。其实在台湾旅游,我时常要提醒自己,这里不是日本,只是我经常会恍惚:上次去高雄,在地铁站大厅停下时,我还以为身在福冈,因为这里大厅穹顶和地下走廊的一切都和福冈一模一样;台湾人谦和有礼的举止与大陆人的直率不同,也和香港人的冷漠不一样,但和日本人总有神似;台湾的街道房舍的布局是日化的,女人一脱离求偶期,穿着立马变成日系朴素中见优雅的风格。这些耳濡目染,很像我生活中接触的香港人,他们的“酷”实在让我觉得那是英国人的理性和冷淡吧!今天电视新闻报道说:春节期间,大陆人在日本旅游总计消费六十亿,人均一天一万。看来,我们中国人真是那水的性子啊,等待的是外来的水杯,去盛满它!
温哥华
01.车门外的教堂在冬日的阳光下,闪着石砖特有的钝拙的光影。拱形的门窗镶嵌着五彩的玻璃,显得神秘和圣洁。整个星期,眼前密布的总是纤细挺拔的褐色枝条,它们出现在目光所及的一切风景的前面:安静的房屋,曲折的小路,崇山峻岭,海阔天空。唯一能让这满满的枝条消失的时刻,将是绿叶爬满枝头的那一刻吧,而那个时刻,似乎已经近在咫尺了。温哥华的阳光很夸张,它使得这里每个人脸上,都不得不挂上一副墨色的眼镜。这座教堂在市中心的一条大路上,再见它,心中漾起的是曾经每天经过它的阵阵的熟悉,也是日久生情后,由熟悉渐渐变成了忘记。车经过了Dennys,记起了里面有一种叫一杯给两杯的厚味奶昔,做了几秒钟的思想斗争后,毅然停下车,爬上楼去。餐厅装修比以前上了一个档次,叫的东西还是超大的分量,让人先是张大口惊讶然后勉强吃完了,撑得想要吐出来。一切味道都很正,是在亚洲开的西餐馆做不出的正宗味道。这份正宗,就像出了北京城,在哪喝你熟悉的面茶似乎都正宗不起来是一个道理吧。餐厅很大很干净,而大和干净在这里又不像在亚洲,是一个评价标准,反而只是西餐厅蛮自然的本色。往往,当亚洲人来到西方,大赞那些所谓让人觉得先进的东西,反被这里的人视为有些大惊小怪。就比如你夸一个白人真白,反会遭他心里的一个白眼吧。我的餐盘里剩了大半的炸薯块儿,奶昔早就吸得干干净净了。服务员态度殷勤,我心里的自然反应是要不要多给她点小费呢。熟悉的思维习惯就这样一点点爬上了心头,就像几天来渐渐被平静所染,又有些回到了从前的日子和从前的平庸。那种平庸源于周围的一切非常舒适,你有着一份满意的工作,你按部就班,你不需要想太多,而渐渐地,你的人生好像就这样停滞下来了,你湮没在这种熟悉里,而后渐渐心生琐碎和平庸……
02.又是个雨天,我的呼吸里饱含湿气和寒冷。一路上叫着要喝姜茶的我,最后落地在一个小岛上。我问市场里操着英国口音的女人,你家卖不卖有姜的茶呢?她从店里探出身来,指着远处,说,那一家,卖世界上各种茶。是,我到了那里,墙上摆满了雅致的黑色铁罐。店员正在向戴着一顶斗牛帽的小女孩探讨茶叶的味道。漫长的等待……一个年纪大一些的满头红发的女人走过来,我问刚才的问题,她转身从架上抱来一个铁罐,里面色彩艳丽,但没有太多呛的味道。我向她确定道:“这里面有姜,是吧?”她带着老练的态度给予肯定。我于是准备付钱。她这时很迅速地望了望我,快速地說,“为什么不给你些姜和热水呢,你觉得呢?”我很快认同。一大杯捧在手里准备付钱了,她爽快地说,“免费的。”我满脸惊讶,她说,“这样我会感觉好些。”是呀,我此时也受了传染,感觉很好地边抿姜茶,边望着窗外巨大的桥身下,停泊的小帆船在海上漂呀漂。
03.那天,下着一滴滴的雨点儿,匀速地,让我想起住院时打的点滴。沉甸甸的,有些重量,很快,衣服就被打湿了。但街道上总是走着不打伞的人,让人先是为他们担忧,继而自己也懒得把伞撑起合上了。没过多久,就出了太阳,是那种巨大的太阳和焦灼的光线。立刻,天空一片惨白,照得人睁不开眼睛。慌忙找出墨镜来,望向远方,刚刚的苍茫的天空突然出现了海市蜃楼般的美景。墨镜成了滤片,把天空的色彩和各种云彩和海面上的轮廓呈现出来。我把墨镜递给旁边忘记戴墨镜的朋友,说这就算天堂了吧!她不信,质疑我在夸张,但戴上后,也静静地点了点头。我们之后进了咖啡厅讲分别后各种的奇闻乐事。当外面的光线渐渐暗下来时,我们突然意识到太阳马上就要落入海里了。于是丢下吃了一半的面包圈,急急忙忙过三条马路,像在和天边的那轮红日赛跑。海水辽阔得像要把整个世界吞下去,我甚至担心在沙滩上雀跃的小黑人影会在瞬间消失掉。沙滩上零零星星地分布着安静的观看海上落日的人。他们的静穆让我对面前的海面心生一种奇特的敬畏来。每个人都在逼视着这轮红日由盛大转入消失得无影无踪的过程,我几乎觉得这是个伟大而悲凉的时刻了!
04.这曾经是他们的故乡,北美印第安人的故乡。但天上的云不屑为此做证,它们只是喜欢聚集然后散去,有时候飞快,有时候缓慢。关于故乡,回忆似乎永远是关于童年的无知和少年的错觉;关于初次的错愕和从此便喜爱上了这种错愕;关于喜欢的一种味道和憎恶的一个声音;关于失望和狂喜;关于害怕和熟练……这错综和复杂随着老去而变成了世上最美好的东西,每每看到天上的白云飘过,都觉得它们曾经见证过自己的美好,那种只有在故乡时的美好……而印第安人好像更加聪明一些,他们不依赖云朵,他们雕刻图腾……
责任编辑 伊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