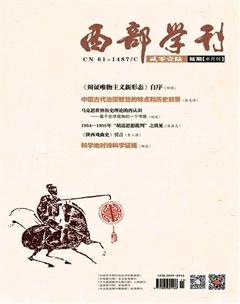让笔尖在人物心田上跳舞
武润泽
能够动之以情的小说,始终对大多数读者有着非凡的吸引力。动之以情即要求写作者用精准细腻的文字把握小说中人物的心理,让读者与小说中的人物心灵相通,进而熏染读者,感动读者。这无疑将心理描写的要求推向了极致。心理描写相对于其他描写手法而言有其特殊性,因其不可名状,即所谓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过,也正是因了这份不可言传,心理描写才可能超越文字本身,达到言尽而意无尽的艺术效果。读者可以通过人物心理的变化反观其行为、样貌等方面的变化,进而可以感知人物在人性、情感、精神等方面的变化。所以说,心理描写看似是在写虚,其实是在写实,心理描写是一切外部变化的根由。写作者对心理描写的重视度和把握的精准度,无疑是小说能否征服读者的关键一环。所以,只有做到让手中的文字在小说人物心田上跳舞,才能让自己的作品,在读者内心世界留下更长久更深刻的回响。
刘心武《煤球李子》,《人民文学》2015年第2期。
或许,世间万事万物都不曾在你心中留下过痕迹,但当你老了,你会发现,青春时的那次无法抑制的荷尔蒙冲动,仍然铭刻在你的心上。一篇优秀的小说,首先要具有可读性,即作者应该有能力让读者产生阅读冲动,《煤球李子》在这一点上可谓少见的佳作。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但小说一开始就用一起猥亵案起头,着实对读者有着十足的冲击力和吸引力。作者从“老流氓”猥亵老年公寓里的一位老太太写起后,慢慢地用温柔细腻的话语,抽丝剥茧般地将这件猥亵案背后的那段跨越时空的感人爱恋向读者娓娓道来。“老流氓”本名叫霍振宝,被“猥亵”的老太太叫郎韵琴,作者用温情的笔调从二人小时候开始写起,讲述了二人成长中的许多记忆烙印,让读者能够在阅读中感受到二人之间那种在特殊环境下不能说破又彼此心知的真摯情感。随着作者逐渐深入的叙述,读者慢慢进入了小说之中,我们会为他们的情感萌动而惊喜,为他们的相知而喝彩,为他们的分离而感伤,为他们的重聚而欣喜。作者用扎实深厚的写作功力,在小说情节、人物与读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情感桥梁,让二者呼吸与共,心灵相通。这样的阅读体验,可谓酣畅。另外,在阅读之时,不得不感叹作者写作的耐心,小说的故事情节,既不拖泥带水,也不粗枝大叶,既不拖沓冗长,也不虎头蛇尾,作者耐心地把整个故事都按常理循序渐进地往前推进,慢慢地解开读者的疑惑,丝毫没有炫技或卖弄的感觉,这样朴实与真诚的写作态度,不禁让读者肃然起敬。煤球李子是霍振宝和郎韵琴爱情的象征,那般的朴实无华又繁盛茂密,像极了那个年代的人们,也像极了现在的人们对那个年代的记忆。
王小王《我们何时能够醒来》,《上海文学》2015年第2期。
小说从父母婚礼上父亲出逃讲起,写了“我”对父亲的寻找与心灵对话,写了母亲精神失常,父亲深居老庙,“我”轻狂放纵,未婚先孕等一系列人间悲剧。“我”在寻找父亲的道路上感悟人生,在陪伴母亲的岁月里看清世界,在自我回归的苦旅中找回幸福。“我”渴望唤醒父亲,唤醒母亲,唤醒世界上所有沉睡的人们,当然,也唤醒“我”自己。但“我”有时甚至不能确信“我”是否是醒着的,“我”是不是也是在另一个梦里,“我在梦里跟你讲了一个梦”。鲁迅先生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打碎了给人看。作者不断地打碎“我”的人生,让“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存在的真实性。当然,绝望之后的呐喊才更能振聋发聩,小说构思巧妙,迂回婉转,亦真亦幻,整个故事在看似纷繁之中娓娓道来,结尾尤其出人意料。
胡金岚《贼的童话》,《北京文学》2015年第3期。
小说的视角非常独特,作者将叙述的焦点定格在一个贼,准确地说是一个良知未泯的贼身上。“贼”这种身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们的“职业”,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的内心世界,在大多数人看来都是鄙夷的,但作者胡金岚却硬是给读者塑造出了一个有情感,有担当,敢于反抗,渴望自我救赎的窃贼形象。贼的身份让“我”终日飘忽,“我”不知道“我的根在哪,我的家在哪,我甚至不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将来要到哪里去,我活着,仅此而已。这样的生活始终在持续着,直到“我”遇到她,当“我”和她的目光相交的一瞬,“一种老贼根本不该有的羞耻感把我变成了一个初做错事的小男孩”,因为“那是一双水一样的眼睛,带着雾一样的眼神”。正是这目光拯救了“我”,“我”开始学着改变,“我”冒着成为团伙公敌的危险把女孩的钱包还了回去,还把自己积攒的钱也一并给了她,让她去治病。在那一刻,“我”与贼再无关系,“我”从身体到心灵都得到了一次彻底的重生。小说的出彩之处在于作者用细腻的心理描写,生动地展示了“我”非同一般的心路历程。从开篇“我”作为一个贼时心里充满的人生迷茫,到后来“我”看到女孩后的心灵激荡,再到“我”对女孩的种种揣度与牵恋,以及最后“我”如英雄赴义般地在团伙的围追堵截中去给女孩还钱包。不同阶段,不同情况下“我”心理产生的巨大的变化,都被作者把握得丝丝入扣,甚至“我”在突破贼这层身份限制之后获得心灵重生时的心理状态,作者也用精准的笔触让读者有所体认,实属不易。作者通过一个贼的自我救赎之路,呼唤着当今时代潜藏在人们心底的那份善良,寻找人性的自救与回归。
张夏《简单生活》,《北京文学》2015年第2期。
一篇好的小说,有时并不在于篇幅的长短,也不在于结构的繁简,而在于小说是不是真正成为了作者的发声器,发出了作者真实的声音。这声音可能是一种希冀,可能是一阵怒吼,可能是一段哀嚎,可能是一腔热忱。《简单生活》并没有曲折婉转的故事情节,也没有高潮迭起的情节设置,就连主人公也是一个丢在人堆里立刻就会被淹没的凡夫俗子。但就是在这样看似流水账般的鸡毛蒜皮的日常记录中,作者张夏为读者传达着一种全新的生活观念,让已经被世俗戒律束缚太久的人们为之一振,引发人们无尽的追问与思索——到底什么才是生活的真正意义?我们又将如何回归生活本来的那份“简单”。小说在情节设计上十分巧妙,作者并没有为了强调简单生活的美好或呼吁人民回归简单生活而刻意为之,反而小说中不乏主人公宋江在自己的“简单生活”中遇到的种种“复杂”的甚至是有违道德的烦恼。这样的叙述方式成功地避免了小说写作中较容易出现的“为强调而强调”的问题,并且也更说明了在当今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想“心远地自偏”是多么的困难。宋江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却无法控制别人的选择,更不可能强迫身边的人也选择和他一样的生活方式,哪怕这个人是他的妻子。作者巧妙设计这样的矛盾,将现实与理想的对立真实地呈现出来,也让读者更加深刻地领悟了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情怀。小说以至真至简的话语诉说了一个简单却满含深意的故事,文学创作其实需要这样朴实的文字,功底的深厚不需要奇巧的字词罗列来标榜,能力的大小也不需要繁复的结构来彰显,比起小说本身,作者张夏做到的这一点可能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