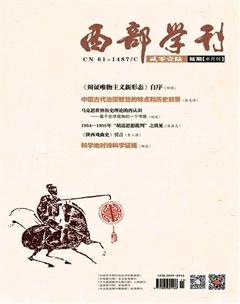童年的最后一个夏天(短篇小说)
莫飞
我在八岁的时候坚定地认为,我和迪庆的友谊会像曾祖父与他堂弟一般,沐浴着廊檐下春天的阳光,把头低垂在两腿间,数着蚂蚁度过一个下午的时光。我在十岁的时候,坚定地推翻了这种想法,我和迪庆毫不怀疑并诚惶诚恐地相信,我们绝对活不过那个闷热的夏天。
关于那年夏天对死亡的恐惧,我们曾在一段时间内整日下午都坐在树林密集的苔藓地上为自己刻划木碑,用我从村里张木匠那偷来的墨汁涂抹上陈洲之墓,史迪庆之墓。阳光投下来树林里的光点,在我和迪庆的脸上微微抖动,我看到他的不安和焦虑,他看到我的无助,我们两人抱头痛哭,像生离死别一般。
矿山背面的树林是我们最隐秘的墓地,这里葬着一只死去的伯劳鸟,一条叫阿童木的狗,还有秦美香的酱紫色内裤,还有一堆公鸡的鸡毛。我们有条不紊的死亡前准备被轰隆的声音给震碎了,远处无数的碎石自山顶像灰色的瀑布倾泄下来。我们垂头丧气地从灰蒙蒙的树林里走出来,相互看了一眼,山顶持续的爆破还在进行,迪庆讲了一些什么,只看到他张了嘴,却没有声音。我们再也没有去过那片树林,也没有提过死亡。迪庆在秋天离开了我,他究竟以何种方式离开,我不得而知,就像他来的时候一样,突然之间就走进了我的眼睛,我的世界。
几天来,远处路两旁的水杉树闪烁着一种明朗嫩绿的色彩,今天我在上学来的路上发现了大豆那像眼睛般深紫色的花朵,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在教室门外罚站。湿润晴朗的天空梦幻似的飘着轻柔的四月云,校园里惟一的棕榈树,张着像巨伞一样的手掌,轻轻地托着明媚的阳光。它的姿态让我想起秦美香杂货店门口不长芭蕉的芭蕉树,去年被冻僵的风情万种的大叶子,此刻一定冒出了新鲜嫩绿的叶子。今年我再也不会拿着她的梳子,把硕大的芭蕉叶梳成像女孩长发一样的细条条了,不然她店里新进了光明牌甜奶都不会卖给我。恍神间,一个干瘦的男孩出现在眼前,他是如何穿过学校操场,走到我的面前,我一无所知。我警惕地看了看他,用脚踢了踢墙,以分散一下我被罚站的困窘。男孩的身边站着一个矮小的男人,尖脸,小眼,头发蓬乱。过分肥大的灰色夹克,衣领拉链一直拉到了锁骨以上,淹没了他的肚子,使他脸部的表情看起来僵硬。男孩的个头比我矮了一截,小麦色的脸上分布着几块白色的癣斑,小小的眼睛上面长了一圈像女孩子一样长的睫毛。他穿了一件簇新的灰色灯芯绒西服,上面还有几条鲜明的折痕,三颗像电珠一样发亮的纽扣,一条黑色裤子下面罩着白色亮眼的球鞋。
男人先在窗口张望了一下教室,接着敲了几下门。班主任是来自城里四十多岁不苟言笑的女人,脸上两道法令纹会让人想到山里阴恻恻不见底的峡谷。她打开了门,目光潦草地扫了一眼眼前的这对父子。她招呼了一下那个男孩,进来,跟同学们打个招呼。接着,她的余光扫到了我,把我喊了进去。我扭扭捏捏蹭着落白灰的墙壁过去,她一把抓起我的衣领揪进了哄堂大笑的教室。
老师为了惩罚我天天迟到,把这个叫迪庆的来自四川的男孩和我安排在一张桌上。我听到同学们的窃窃私语,谁都不愿意跟转学进来的新同学坐一起。“他的身上有味,经常不洗头发,”女生说的时候会假模假样地捏着鼻子,好像闻到了似的。“还在上课的时候抓虱子。”这句话让我的皮肤一阵瘙痒。
迪庆没有女生们说的陋习,他甚至比我干净,擤鼻涕的时候还会找出一块手绢来,不像我,直接擦到了鞋帮子上。迪庆认为我是个了不起的人,因为我可以天天被罚站在教室門口,直到两节课后才被允许进教室。他除了崇拜我,还喜欢上天天送我到路口的狗,阿童木,是一条会撒娇粘人的黄毛母狗。学校门口有一条种着水杉树的石子路,走上一段便是一个丁字路口。一端通往村里,要穿过一个小岛似的桑园,另一端便是石矿场,迪庆住在矿区。我和迪庆就在这路口分道扬镳,第二天他很早就会在这路口等我和阿童木。爷爷曾经关照过来,千万不能让阿童木跟着过了路口,不然狗会成矿工们的下酒菜。所以,跟阿童木在路口分手并叫它乖乖回家是需要很长时间的。阿童木追着迪庆在桑园里乱窜,迪庆当然也成了天天迟到的人。老师们都说迪庆是被我带坏的,我觉得他是被阿童木带坏的。
我和迪庆罚站在教室门外。我们用鞋子把墙灰都耐心地踢下来,迪庆当初白得亮眼的鞋黑得辨不出颜色。云雀在空中划出剪影般漂亮的身影,五月的各种香味从我们身边经过,远处的水杉的叶子早已翠绿成一片。我们禁不起这种诱惑,慢慢向学校外面走去,后果就是令人生畏的办公室罚站。
刚开始我们还能鼻尖贴着墙壁,慢慢我们为了看清墙上钉着的中国地图,后退到老师的椅子上。迪庆嵌了许多黑色固体物的指甲在地图上幅员辽阔崇山峻岭的四川省部分游移。
“陈洲,老师说这里的山根本就不叫山,是丘陵。”迪庆将指甲一直往东,停留在杭嘉湖平原上。
“嗯,丘陵也是山。”我可没见过什么山,我们这里的人都管这叫山,以前冬天到山里捡柴火,松球,还会遇到小松鼠。春天的时候,山坡的茶树林里全是系着头巾的女人在采茶叶。可是这两年,这座郁郁葱葱的山像突然裂开了一道很大的伤疤,露出了黄色的岩石。许许多多像迪庆父亲这样的人,像蚁群一般蜂拥在山上没日没夜的劳作。轧石机隆隆地作响,炸山警报声盘旋在村庄,山的伤疤逐渐扩大,那些从村庄望过去青黛色的山体逐渐消失了。
“如果丘陵被开挖完了,就真的叫杭嘉湖平原了。”迪庆把手又移到四川省那部分去了。我们在地理课本上学过自己的家乡,杭嘉湖平原,6400平方公里,盛产茶业和丝绸。每念完一段,迪庆都会小声嘀咕,我家乡可不是这样。
我问迪庆,如果他爸知道他被罚站,会不会揍他?
迪庆几乎是欢快地摇摇头,“他才不管我呢,只要把我送到学校,其他才不管。”他咬了一下嘴唇,又眨了下眼睛,长长的睫毛像阴影一般盖下来,这些动作都像一个秀气的女生。
迪庆的爸是石矿上的包工头,管招工的头头。据说迪庆的老家有很多人都巴不得送礼送钱要把儿子送到矿上,不是亲戚,拉不上关系,还来不了矿上。后来迪庆把我介绍给了小白鼠,就是他的一个远房表哥。小白鼠是绰号,因为皮肤长得白,身材瘦长,有两颗小虎牙,大家就送了他这个绰号。迪庆告诉我,因为远房表哥家在深山里,天天被来来去去的雾气笼罩着,那里的人皮肤都很白。
我们下学后会去矿场找小白鼠,他会请我们去美香店里喝甜牛奶。多数情况下小白鼠还在拉车,右肩膀上缚着一根绳子,穿过他鱼腔似的上腹部,两只手紧抓着铁车的车把,遇到一个上坡,他得往两个手掌吐口唾沫,像旁边的工人一样,“嘿唷嘿”,响亮地喊一个口号。下坡时,卷到膝盖藏青色工作裤下面像竹竿一样的细腿,总是绷得紧紧的,我们能听到他的布鞋和细沙路面发出很响的磨擦声。他把石料推到码头,往深不可测的船里倾倒下去,河面飘荡起一团团的粉尘,把夕阳落在水面的光照都变得模模糊糊。装满石料的船鸣一声笛,雄赳赳地向着太阳落下的地方驶去,船上一面紅色的旗帜在猎猎招展。我看到这景象一点也不高兴,因为我的父母就是开船的,大部分的时间他们都在船上跟阿童木生的小狗待在一块儿。
美香杂货店开在矿场外的石子路旁,红砖砌的平顶屋,周围的金樱子和爬山虎顺着屋前搭的丝瓜竹棚子登门造户。门前还种着一棵很大的芭蕉,听说是从很远的南方过来的。芭蕉叶上全是厚厚的一层灰,我看到好几次,美香拿着湿抹布在擦叶子。傍晚矿工们一放工,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窝在店里,盯着14寸的黑白电视机。来得晚的,坐不下,就搬个长条凳子坐在外面瞅芭蕉树抽烟。矿工们说美香长得跟芭蕉叶一样,风情万种,就是骂起人来也像叶子拂在脸上,痒痒的。
美香很少骂人,我只见过一次。那天我在看电视,她到外面收衣服,进屋后边扔衣服、边用不高不低的声音说,“偷什么不好,短裤也偷,迟早一天这些个人要吃苦头。”
村里人都说美香开在棺材上的店几里外都能闻得到一股臊味。“那是矿工们都在墙角边小便。”这个我最清楚了,有一次一个矿工刚对着墙掏出家伙,便被美香拿着扫把追着打。爷爷给了我一记爆栗,敲得我脑袋发晕,他说大人讲话,小孩子乱插什么嘴。迪庆刚来那会儿听不懂方言,许多话都请我翻译,我挨了一个爆栗子,很不耐烦地说,“最早开石矿的时候,她的老公古力是炸山的,爆破,结果被炸死了,听说可惨了,落下来的每块石块都粘着血,他妈还要了这样一块石头当垫脚石。”我当然没见过这么惨的场面,只是听说,村里的男人再也不敢去矿山做了,矿场只能去外地招苦工。“美香要求矿场赔偿,并答应给她在场边盖一个房子开一家杂货间。店里生意好,村里人眼热,都说她的店可是开在老公的棺材上。”
美香给我和迪庆一人一瓶甜牛奶。她顶着一头烫得时髦的卷发认认真真地趴在玻璃柜台上记账。年轻的矿工都不发工资,只能隔一段时间领一次几百块的生活费,等做满一年,再给结算。所以他们发的少得可怜的生活费基本全被美香一五一十地记在账本上了。我们喝完牛奶走的时候,小白鼠还要继续留在店里。小白鼠的话从来不多,他跟美香讲话的时候总是讲慢,像迪庆在课堂上发言,努力把属于自己方言的那些附属音去掉。可正是他慢慢悠悠的样子,显得滑稽,美香好几次从算了几次的账本上抬起头,卷发下露出一双拼命想忍住笑的黑白分明的眼睛,忍得肩膀都会抖动起来。
矿上的爆破工二虎拉着他的老鹰站在芭蕉树下,总是用不明朗的脸色和一双促狭的眼睛瞟向屋内的两个人,又暗示性地发出沙哑的声音与我们交谈,那些成人间的玩笑让我脸红。他白天总是有很多时间出来溜达,他也是惟一到村里不被当小偷防着的人。“这个人脑袋都别在腰上工作的,说不定哪天就跟美香的老公一样了。”村民说的时候,脸上总是挂着同情和无奈。
被缚了一只脚的老鹰扑楞着被剪短羽毛的翅膀神情紧张地注视着竖起背毛的阿童木。我拉着迪庆总是以最快的速度逃离二虎追踪的眼神,直到很远,还能感受到背后仍像被他老鹰的利爪攫住的感觉。阿童木在确定自己不会受到利爪的威胁后,朝着老鹰汪汪叫了两声,又飞快地赶上我们。
迪庆一定要我去带他看那块古力染上血迹、后来被他妈铺在门口当垫脚石的石块。老太太驼背耳聋,独自住在长满构树的河边小屋。她的屋子墙壁是用乱石垒的,涂了泥浆灰,屋顶稀疏的瓦片上长了许多直挺挺的瓦松。石块就放在门口,老太太坐在上面,跟我曾祖父一样喜欢长时间耷拉着脑袋。迪庆非要过去看血迹,我说没有了,早就没有了。
我们去附近的树林子看别人捕鸟的网上有没有鸟,山被开挖后,很多的鸟都来到村庄附近的树林,树林里能捕到很多平时见不到的品种。张木匠的老鹰也是一次炸山的过程中,被声音震晕才倒栽葱一样掉在了桑林里。这一次我们发现了一只伯劳,它的翅膀在网上挣扎的时候受了伤,不能飞行。迪庆说,拔了毛,吃了它。“这是黄伯劳,鸟类的屠夫,我们这里从来不吃这种鸟。”我决定带回去养着。“你怎么什么都想吃。”我对迪庆说。
“我看矿上好多人都抓过这种鸟来吃。”迪庆说。
“他们是一群饿死鬼,还经常来村里偷鸡偷鸭,还揭过我们家锅盖,扛走过一袋米,还挖过地里的红薯,采过南瓜,摘过藤蔓上的嫩丝瓜……”为了那一袋米,我奶奶站在丁字路口朝着矿山方向足足连哭带骂了两个多小时,我只好坐在一旁陪着。
迪庆低着头,看着我手里拼命转动的伯劳。
他穿着一件好像是他爸爸的灰色过时西装,快没过膝盖,下面是肥大的运动裤,裤腿层层叠叠,整个人看起来就像蜷缩在衣服里的毛虫。
他一把夺过了伯劳,把它摔到了地上。阿童木一下子扑了过去,我喝住了它。伯劳滚了许多圈,扑腾着翅膀,慢慢地安静下去。
我推了迪庆一把,他一屁股坐到地上。我看到他伸出手捡起伯劳放进了自己宽大的西服口袋。
“狗改不了吃屎。”我用电视里学到的一句话骂他。
我们一前一后互不理睬。河边的小屋前老太太已经不在了。
迪庆用他颤抖的声音问我,敢不敢去石块上坐坐?
我承认那个时候只有嘴上大胆,其实从坐上去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屁股到肚子都在打颤。阿童木一直在脚边拱我。最后一缕光线从我们头顶消失,逐渐生起凉意的石块上,我们谁都没有离开。
“我表哥,就是小白鼠……其实一直吃不饱……他晚上还经常会跑到我睡的地方,从我的床底下掏出红薯来,连皮都不削,像只老鼠一样啃。”迪庆的声音像一种抱怨,好像是为了博得我的同情。可我没有搭理他。他继续自说自话,“别人给他说了门亲事,可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他就找到我家,说想出来打工,等赚到了钱,再回老家结婚。”
我们在暮色里各自回家时,都没有说再见。
阿童木站在路口迟疑地看着我们朝两个方向越走越远,它朝着迪庆轻轻地叫了两声,迪庆没有回应它,它又飞快地撵上我。
我和迪庆发生了旷日持久的冷战。这期间有两件事。一件事是因为迪庆跟不上学习,留了一级。第二件事是桑园受到粉尘污染导致无法饲蚕,村民们带上了锄头、火钳、扫把,声势浩大地到场门口理论。联防队也赶来调解。村民们顺便把村里鸡鸭被盗的事一股脑摊出来,要求场里给解释。
我看到迪庆站在他爸和一群矿工间,都和小白鼠相近的年龄,嘻笑地看着神情愤怒的我方村民。我向迪庆挥了挥拳头,我看到他躲闪到人群里,只露出宽大的衣摆在人群里闪闪烁烁。
村里和矿上永远达不成一致。矿场表示,场里已经有专门对付工人偷盗的法子了。可村民们不相信,有段时间,村里的失窃食物的现象少了很多,可过一阵子又有人家发现,家里又少鸡少鸭少米了。
美香说:“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让矿工们吃饱,都是十几二十的青年,干那么重的体力活,吃的都是啥?”矿方代表腆着肚子说,这比他们在老家吃得好多了,老家都没得吃才出来打工的。迪庆的爸爸总是蹲在一边抽烟,不表态。迪庆曾经说过矿上的老乡亲戚们晚上摸到他家屋子里聊天,临走时总不忘记顺几个地瓜,或者一根烟。
我和迪庆重归于好,是因为阿童木的死。
“陈洲,你家的狗疯了。”放学回家的路上,有人冲着我喊。
“你才疯了。”我说。
“陈洲,你家的狗疯啦,在田里乱窜呢。”我遇到第二个人冲着我喊。
我瞪了他一眼。“你他妈的才在田里乱窜呢。”
“小洲子,阿童木吃了投毒的肉,现在正发癫。”我隔壁割草的爷爷跟我这样说。
我扔下了書包。跑到田野,看见阿童木正在狂奔,绕着田野跑圈,整个身体像迅速滚动的火球。我拼了命地呼喊着它,嗓子都喊哑了,我感觉它身体里那团火焰,盖住了它的听觉,遮蔽了它的双眼。它从我身边跑过,朝河水的方向跑去,我看到了它的一闪而过睁大的惶恐的眼睛,像正往山顶坠下的不安的落日。我追赶着它,看见它像一个失重的物体,“呯”地落入了桥底的水里。
迪庆没脱衣服就跳下河,抱上了阿童木。我们都以为,它还活着,偶尔还会抽动一下肢体,可是天黑了,阿童木逐渐变得僵硬。我们两人抱着阿童木哭哑了嗓子,发誓要为它报仇。
我给阿童木戴了红帽子埋在树林里。那是一块平整的土地,在矿山的背面,远离着炸山的危险。迪庆告诉我,伯劳鸟也被埋在这里。
整个冬天,我们一直在寻找毒害阿童木的人。白雪覆盖了桑园,河流长出了薄冰,光秃秃的水杉树,枝桠上留着一大蓬铁锈红的杉叶,那是鸟窝。迪庆告诉我,给阿童木下毒的肯定是二虎,因为只有他懂得怎么对付狗。我想起二虎对阿童木的眼神,好像盯着收衣服时美香丰满的臀部。
迪庆说,二虎和小白鼠也是远房表亲关系。比小白鼠早来一年矿上,一直做爆破工,在家的时候就死了老婆,没有牵挂。二虎住在一个临时搭建的木棚子里,像这样的棕色的木棚子,还有由石块简单搭就的石屋子缀满了山坡。晾衣绳纵横交错地穿过这些屋子,上面晾着肩膀打了补丁的衬衫,软塌塌的蓝色秋裤,露出棉胎的被子,香烟烫过的粗布条纹的床单。我们在这些绳子上找到了一个系在狗脖子上的皮项圈,上面还有一个铜质的铃铛。看,这就是证据。阿童木肯定是被他下的药。我和迪庆一厢情愿地认为,并决定把二虎屋子里的被子搬走,让他晚上吹西北风。
昏沉沉的屋里面只有四个角垫了砖块的木床,一堆灰色的破棉絮堆在角落。迪庆准备去抱那堆棉絮。
突然一阵很大的扑腾声吓了我们一跳。我看到二虎的老鹰在阴暗的角落里,前面因为光线暗淡,我们都没发现它。它那两颗镶了黑色水波纹玻璃球般的眼睛正发出警惕和凶狠的光。我们想不明白二虎为什么要养老鹰。我拿了墙角的一根棍子,朝老鹰头上做假动作。老鹰突然张开它的大翅膀朝我扑来,我吓得直往后退扔掉了棍子。
迪庆说:“别管老鹰了,我们把被子抱走吧。”
“这地方晚上睡着怪冷的吧。”我看了一眼屋子。
迪庆没回答我,抱起了被子,眼睛却瞟到地上一样东西,是被子里掉出来的。我蹲下去捡起来,是一条酱紫色的女式三角裤。
“这是女人的。”我说。
“这附近没住女人。”迪庆想了一会儿说,“你说是谁的?”
“我怎么知道是谁?”我想起了美香的黑色波浪卷发,“反正一块儿全都拿走。”我说。
我们把被子藏在树林里,把酱紫色内裤像安葬阿童木一样埋了起来。
整个冬天我们一直处于这个秘密的喜悦中。虽然我们没有打听到二虎是否被我们抱走了被子而受冻,是否被我们发现了内裤的秘密而不安,我们一厢情愿地认为,我们高兴了,他肯定就受到惩罚了。
二虎真的受到惩罚了,可不是来自我们。我们在美香店里蹭电视看的时候,听到警报声响起,然后爆破的声音开始了,巨石哗哗滚落的声音。接着我们听到无数嘈杂声,门前奔跑过许多矿工,美香站在门口,用手捂着胸口,喃喃地说着:“出事了,矿上一定又出事了。”美香拦住了奔跑的小白鼠。小白鼠说,二虎放炮的时候躲避不及,炸伤了。
二虎浑身血淋淋地躺在担架上,我和迪庆趴在桥的栏杆上看到他被抬到船上。那天黄昏矿上难得停工了,耳朵似乎一下子承受不了寂静的压力。大伙都沉默地站在桥上,夕阳最后的余光落在远处的水面上,突突直响的挂桨船载着二虎成为一个黑点消失在那片波光里。
我们跟着神情惆怅的小白鼠去二虎屋里收拾明天要送去的衣物被子。美香的店里没有矿工在,他们都躲进自己矮小潮湿的屋子里去了。电视机空空荡荡地响着一对男女单调的对话,美香背对着门坐着,跟门外那棵美人蕉一样在无风的傍晚纹丝不动,连我们走过,都不扭过头来看一眼。
没有东西可以收拾。二虎床角落里一堆四季衣服,疲沓的破洞的毛衣,夏季的背心,蓝色白条纹的秋裤,小白鼠挑不出可以明天送到医院的东西。“被子呢,他床上怎么没有被子?”小白鼠好像突然间发现床上连一床被子也没有,只有一条很薄的绒毯。
我和迪庆在昏暗的光线下交换了一下目光,我们不能告诉小白鼠是我们扔掉了他的被子,当然也包括酱紫色内裤的事。
我们又折返到美香店里。美香依旧保持着我们经过时的样子。小白鼠说了找衣服明天送去医院的事。“也许就回不来了,在这矿上,这样的事太多了。”美香顿了一下说,“他干这个迟早要出事的,我老早就跟他说过,他不是贪图多一些钱吗……现在好了……”
外面的夜很黑,矿上一片静寂。屋里昏黄的灯光流淌到丝瓜架下,手掌形的叶子成了地上一个个随微风抖动的黑影。小白鼠自己去柜台里拿了一包烟,蹲在门边抽。他划了好几次火柴,火都被风给吹灭了。他粗糙开裂的手握成了半个空拳的形状,头低得几乎快钻进去,还不能留住那朵火柴梗上细小的火光。他保持着这个姿势很久都不动弹一下,叼在嘴里的烟掉在了地上。我看到他的侧脸,已经不是刚来的时候大家叫他小白鼠的样子了,薄薄的一层皮贴在颧骨上,在晦暗的灯光下,就像学校教折纸时用的发光的蜡纸,随便一抓,全是褶子。
美香拿着打火机走过去,捡起了小白鼠脚底下的烟,塞到他的嘴里,替他点着了烟。他们两个人面对面蹲着,顺着流淌到店外的灯光看向黑夜。我和迪庆从来没有这般紧紧相偎在一张凳子上,并且不发出一点吵闹的声音来。
那个晚上,爷爷用桑条棒子撵着一路哭哭啼啼的我,原因是我忘记回家吃晚饭了。他很奇怪平日里能灵活躲避他棒子的我,为什么会挨了那么多下,并且哭得这么伤心。
“美香也当真是命苦,这个二虎愿意当爆破工,不就是想多赚钱来娶她吗?”村里男女老少三三两两在村口的亭子里,谈论着今天矿上有人炸伤的事。
“这男人呐,都是毁在女人身上的。”爷爷已经忘记撵我回家吃饭的事了,跟村民们聊起来。我独自一个走回家,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一直觉得很难过。我想好了,等二虎回来,我一定找一床被子给送回去。
大约两个月后,二虎回来了,锯掉了一条腿。他天天在美香店门口坐着向来往的人展示着他的伤痛,从膝盖处缝合的伤口像一条宽大的拉链。我曾想送被子给二虎,没有成功。出院时有人给他送了许多东西,包括崭新的被子。可他说他很快就会离开矿上,因为没有人再想要他了。他说的时候盯着倚在门框上的美香。美香伸出一只手好像要从口袋里掏瓜子,又换了一只手放在另外一个口袋,结果什么也没掏出来,她就转身走回店里。
二虎的老鹰从木棚里逃走了。它剪短的翅膀已经重新长出,挣脱了链子,飞离了昏暗低沉的木棚。如今它停在水杉树顶上,有好多知道它来历的人都盯着它看,帮二虎想对策。我和迪庆挤在人堆里,兴奋着,恐惧着。
“它忘记怎么冲上蓝天了。”美香倚在门框上。
“它被关久了,现在只是暂时的,它会飞上去的。”小白鼠看了一眼美香。他们的眼睛里交流着一些东西,水杉的树影,蓝天,或者鹰的翅膀,我这样想。
有人找来了梯子为二虎抓老鹰。老鹰一面用爪子紧紧抓住树干,一面扑腾着翅膀试图飞起来。我仰着头听到自己心脏剧烈地跳动,那只老鹰猛烈地扇动翅膀后,好像发现了自己的飞翔能力,慢慢地往上飞去,毫不犹豫地越飞越高。
“它不会回来了。”美香说。
这回小白鼠没有接话。我们都盯着天空,寂静间,老鹰消失在蓝色的天空里。大家都收回了视线,不经意间,又会抬头看看老鹰消失的天际。
随着初夏的来临,我和迪庆游玩的时间变得漫长而单纯,好像经历了阿童木、二虎还有老鹰的事之后,我们都长大了许多。我们会沿着矿山的背后走出很远,从最初林子的营地到树林的纵深处。我们踏进了一大片廣阔的地方,高大的松树和楝树边躺着许多的奇形怪状的石头,岩石上还攀着各种藤类,长着一簇簇深浅不一的苔藓。我要去揭一块下来。迪庆阻止我:“不要动它们!”我问为什么,他说在他们家乡,山是圣山,所有的人都只能膜拜,更别说上山采石头挖花草了。
“山上有神仙?”我问他。
迪庆郑重其事地点点头。
我们彼此不再说话,仿佛笼罩在一片神仙经过的圣山中。我们坐在岩石上,整个树林安静极了,只有鸟儿偶尔扑翅的声音。地上去年落下的松针叶厚厚的一片,斑驳的阳光透过树叶子洒下来,抬头仰望,树叶的间隙里,天空湛蓝一片。风慢慢地穿过我们的身体,我嗅到了初夏忍冬的香气。
小白鼠出事那天,我和迪庆正在桑园中采桑椹吃,吃得满手满脸的紫色。我们听到桑林外人声嘈杂。一群人涌了过来,接着在人群中看到了低着头的小白鼠,以及他被人反扭着的两个胳膊。他的脸比往常更加的惨白。我们不明就里地跟了上去,直到看见村里的女人手里拎着一只死去的鸡。
我和迪庆犹豫着要不要跟去矿上。矿上解决偷盗的办法,是造了一间屋子。里面摆着长条凳子,系着皮绳,还有电击的棍子。屋子特地开了一个很大的玻璃窗,村民可以站在那里看。
路过美香店的时候,人群突然不走了,在那里扭动起来。我跑上前去看,原来是小白鼠蹲在地上,好几个村民推拉着他,他就是不肯起来。这个时候瘦弱的他好像一头固执的牛。我说:“我们去告诉美香吧,美香能向矿上求情吗?”想起记在小白鼠账上我们喝过的甜牛奶,我就感到心慌。
“没用的,我爸上次说了,不管谁犯事,一样照打。”迪庆的嘴唇上全是紫色的,他说打的时候让我看了觉得害怕。
村民和矿方进行交涉。大家站成了一个圈,我和迪庆不敢看小白鼠,茫然无绪地将眼光盯着几棵在风中乱晃的狗尾巴草。可我还是不小心和他的目光相遇了,他朝我虚弱地笑了笑。我撇开嘴笑了一下,眼泪就要奔涌出来。
美香也来了,她站在阳光里,不停地绞着发白的手,眼睛死死地盯着地面。
小白鼠被送到阴暗的房间里。外面和里面一样寂静无声,闷热的夏天让人觉得窒息。过了很久,我们随着几个矿上的人进去,小白鼠蜷缩在角落里,这让我想起二虎房间那床堆在角落的破棉絮。他被电击过,暂时失去了意识,身上还有许多拳脚留下的痕迹,裤子被扯破了,裆部有一个很大的洞。
小白鼠躺在床上的时候,美香经常拉着我去。他的脸一直处于青灰状态。美香叫我去门口坐着。我听到他们一直反复地提起那只老鹰。比如飞出去,外面有广阔的世界啊。小白鼠总用低沉的声音说他飞不动了。二虎也来看过小白鼠,他是来表示歉意的,他说是因为自己想吃鸡,小白鼠才答应帮他去弄的。美香朝二虎吐了口口水,我从没见过这么粗鲁的美香。
那个夏天注定要在快要窒息的闷热中结束。小白鼠的尸体在桥墩下被水草缠住了。联防队来查,开了个证明是溺亡。矿上很沉默,村民们不再谈起此事。只在私下里悄悄地说,小白鼠是被打残了,失去生育功能,寻死了。小白鼠被火化,骨灰盒一直放在他生前住的阴暗潮湿的石头房子里。
我和迪庆再也不敢走近那屋子,我们整日在惶恐中,我们总觉得死亡离我们这么近。
美香消失了。听说,她把所有赚来的钱都给了驼背耳聋的婆婆。二虎一瘸一拐管理起了杂货店,每天给美人蕉擦叶子,他跟谁都没有谈起过美香。随着消失的还有小白鼠的骨灰盒。小白鼠的家人来领的时候,矿上才发现骨灰盒不见了,他们出了一些钱便打发了啼哭着的家属,其中有一个清秀短发的女人是小白鼠未过门的妻子。
迪庆随着他们消失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竟然都没有跟我好好道别。
责任编辑:李 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