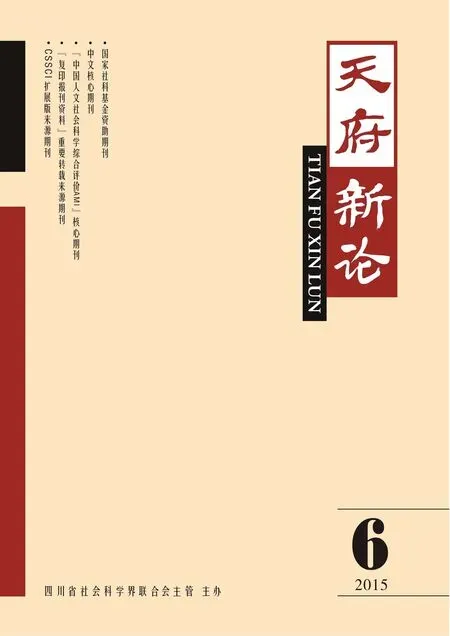女性主义、关怀伦理与当代公共行政的重塑
琚挺挺
女性主义、关怀伦理与当代公共行政的重塑
琚挺挺
女性主义从性别的角度对公共行政领域的男性特质的批判,要求引入一种基于女性视角的价值观念。与男性相比,女性更为重视的是对人之“关怀”,而“关怀伦理”集中地体现了女性主义的伦理主张。通过梳理女性主义对当前公共行政的批判以及“关怀伦理”的基本内容,本文主要从“关怀伦理”这一立场出发,并从公共行政的价值理念、公共事务的范围、公共治理主体以及治理方式等多个层面,思考了重塑当代公共行政的可能。
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公共行政;程序主义;性别困境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开始遭到后现代思潮的严峻挑战,①这一方面出现了大量的著作,如:C.J.Fox&H.T.Miller.Postmodern Public Administration:Toward Discourse.Thousand Oaks,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1995;D.J.Farmer.The Langua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Bureaucracy,Modernity,and Postmodernity.Tuscaloosa,Alabama: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95;O.C.McSwite.Legitimacy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A Discourse Analysis.Sage Publications,Inc.,1997;G.Adams&D.Balfour.Unmasking Administrative Evil.Thousand Oak:Sage Publication Inc,1998.后现代理论家们全面检讨了现代性及其思维方式的影响,“而在公共行政领域,现代性的影响则突出地表现为技术理性的霸权与对社会问题表达方式的限制”。〔1〕作为后现代思潮当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女性主义者们同样对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进行了持久、深入的批判。引人注目的是,女性主义的批判不仅反思了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更试图从根本上挑战主流公共行政范式的知识基础。根据女性主义者的理解,我们当前的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男性所构造的,反映的也只是一种男性看待世界的方式。具体到公共行政领域来说,男性中心主义通常体现在诸多方面:从围绕着公共行政合法性展开的各种辩护(主要体现为专业知识、领导才能、个人美德等主题),②关于从女性主义视角对公共行政合法性提出的质疑,可参阅〔美〕卡米拉·斯蒂福斯:《公共行政中的性别形象》,熊美娟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到日常行政过程当中对专业知识的强调以及对规则、章程和法度(即“程序主义”)近乎刻板地遵从,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出某种男性的立场。与之相比,女性更为看中的则是关心、照料他人的能力,也就是内尔·诺丁斯(Nel Noddings)等人大力倡导的“关怀”(caring)。当我们回溯孕育了公共行政学③在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美国公共行政学的历史,因此,我们不讨论美国公共行政学与欧洲公共行政学之间的差异。之美国“进步时代”(the Progressive Era)的时候,女性的“关怀”行动曾为这一时期的政府改革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遗憾的是,它很快地消融在公共行政学者们所迷恋的“程序主义”之中〔2〕,以至于我们现在需要“重新”思考其有可能为公共行政做出的贡献。
文章首先简要地回顾了女性主义对当前公共行政领域的批判,通过引入一种基于女性主义视角的“关怀伦理”,我们试图从这一“关怀”的立场出发,思考重塑当代公共行政的可能。
一、“性别困境”:女性主义对当前公共行政的批判
作为一股重要的思潮,女性主义早已在学界耳熟能详。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主义已经得到了某种清晰、一致的界定,与之相反,“今天大多数女性主义的理论家不再相信只有一个明确的女性主义的定义是可能的”〔3〕。不过,这些女性主义者们仍然会在很大程度上认同:女性主义首先代表的是一种对现代话语的批判,“在这种现代话语中,男人是人的典范,而妇女则是另外的一种东西,一种附属的性别”,换言之,“大写的‘人’(Man)字直接掩盖了男女之间的差别,暗中支持了男性对女性的统治”〔4〕;其次,我们需要真正地引入一种值得尊重的女性的视角、价值观念或者思维方式。因此,卡米拉·斯蒂福斯(Camilla Stivers)指出,女性主义至少向我们传达了以下三层意思:“假定性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析变量;一个对女性当前的地位和前景的重要看法;或用格达·勒纳(Gerda Lerner)的话来说,‘一套理念和实践的体制,假设男性和女性必须平等承担工作的权利,分享对世界的认识和梦想’”。〔5〕
由于女性主义自身的复杂性,女性主义者们对公共行政的批判也是从多个不同的层面来展开的,主要包括:(1)基于经验研究的结果,对当前公共行政领域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的反思;(2)彰显出女性的价值立场,主张必须推翻在当前公共行政研究之中占据着主流地位的男性话语;(3)彻底挑战、颠覆这一领域已然形成的普遍信仰、概念以及话语体系,试图构建一种“倡导性别多元、身份解构和话语重构”的女性主义公共行政理论。〔6〕在下文中,我们将主要借助卡拉米·斯蒂福斯教授的研究,说明女性主义对现有公共行政理论模式的批判。这不仅仅因为斯蒂福斯教授在这一领域已经取得的杰出声誉,更重要的是,斯蒂福斯的讨论直接关注了公共行政本身的合法性(legitimacy)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既从根本上影响到对公共行政之本质的理解,从而牵涉公共行政领域的知识积累、理论建构,而且,它还会为公共行政的实践形态打下深刻的烙印。
斯蒂福斯敏锐地观察到,“美国政治思想史建立以来,维护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就一直是其主题之一”。〔7〕在她看来,传统的、为公共行政合法性提供的各种辩护都不约而同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公共行政人员的基本素质上面——主要包括专业知识、领导才能、个人美德之类。不过,斯蒂福斯认为,这些不同的辩护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取得过成功。以我们最为熟悉的专业知识为例,早在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等人那里,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就已经得到了从这个角度为其进行的辩护。具体来说,公共行政被理解为“只是简单地通过科学的专业方法来执行立法的命令,……行政是合法的,因为它是中立的”〔8〕。尽管这种观点实际上已经遭到了“过于简单,与官僚制的现实不符”〔9〕的责难,从专业知识的角度而展开的论述,仍然为公共行政的合法性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经典、最普遍深入的辩护。遗憾的是,合法性问题并没有因此得以解决,如同西西弗斯的悲剧命运一般,合法性这块“大石”几乎总是在快要到达山顶的时候,又一次滚落山脚——当某些公共行政学者迫不及待地转入讨论“相对次一级的问题,例如专业知识的具体性质,或者说公共行政从逻辑或者策略来看,是否是一个职业”〔10〕的时候,斯蒂福斯指出,合法性问题其实仍然停留在那里,即:“专业知识能够为公共行政的合法性提供充分的辩护吗?”
基于女性主义的立场,斯蒂福斯对这一问题予以了否定的回答。她认为,专业知识的辩护至少会在四个方面受到女性主义者们的质疑(也就是斯蒂福斯所说的“性别困境”):“对科学客观性的宣称,对自主权的追求,它所寻求的权威本质上是等级制的,以及兄弟关系这种潜在的规范”。〔11〕斯蒂福斯是这样展开其论证的:(1)专业知识强调的就是一种客观的、无偏见的知识,在西方思想史上,这种知识通常与男性特质(如:理性、客观、冷静)关联在一起,试图通过抹去研究者所有的个人痕迹,以期获得一种硬数据(hard data)的特征,从而将那些基于女性特质的观察方式(如:注重个人经验、观察、情感交流等)获得的“知识”,放逐到某种极为次要的位置;(2)这种专业主义的思维方式,引起了公共行政人员对职业自主权的强调。根据我们所熟悉的那一套公共行政理论,公共行政人员通常被视为人民或者公共利益的代理人,因其自身所具备的专业素养或者基于公共行政有效性的考虑,需要为他们保留出足够的自由裁量空间。斯蒂福斯认为,问题并不在于这种“自主权”的范围及其现实意义,而在于隐藏在这种“代理人”意识的背后,实则暗含着这样的努力:一方面,行政人员需要“找到一种包括回应性、服从公共意志、遵从政府其他部门的法律命令”,〔12〕因为“他们也是不同主人(机构长官、立法机构、法院、广大人民)的被注视的客体”〔13〕;另一方面,他们很想摆脱这种服从的地位,因为服从是和女性特质密切相关的。通过其所拥有的专业知识以获得一种“代理人”的地位,公共行政人员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男性的“尊严”,即取得了符合其认同的、男性特质的“自主权”,而代价则很可能是将公众处理为政府服务的被动且消极的接受者;(3)对职业自主权的强调,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关于权威的宣称,在此基础上,公共行政领域很容易建构出一种满足男性权力意志的等级链条; (4)最后,我们将会看到,公共行政领域已经形成了一种男性特质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潜在规范。斯蒂福斯借用了“兄弟关系”(brotherhood)来描述这样的规范。所谓“兄弟关系”,就是“职业成员采用共享的规范和共同的看世界的方式”。〔14〕显然,这种“兄弟关系”带有鲜明的排外色彩,而且充满着男性的特质,它意味着全心全意地投入事业。换言之,这种意识形态将“工作”抬高到更尊崇、更光荣的地位,从而将承担了更多家庭负担的女性,或者,提供关怀、照料他人的公共事业(通常这是由女性承担的)边缘化,使得女性的职业前景日趋暗淡。
通过对专业知识展开的深入剖析,斯蒂福斯揭示了隐藏在这一辩护理由背后的男性意志。在斯蒂福斯看来,专业知识的辩护绝不是如其所宣称的那般“价值中立”,它在暗中支持着一种男性特质的价值观,将女性放逐到一种极其不利的地位。通过对为公共行政合法性辩护的其他主题(如:领导才能、个人美德等)的解构,斯蒂福斯再一次发现了这种男性中心主义的色彩。在此基础上,斯蒂福斯指出,公共行政领域从其深层根源即遭遇到某种深刻的“性别困境”,这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公共行政的实践(如:刻板地遵循规则、忽视与公民之间的真正对话),并且困扰着我们关于公共行政之本质的认知。
那么,公共行政为什么会一再地遭遇所谓的“性别困境”呢?根据斯蒂福斯的解释,公共行政领域长期存在的性别歧视,例如,女性公务员的比例较少且女性通常从事的只是一些不太受人重视的工作,这固然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还不是问题的关键。在她看来,真正的困难在于我们早已经习以为常的二元化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通常体现在“包括理性与情感、果敢与被动、强壮与柔弱或公共与私人等一系列二元区分”〔15〕。通过这种二元区分,女性所从事的活动(如:照料他人、家务劳动)被贬压到次要的位置,而她们考察问题的视角、价值观念以及思考方式等,同样被放逐到私人领域。诚如斯蒂福斯对美国“进步时代”(the progressive era)的历史考察所发现的,女性曾经在公共行政的舞台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是她们提供的社区服务(如:“市政家务管理”、初步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为“进步时代”的政府改革奠定了基础,然而,女性的这些努力很快就被人们,尤其是公共行政研究的奠基者们所淡忘,甚至,被融入了由男性主导的“程序主义”之中〔16〕。这就使得公共行政领域逐渐演变为男性主导的舞台。诚然,个别的女性也曾经在这一领域取得过一定的成就,但她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是与其男性同事完全不同的,“如果没有不断努力去在工作上管理她们的女性特质(例如,处理如何显得有权威又不男性化的这种问题),没有不断奋斗去平衡工作和家庭责任,她们实际上从来就没有做到过”。〔17〕从这个角度来说,公共行政不断地遭遇“性别困境”的根源,就在于其对女性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拒斥。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仍在于寻找到——借用斯蒂福斯的话来说——一种能够调和“社区女人”(settlement women)和“机关男人”(bureau men)的方式,或者,至少也要为当前的公共行政领域引入“社区女人”的观念。〔18〕
二、关怀伦理:作为一种伦理形态的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对公共行政领域的批判,要求引入一种基于女性视角的价值观念或者思维方式。虽然学界目前尚未就一种清晰、明确的所谓女性的价值观念,达成一致的意见,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者倾向于将“关怀”(caring)视为其学说的核心①当然,由于女性主义本身的多元性,关于这一点,也有着其他不同的解答,参见A.M.Jaggar.Feminist Ethics:Some Issues for the Nineties.Journal of Social Philosophy.1989(20):91-107.。近30年来,大量的著作论述了“关怀”作为人类道德生活的一种取向以及关怀理论对现代伦理学的贡献,使得女性主义者大力倡导的“关怀伦理”(care ethics)①我们没有采用“关怀伦理学”的通用译法,根据我们的理解,“关怀伦理”不同于抽象的道德原则,它更关注的是道德实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关怀伦理”缺乏严肃、认真的学理思考。得到了充分地发展。本文认为,通过“关怀”这一概念,我们既可以把握到女性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而以此为根基的“关怀伦理”——作为一种重要的实践伦理——又可以为我们的行动(如:寻求公共行政领域的合理改善)提供指引。
“关怀伦理”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仍处于一种不断充实、发展的过程当中。②有关“关怀伦理”的发展历史,参阅〔美〕弗吉尼亚·赫尔德:《关怀伦理学》,苑莉均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8—42页。显而易见,“关怀伦理”的核心正在于如何理解“关怀”这个概念,女性主义者们也一直都在尝试着对“关怀”进行描绘。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关怀”通常被理解为一种动机、态度或者美德。此外,“关怀”还特别地指向一种付诸实践的能力,即:它不仅仅意味着一种关怀他人的意愿,更意味着关怀者有能力对他人予以关怀,也就是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被关怀者的现实需求。③关于“关怀”的内涵梳理,参阅〔美〕弗吉尼亚·赫尔德:《关怀伦理学》,苑莉均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43—67页。“关怀”源于对人之关系本质的一种深切体认,即我们每一个人始终处在和他人休戚与共的关系之中,如内尔·诺丁斯所指出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所强调的那种理性的、自主的行动者,或者一个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独立的、孤伶伶的个体,人是一种“关系性的自我”(relational self),人必然处在和他人的关系之中,“自我的确是一种关系,它是动态的,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它汇聚着影响和意义”。〔19〕
根据诺丁斯的解释,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母亲(女性)受孕、分娩的过程当中,就已经获得了一种天然的开端,“关系性自我的发展始于子宫”,〔20〕而且,“关怀”情感最初即孕育于孩子从其家人,尤其是他们的父母那里得到的细心呵护、精心照料。从这个角度来说,“关怀”首先自然而然地产生于私人领域(即家庭),这是一种“无需诉诸伦理努力”“或多或少地由深情或内心愿望自发产生的那种关怀”;〔21〕然后,随着孩子们自身的成长及其交往范围的逐渐扩大,在那些更为一般意义的人际交往过程中,“关怀”得以拓展,从而演变为一种更加普遍的“伦理关怀”。就其根本而言,“关怀”最终意味着一种对于人之关系本质的体认,由此而培养出某种真诚地在意他人之幸福的道德素养。因此,“关怀”合乎情理地“始于家庭”,如诺丁斯进一步指出的,“始于家庭,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限于家庭”,〔22〕事实上,“关怀”要求我们始终保持对他人的合理关注,它同样引导着我们对有关公共领域的一些问题(如:正义原则、制定社会政策)的思考。〔23〕
以对“关怀”的这一理解为基础,我们就可以更好地识别出“关怀伦理”的主要特征。关怀伦理并不像主流的道德伦理学说那样,追求一种普遍而又抽象的伦理原则,也就是以一种所谓“公正”的、不偏不倚的方式来对待人,给予每个人以同等、同质的考虑。与这种道德伦理学说相比,关怀伦理更为尊重的是人类真实的道德情感。由于“关怀”往往是从最为亲密的人际交往活动开始的,关怀伦理对那些和我们有着特殊关系的个人及其要求予以充分、合理的尊重。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这并不意味着关怀伦理只是一种蜷缩在狭小的范围(如:家庭生活、朋友圈子)之内的伦理规范,准确地理解关怀伦理,关键在于对人之关系本质的把握。关怀伦理从根本上反对的就是主流道德伦理学说的做法,即将人视为一种理性的、自足的、独立的个体,并在此基础之上,通过抽象的推理、演绎方式,发展出与之相应的行为准则。与此相反,关怀伦理的倡导者们深切地认识到,“每一个人从儿时开始就依赖其他人提供关怀;我们在一生中都以很根本的方式和其他人相互依赖。我们仿佛独立地思考和行动这一点依赖着一个社会的关系网络,而我们的关系又是构成我们身份的一部分”,〔24〕换言之,“关系”是我们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甚至,人之“独立、自主”同样体现为“一种重建和培育新关系的能力”。〔25〕
由于深切地体会到人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关系性的自我”,关怀伦理实际上并不主张我们每个人都蜷缩在“我”这个狭小的天地里面,它期待着人们能够走入更为广阔的公共世界,走向与他人亲切、友好的交往:一方面,关怀伦理要求我们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行动——倾听他人,理解他人,和他人一起解决其所面临的各种困惑、问题;另一方面,关怀伦理还意识到,我们直接关怀他人总会遇到许多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如:我们显然难以直接关怀每一位贫困山区的失学儿童),在这种情况下,“关怀”实际上仍未退位,它至少引导着我们思考更为普遍的正义原则、制定行之有效的公共政策。因此,关怀伦理体现的就是真诚地在意他人之幸福,它并不特别关注构建一个貌似“公正”的制度、规则体系,然而,它始终保持对于人之生活本身的敏感,在这里,活生生的人及其所遭遇的苦难、挣扎、迷惑始终牵动着我们。
与关怀伦理的这一理解相比,目前,仍居于主流地位的道德学说——无论是坚持义务论,还是抱有功利主义见解的理论——都过分地依赖于“普遍的准则”或者“简单、抽象的原则”,从而将现实的人打发得无影无踪。〔26〕尤其是在公共行政领域,官僚机器的运转使得我们每一个人不断地匿名化,以至沦为拉尔夫·哈默(R.P.Hummel)所说的“案子”(case)。根据哈默本人的解释,这里所谓的“案子”,就是现代官僚机构发明的一种办事方式:他们首先确立一系列的条件、标准(如性别、年龄、家庭情况、收入状况之类),只有在符合“立案”要求的情况下,个人的问题才会引起官僚组织的注意;然后,以一种“办案”的方式,而不是以一种人与人打交道的应有方式得到处理。〔27〕
从关怀伦理的立场来看,现代官僚机构的这种办事方式无疑是过于冷漠、敷衍了事的。关怀伦理的倡导者们坚持,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以活生生的人的方式得到倾听、理解和尊重,这也是我们帮助他人真正地解决其问题的途径。由此,关怀伦理向我们提出了一种重塑公共行政的期待。
三、走向关怀:“关怀伦理”与公共行政的重塑
女性主义的批判指向公共行政领域潜藏的、由男性主导的话语体系,为我们揭示出公共行政所遭遇的“性别困境”,这种“性别困境”集中地体现在现代公共行政追求的技术理性、客观性、中立性等一系列努力,其实质则是对人之现实生活缺乏真切的关怀。通过引入基于女性视角的关怀伦理,我们有可能走出这种“性别困境”,从而在公共行政领域做得比目前更好:
(一)公共行政价值理念的重塑
戴维·罗森布鲁姆(D.H.Rosenbloom)等人认为,当前的公共行政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诠释途径(approach),亦即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而这三种途径分别基于各自不同的价值理念。其中,管理途径强调的是效率、效能和经济,而在这一途径的新版本(即“新公共管理”,NPM)中,“成本—效益”、回应顾客需求得到了进一步的讨论;政治途径则对行政管理的公共性有着更为清楚的认知,在这一途径之中,代表性、回应性和责任性等理念,被放置到了更为核心的位置;最后,法律途径则突出了程序正义、权利保护以及公正等要素。〔28〕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管理主义途径仍然是当前公共行政研究中的主流范式,对效率、经济和成本—效益的追求,仍是这一领域的主导理念。〔29〕
从女性主义关怀伦理的视角来看,我们显然有必要转变当前公共行政领域的价值理念,要以“关怀”为核心,重塑公共行政的价值理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效率、经济、公平等理念的彻底否弃。由于“关怀”包含对被关怀者的现实境况加以改善的能力,“关怀”实际上不可能是不顾及效率、经济、公平的,但“关怀”从根本上来说的确不同于效率、经济以及公平。简单地说,“关怀”要求公共行政应当更加贴近、服务于人之现实生活,“关怀”意味着我们不是在公共事业中将人匿名化,以至仅仅关注那些空洞、抽象的公共服务的数字,它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加注重人之实际生活的改善——通过公共行政这一方式。在这里,“关怀”是对效率、经济、公平之类的一个有益补充,并且,它还影响着我们对于公共事务之本质、公共行政之方式的理解。
(二)公共事务范围的调整
从“进步时代”的理论家们开始,就已经在尝试着划清公共行政领域的边界。伍德罗·威尔逊告诉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政府能够适当而且成功地完成哪些任务”。〔30〕在今天的公共行政研究中,随便哪一本公共行政学的教材都能够或多或少地为我们提供有关这一问题的解答,例如,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家庭之间的职责区分。
关怀伦理同样主张有必要划清这些不同领域间的界限,不过,它也对主导当前有关这些问题探讨的自由主义,尤其是其经济学说提出了批评、质疑。在这种主流话语体系中,“‘市场’往往被视为模式,不仅经济生活,而且几乎所有人类活动都要依照该模式来运行”。〔31〕以公共领域而言,无论是公共物品的供给,还是公共服务的提供,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私有化”“市场化”了,如果这里还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私有化”“市场化”的程度仍然不够的问题。的确,政府需要更快捷、更高效地运转,但关怀伦理坚持政府同样需要对其活动领域和范围进行审慎、严肃地思考。
根据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我们每个人都被假设成互相独立、只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子,公共行政的意义即在于维持一种“公正”的、不偏不倚的规则体系,它不应该涉入我们的私人生活。关怀伦理则根据女性特殊的生活体验(生育、抚养子女),从“关系”的立场对这种作为独立个体的“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由于认识到我们始终处在某种互相依赖、互相关联的关系之中,关怀伦理的倡导者们主张我们必须为维持、改善彼此之间的关系做出积极的努力。基于关怀主义的这一立场,政府也要对其公共事务范围进行调整,亦即纳入更多、更富有“关怀”精神的活动,如:学校教育、社区工作、对老年人的精神与健康照料等等,并且将它们提升到更为重要的位置。换言之,政府需要尽其所能地改善我们的现实生活,支持充满“关怀”精神的公共服务项目,而不是任由它们在市场机制的无情检验之中载浮载沉、自生自灭。
(三)公共治理主体的培养
在治理主体方面,关怀伦理同样能够为我们带来有益的启示。虽然公共行政领域并不缺乏围绕着公共治理者的探讨,如:安东尼·唐斯(A.Downs)讨论了官僚之动机及其行为类型,〔32〕科恩(S.Cohen)等人则关注公共管理者如何取得绩效〔33〕。不过,他们更为关心的乃是对于官僚自身的控制或者赢得绩效,而不是如何培养出“好”(伦理意义上的)的公共治理者,“由于现代公共行政通常更加强调制度创新、组织再造等内容,对行政人员的公共精神的培养,往往缺乏足够的关注”。〔34〕关于公共治理者的德性培养,关怀伦理同样能够为我们提供帮助。
关怀伦理主张,公共治理者(当然,这里主要指的是一线的行政人员)及其服务对象应处于一种关怀关系之中,而且在这一关系里面,公共治理者更多扮演的是“关怀者”的角色。内尔·诺丁斯分析指出,“关怀”并不是要将关怀者抬高到主导者、施予者的地位,被关怀者在这一关系中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关怀”从来就不是一种简单、浮浅的“父爱主义”,而是关怀双方通过交流、协商,共同寻求一种解决问题的途径。事实上,正是被关怀者首先发出了渴望关怀的邀请,允许关怀者进入他们的“世界”,从而为营造良好的关怀关系提供了可能,“关怀”建基于对他们真正的理解、尊重。〔35〕因此,培育一种“关怀”精神,意味着公共治理者不仅需要具备关怀他人的能力(如: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资源分配权力),更重要的是,公共治理者还需要致力于培养“关怀”的德性,即“照顾、同情、关心、爱心、体贴和慷慨的美德”,〔36〕这意味着公共治理者不再是冷冰冰的“官僚主义者”“程序主义者”,而是坦率、真诚地走入他人的世界,倾听、理解其所服务的对象,并且和他们一起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在这一意义上,“关怀”可以被视为一种德性。关怀伦理认为,公共治理者需要加以培养的就是这种关怀他人的德性。
(四)公共治理方式的转变
最后,关怀伦理也要求当前的公共治理方式做出相应的转变。关怀伦理拒斥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这种模式往往让我们想起数不清的规则和章程、令人生畏的科层制链条、漠不关心的办事态度……而在处理实际问题的时候,拉尔夫·哈默所说的“案子”(case),则生动、形象地反映出了官僚机构的办事风格。
与之相比,关怀伦理吁求一种更为人性化的治理方式,即公共治理需要关心人们的现实生活,帮助人们解决其所面临的实际困难。为了有效地做到这一点,我们不仅需要重视在官僚机构之外培育那些更加贴近人之现实生活的公共治理主体,如:社区、公民团体和其他类型的组织,激发它们在公共治理过程中的活力,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人们的切实需求;同时,我们也需要转变传统的行政模式,尝试着寻找一些新的治理途径,例如:鼓励公众参与、鼓励公众和行政人员之间的相互了解、对话。总体而言,我们需要寻找到的这种新的治理方式,将不再是如传统官僚制模式那样依赖于等级链条的传递,而是应当致力于缩短政府和公众之间的距离,使得他们能够彼此沟通、相互了解,从而真正地处于一种同休戚、共呼吸的关怀关系之中。

表1 关怀伦理与公共行政领域的改进
通过表1,我们简单地勾勒出了关怀伦理有可能为公共行政领域带来的改进。我们在这里的分析仍只是理论层面的,但我们相信,“关怀”理念与公共行政实践的结合,能够创造出一些更为丰富、生动的内容,关键在于,我们需要扭转当前公共行政对“程序主义”、技术理性的迷恋,从而为这一领域真正地引入这种女性主义的视角,即“关怀”的视角。
四、总结
基于“性别困境”的视角,女性主义对公共行政领域的深入批判,从根本上挑战了这一领域长期占据着主流位置的话语体系,解构了其中的权力意志,从而呼吁一种更加贴近现实、融入生活气息的公共行政。著名的公共行政学大师德怀特·沃尔多(Dwight Waldo)曾经说过:“我们所有人的福利、幸福以及实实在在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影响并维持着我们日常生活的行政机构的表现。现代社会中,公共行政活动的影响既深且广,从食宿问题直到我们的思维方式”。〔37〕由此可见,公共行政的根本意义正体现在其对于人之现实生活的改善。
本文通过引入一种“关怀伦理”的视角,从公共行政的价值理念、公共事务的范围、治理主体、治理方式等多个层次,思考了重塑当前公共行政的可能。根据以上理解,关怀伦理的突出意义正在于如下的期待:使公共行政能够真正地服务、融入我们的现实生活。
〔1〕何艳玲,张雪帆.公共行政学说史的认识论传统及其辩论〔J〕.中国行政管理,2014,(6).
〔2〕Camilla Stivers.Settlement Women and Bureau Men:Constructing a Usable Past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95(55):522-529;Camilla Stivers.Bureau Men,Settlement Women:Construct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the Progressive Era.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00.
〔3〕〔5〕〔7〕〔8〕〔9〕〔10〕〔11〕〔12〕〔13〕〔14〕〔17〕〔美〕卡米拉·斯蒂福斯.公共行政中的性别形象〔M〕.熊美娟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134,135,1,1-2,2,37,39,49,50,55,58.
〔4〕〔15〕〔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M〕.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231,231.
〔6〕王宇颖.公共管理研究的性别视角——美国女性主义公共行政理论评述〔J〕.中国行政管理,2011,(3).
〔16〕〔18〕C.Stivers.Bureamu Men,Settlement Women:Construct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the Progressive Era.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00.
〔19〕〔20〕〔21〕〔22〕〔美〕内尔·诺丁斯.始于家庭:关怀与社会政策〔M〕.侯晶晶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97,116,26,2.
〔23〕〔24〕〔25〕〔26〕〔31〕〔36〕〔美〕赫尔德.关怀伦理学〔M〕.苑莉均译.商务印书馆,2014.93-121,18,19,93-94,171,52.
〔27〕R.P.Hummel.The Bureaucratic Experience:The Post-Modern Challenge.Armonk,NY:M.E.Sharpe,2008,pp.25-29.
〔28〕〔美〕戴维·罗森布鲁姆,罗伯特·克拉夫丘克.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M〕.张成福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6-41.
〔29〕马骏,刘亚平.中国公共行政学的“身份危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4).
〔30〕J.M.Shafritz&A.C.Hyde&S.J.Parkes(ed).Classic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4.
〔32〕Cohen,S.&Eimicke,W.The New Effective Public Manager:Achieving Success in a Changing Government.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1995.
〔33〕〔美〕安东尼·唐斯.官僚制内幕〔M〕.郭小聪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86-119.
〔34〕郭小聪,琚挺挺.论儒家传统文化的“治道”思想及其现代意义〔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
〔35〕Nel Noddings.Caring:A Feminine Approach to Ethics and Moral Educa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37〕D.Waldo.The Stud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New York:Doubleday,1955,p.70.
(责任编辑:邝彩云)
D035
A
1004-0633(2015)06-107-7
2015-09-23
琚挺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行政伦理、儒家“治道”思想。广东广州510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