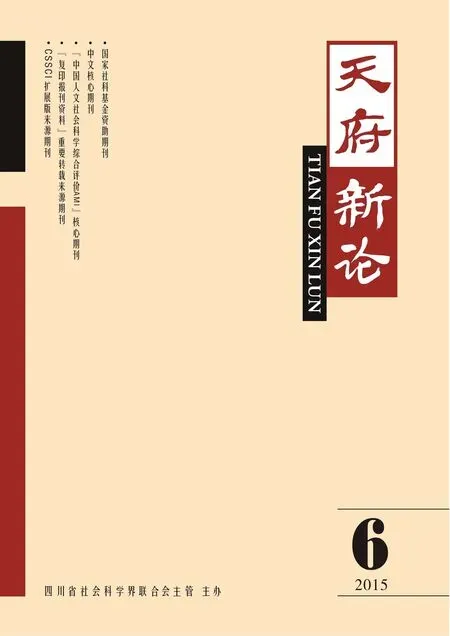以胜利者的名义:新的抗战记忆与抗战影视剧的书写策略
张慧瑜
以胜利者的名义:新的抗战记忆与抗战影视剧的书写策略
张慧瑜
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中的重大事件,抗日战争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国家形态和中华民族的品格。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抗日战争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战争;那么,20世纪80年代抗日战争则变成“落后就要挨打”的悲情动员;而新世纪以来,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大背景下,抗日战争又被书写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组成部分。与此相应,20世纪80年代以来影视剧中的抗战叙述也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
抗日战争;抗战记忆;影视剧;创作类型
今年,中国举行了盛大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抗日战争再次成为热门话题。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中的重大事件,抗日战争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国家形态和中华民族的品格。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抗日战争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战争,那么,20世纪80年代抗日战争则变成“落后就要挨打”的悲情动员,而新世纪以来,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大背景下,抗日战争又被书写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组成部分。近些年,抗战影视剧的流行也是大众文化领域中引人注目的现象,既有电视剧《亮剑》、《我的团长我的团》等经典之作,也有《抗日奇侠》、《一起打鬼子》等抗战雷剧。本文主要分析四个问题,一是为何要重新纪念抗日战争,二是抗日战争的性质和两种史观的转变,三是近代以来中国对日本的双重态度,四是近些年抗战影视剧的创作类型。
一、以“胜利者”的名义
以前,中国只有国庆大阅兵,今年是首次以纪念抗战胜利的名义举办阅兵,而且,这还是一场带有国际色彩的大阅兵,邀请了一些国外政要和外国仪仗队参加。这种“胜利日”的纪念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很新鲜,也是比较陌生的历史经验,尽管抗日战争已经过去了70年,但中国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纪念抗战“胜利”。与血泪斑驳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悲情叙述不同,中国是以抗战胜利者、二战胜利国的身份来举办这次盛会,抗日战争也被重新指认为一次伟大的胜利,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可以说,这次找回历史的“胜利”不像是历史的缅怀,更像是一次历史的重新追认。
9月3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是1946年中国国民党中常会决议确定的,新中国成立之后,1949年12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把“八一五”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1951年8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通告,将抗战胜利纪念日改定为9月3日,直到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进行修订,延续了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的规定。①参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百度百科。在当代,中国与抗战相关的纪念日是“九一八”、“七七事变”和“八一五”,前两个是日本侵略东北和发动全面战争的日期,被作为中国遭遇耻辱、动员全民族抗战的特殊象征,“八一五”则是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八年全面抗战结束的日期,9月3日没有特别作为重大纪念日。其主要原因是在革命历史叙述中,抗日战争只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者的一个历史阶段,抗战之后的解放战争才是最终的胜利,也是新中国的胜利。再加上9月3日作为胜利纪念日带有国民政府的色彩,实际上也是当时作为中国政府合法代表的国民政府接受了日本政府的投降书。
重新把9月3日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是2014年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以国家立法的形式通过的决议,今年是第二次纪念抗战胜利日。在这次人大会议中,还确定把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从这样两个纪念日可以看出一种新的对于国家和人民的理解。这两次纪念日的主体都是国家,一个是国家的胜利,一个是国家的耻辱,此处的国家是一种相对抽象的“中国”,一个模糊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界限的国家。在这种国家的论述中,人民是被屠杀、被砍头、被杀害的死难者,而不再是因反抗而壮烈牺牲的人民,也就是说,只要在战争、灾难中无辜受难的中国人,国家都有责任纪念。这种被动的受害者同样是一个抽象的人民,这也是南京大屠杀故事在抗战图景中被反复讲述的原因。这样两个国家纪念日成为抗战故事中最重要的节点,一个是受害者的耻辱,一个是胜利者的骄傲,至于如何从受害者变成胜利者,却有些语焉不详。从近些年每次遇到地震等自然灾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时设立国家哀悼日,也能看出这种新的国家与人民的关系。
这种模糊中华民国与新中国界限的叙述所完成的是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一体化的任务,从两个影视作品中也能看到这种趋势。一是2009年的《建国大业》,这部电影论述1949年的合法性是放在1945年抗战胜利组建联合政府的背景中展开的,仿佛说内战之后1949年的政治协商会议是对1945年抗战胜利的接续,也就是说,1949年的新中国建立在1945年抗战建国的基础之上。二是2011年的《建党大业》讲述共产党诞生的故事。在原来的革命史叙述中,共产党诞生是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讲起,从一战结束、苏联建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始。而在《建党大业》中,历史往前延伸了,其把建党放在1911年辛亥革命的背景下展开,也就是说,1921年共产党成立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是对1911年中华民国的接续,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接续在一起,变成了同一个现代中国。所以说,南京大屠杀是国民政府的耻辱,也是当下中国的耻辱;抗战胜利是国民政府的胜利,也是当下中国可以分享的胜利。这种从历史中找回了曾经拥有或不曾拥有的“胜利”,是一种新的历史记忆的重塑。
二、抗日战争的性质与两种史观的转变
现在大规模纪念抗战,着眼点往往放在战争与和平的永恒主题上,而很少讨论抗日战争的性质问题,这个问题恰好是需要特别强调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抗日战争只被作为民族国家之间的常规战争,反而弱化抗战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面向。
先从三个概念说起,一是“抗战”,二是“反法西斯战争”,三是“二战”。这三个概念有重叠的地方,但强调的侧重点不同。“抗战”主要是指中国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这一概念一般是中国使用。“反法西斯战争”是冷战年代社会主义国家指称“二战”的说法,也是对二战性质的定位。上世纪30年代德国、日本走向法西斯化是其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根本动因,反对德国、日本的侵略就是反对法西斯主义,而反法西斯主义战争包括着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含义,因此,其带有左翼或共产主义的色彩。“二战”是英美国家经常使用的概念,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放置在“一战”的序列中,这种说法其实模糊了“二战”的性质。过去在“二战”的叙述中是没有中日战争的位置的,因为只有发生在欧洲的战争才具有“世界性”,中日战争只是附属的、区域性的战争。我们现在更多地使用“二战”的说法,实际上采用的是英美等西方国家对这场战争的定位,抗日战争也被作为“二战”的“东方主战场”,这其实消弱了抗战反法西斯主义的意义。
这次抗战胜利纪念日的全称依然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指出了抗日战争的双重性质,一是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者的国家战争,二是抗战也是落后国家的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法西斯的国际战争。因此,抗战不仅是中日之间的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之所以强调抗战反法西斯的一面,与探讨抗日战争为什么会发生有关,也就是追问日本为什么要侵略中国?难道中国落后就应该被“侵略”吗?这和日本在上世纪30年代国际经济危机和大萧条的背景下走向法西斯化、军国主义化有关。近代以来,日本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主动进行明治维新改革,走向“脱亚入欧”的道路。只是,日本在追求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对外侵略战争,如1894年的甲午战争、1905年的日俄战争、1931年的侵华战争、1942年的太平洋战争等,这和西方原发资本主义国家先工业化后进行海外殖民的道路是一致的。通过对外战争,它一方面掠夺殖民地的资源,另一方面开辟海外市场,这些都与服务国家的工业化有密切关系。抗日战争的背景还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有关,一些国家通过战争转移、转嫁国内社会矛盾。可以说,德国、日本走向法西斯化,这本身是资本主义无法克服自身危机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反法西斯主义不只是抵抗外来侵略,也是反思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发展道路。与“一战”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争霸战不同,“二战”的反法西斯主义具有“世界性”,这不仅体现在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大联合”,而且,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主义精神也参与到反法西斯主义的实践中。就像白求恩的故事是典型的国际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的结合,还有西班牙内战中来自各个国家的“国际纵队”。二战结束之后在冷战的背景下,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用“二战”来掩饰法西斯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必然渊源,而社会主义阵营则用反法西斯主义来批判资本主义必然法西斯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抗战论述开始从反法西斯主义战争转变为一种中日之间的国家战争,这是在“告别革命”、去冷战的背景下从革命史观向现代化史观转变的结果。与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斗争、人民作为历史的主体等革命史观不同,现代化史观以民族国家为叙述主体、以现代化的发展主义为任务,于是,包括抗日战争在内的中国近现代历史重新从革命史改写为现代化史观。在毛泽东时代,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革命史的组成部分,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重要环节,抗战之后的解放战争则是反帝、反封建的继续,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抗战史镶嵌在百余年来中国反抗外来侵略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大叙述之中。新时期以来,在现代化史观中,抗日战争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抗日战争被作为中国贫穷、落后而遭受外敌侵略的屈辱历史,尤其是南京大屠杀的故事,成为苦难深重的中国人遭遇凌辱的象征。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者的革命史、抵抗史变成了中国遭受屈辱和创伤的受害史、悲情史,也就是用“落后就要挨打”来作为新一轮现代化的悲情动员。与此相关的是,关于中国的自我想象重新变成了前现代的、没有经历现代的乡土中国。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爱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叠加”成为新的主流意识形态,抗日战争也成为传达这种主旋律的影视剧题材。新世纪以来,伴随中国经济崛起,主流意识形态进一步升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20世纪80年代的民族悲情史又被组织到民族复兴的论述中,抗日战争开始从民族屈辱和悲情转变为一种抗战胜利的故事。抗战胜利被指认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起点,这恐怕与当下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大国崛起的心态有关。
三、抗战胜利的暧昧性与被遮蔽的历史叙述
抗战“胜利”本身在中国现代史中是比较暧昧的,这种暧昧性与二战后的冷战历史格局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次深刻影响当下世界秩序的战争,这场战争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让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站在了一起,结成了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同盟国”。二战一结束,冷战铁幕随之降临,世界分隔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像中国的内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都是发生在两大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的战争。
内战爆发以及国民党的败北,使得国民政府作为抗战胜利者的身份非常可疑。一方面,抗战的最终胜利并非完全来自于国军将士的勇敢作战,反而有赖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包括美国、苏联等同盟国的大力支持,尤其是1942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把美国拖入太平洋战争以及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按照日本的说法,日本被美国打败,而不是当时积弱积贫的中国;另一方面,抗战之后的国共内战,国民政府很快一溃千里,从抗战胜利者变成了偏居一隅的流亡政府。因此,对于抗战的胜利,国民政府更像是胜利的失败者。另外,冷战之后,美国占领日本,至今依然在日本驻军。由于冷战的需要,日本作为法西斯国家的战争责任被英美世界极大地赦免,这也造成德国法西斯是人类的公敌,而日本则不是“世界”的敌人,反而日本国民的普遍感受是从侵略者变成了二战的受害者。①在这个意义上,广岛、长崎作为对日本走向军国主义道路的惩罚,给日本人民也带来的惨痛灾难,只是广岛、长崎作为一种“亚洲的伤口”又纠缠于亚洲/西方的话语之中。日本的侵略战争是在抵抗西方列强的旗帜下展开的,而日本作为失败者/原子弹受害者的身份又被作为亚洲的失败,“亚洲”成了日本成功与失败的双重“借口”。在“亚洲”的遮羞布之下,那个已然晋身为西方列强之一的日本以及成功走向帝国主义侵略之路的日本就消失不见了。
近代以来,日本确实是对中国产生过特殊影响的国家。我们评价日本经常会出现两种情绪,一种就是仇恨、憎恶,把日本叫做“小日本”、“日本鬼子”,另一种情绪则是羡慕和崇拜,认为日本更文明、更现代。这样既爱又恨的情绪从甲午战争以后就出现了。甲午战争的失败让晚清知识分子倍感耻辱的同时,也发现东洋的富国强兵之路是值得贫穷落后的中国学习的榜样,因此,留学日本成为晚清民初很多知识分子的选择,如鲁迅、蒋介石等。到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也被认为是“亚洲的胜利”,②如1924年,孙中山逝世前夕在日本神户发表了名为《大亚洲主义》的演讲,号召其他弱小的亚洲国家向日本学习,因为日本打败了传统的西方国家俄国,暂且不讨论俄国作为西方内部的他者,这种亚洲主义的问题在于,日本的胜利究竟是亚洲的胜利,还是西方的胜利呢?因为正是凭着日俄战争日本加入了西方的列强俱乐部。是亚洲国家“脱亚入欧”最为成功的典范。日本确实也是少有的落后国家能够避免被西方列强殖民的案例,其所选择的道路是把自己也变成西方列强,加入“八国联军”俱乐部。直到二战结束,日本被美军打败、占领,这种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现代化之路才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最终走向了法西斯主义。与之相反,中国经历近代受侵略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变成主权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被认为是落后国家摆脱殖民、获得民族独立的成功范例,中国也改变了对日本既爱又恨的情绪,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视野中体认到日本人民也是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并把二战后日本国内的反美斗争作为受压迫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组成部分。
冷战时期,日本在美国的大力扶持下迅速实现经济起飞,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员。这与日本处于冷战的前沿阵地的位置有关,也是续日本之后亚洲四小龙经济崛起的地缘政治原因。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开始。1978年底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访问日本,他乘坐日本高速列车新干线的新闻报道,让中国人看到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的日本,日本的形象从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再度转变为现代化的优等生。这种“震惊”体验又一次改变中国人眼中的两国近代史,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文革结束的历史被认为是现代化的失败,而日本从明治维新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才是现代化的“正途”。与此同时,在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现代化论述中,日本继续扮演着给中国带来巨大创伤的外敌形象,这种对日本既爱又恨的情绪再次“复活”。③这一点在《南京!南京!》(包括《拉贝日记》)中呈现得更为清楚,正如导演在回应为什么要选取日本人的角色时有意无意地说:“70年前日本真的很强盛,一个步兵单兵一年可以有1800发子弹的实弹射击训练,我们能有10发就不错了。1943年以前我们拼刺刀拼不过日本人,必须是二对一。日本人在日记本上对自己参加的每一场战役都画有战略图,我们的军队文盲占百分之九十九”。陆川对于年轻日本演员的敬业精神也赞许有加,正如他们的前辈配备着优良的装备和素质,这些年轻的日本演员也是如此充满良知地不敢演强奸戏,直到导演说如果不演这些女大学生就会一直裸下去,这些日本演员才勉强同意,演完后马上就把衣服给女演员盖上,如同影片中那些充满内疚和悔恨的日本士兵,及时枪毙了遭到奸污的中国女人,因为“这样活着还不如死掉”。《陆川全面回应<南京!南京!>观众质疑》,载南方日报,2009年04月24日。这份爱恨交织的情感是一种典型的殖民地、落后国家对西方现代性的双重经验,既渴望现代化(变成西方),又深受现代化所害(被西方侵略)。在这种现代化的视野中,只有进步与落后、变成西方或被西方所侵略的两种选择,那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导致的法西斯化以及落后国家寻求民族独立与现代化并重的革命之路都不可见了。④当然,能否在现代性之外对现代性进行批判依然是一个问题,从某种程度来说,现代性的全球扩散恰好是以对现代性的抵抗的方式完成的。18世纪北美反抗英国殖民地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20世纪俄国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下反抗资本主义全球秩序,显然,马克思对于现代性的批判也是在现代性内部展开的,而日本所谓的“脱亚入欧”也是以打败俄国这样的西方国家才得以晋级为西方列强之一,并进一步打着反抗西方的旗号,吞并、殖民东亚各国,对现代性的反抗和质疑却使得现代性的逻辑播散到更多的区域。
这种以现代化为基调的民族国家史观也带来一些历史叙述的困境,特别体现在两个领域,一是如何讲述内战的故事,二是如何处理抗战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如果把抗日战争讲述为国共联合抗日的民族国家之战,那么,随后发生的国共内战就变得非常暧昧和难以讲述。新世纪以来最热播的革命历史剧《亮剑》主要讲述李云龙打鬼子以及与国民党将领楚云飞联合抗日的故事。《亮剑》中有一句台词是“国家利益高于意识形态,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这句台词被李云龙、楚云飞和日本特种兵将领山本一木都说过,他们都是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来打仗,也是忠实于自己国家、民族利益的职业军人,如果没有战争,他们三个彼此惺惺相惜的男人应该是好朋友。用国家主义来理解抗战,使得抗日战争的性质变得模糊了,战争没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只是两个国家为了各自的利益来打仗。这部电视剧的魅力是把李云龙这样的红色将领塑造为民族国家的英雄,从而使得以阶级革命为内核的红色经典实现华丽转身。为了避免内战中两个好兄弟李云龙与楚云飞兵戎相见,电视剧采取了内战一开始李云龙就负伤住院、谈恋爱的情节,解放后借民主党派之口质问李云龙“中国人为何要打中国人”。确实,从中华民族的角度很难处理内战作为阶级战争的事实,这导致抗战剧流行、内战剧很少的现象。如果非要讲述内战的故事,新世纪以来的影视剧发现了一种恰当的好办法,把国共内战呈现为暗战和谍战故事,像《暗算》(2006年)、《潜伏》(2009年)一样勾心斗角的办公室化的职场政治。比如《人间正道是沧桑》(2009年)中大哥国民党杨立仁、小弟共产党杨立青是亲兄弟,他们抗日战争时期联合抗日,内战开始就通过谍战来智斗。所以,国庆献礼剧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不再讲述“三大战役”的故事,只讲述北京和平解放的故事,如《战北平》(2009年)、《北平战与和》(2009年)、《北平无战事》(2014年)等。
另外一种被国族抗战史所遮蔽的历史,就是中国革命与抗日战争的内在关系。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主要讲述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游击队率领人民群众打击、骚扰小股日军的故事,如《平原游击队》(1955年)、《铁道游击队》(1956年)、《地雷战》(1962年)、《野火春风斗古城》(1963年)、《地道战》(1965年)等,那么,在恢复国共联合抗战以及国民党正面抗战的“拨乱反正”中,正规战、国军抗战的故事则成为新的主流,尤其是以《我的团长我的团》(2009年)、《中国远征军》(2011年)等为代表的赴缅抗战的国军故事,这就使得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的故事变得斑驳游离。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从工人阶级的先锋党转变为中华民族的政党的关键时期,实现了阶级论述与民族论述的辩证统一,也进一步完善和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任务。这从毛泽东抗战期间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重要文章中可以看出。另外,抗日战争对于共产党来说,一方面是反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对外战争,另一方面,也是发动、组织和动员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过程。与那些把敌后游击战表现为《抗日奇侠》(2010年)、《一起打鬼子》(2015年)等抗战雷剧不同,游击战争恰好是与人民战争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而不只是像好莱坞超级英雄那样打击僵尸化的敌人。
四、抗战影视剧的三重转型与五种创作类型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抗战叙述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第一次是把抗战故事变成悲情史、受难史,这主要体现在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故事上。第二次是把抗战叙述的民国化和国家化,体现在以革命者及其领导的革命群众为叙述主体的敌后抗战故事转变国共联合抗日的故事,或者突显国军将领在正面战场上的意义。这种抗战叙述的“民国化”也始终伴随着国家化,也就是把反日本法西斯的战争叙述为两个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抗战英雄被塑造为国家英雄、民族英雄,这种抗战影视剧服务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第三次是把国家化的抗战叙述进一步国际化和二战化,也就是把中国的抗战故事升级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变成与美国、英国“同一个战壕”的同盟国,突显抗战的国际面向,这与新世纪以来中国作为大国的自我想象以及中国的新国际视野有关。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五种抗战剧的创作类型。
第一种是南京大屠杀的故事。南京大屠杀作为历史事件在20世纪50到70年代的革命叙述中,不仅仅被作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血泪斑斑的近代史中最为惨烈的一幕,而且作为日本走向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明证,是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最为具象化的呈现,但是,在那个时代并没有出现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抗战影片。因为“南京”这一国民政府“消极抗日”而丢失的“首都”无法放置在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抗战的革命叙述里,再说,只有人民被屠杀而没有人民奋起反抗的情节,很难完成“人民作为历史主体”的论述。20世纪80年代之后,南京大屠杀才开始被不断地拍摄为电影,如《南京大屠杀》(1982年,纪录片)、《屠城血证》(1987年)、《南京大屠杀》(1995年)、《黑太阳南京大屠杀》(1995年)、《栖霞寺1937》(2005年)、《南京梦魇》(2005年,朗恩·乔瑟夫导演纪录片)、《南京浩劫》(2007年,好莱坞拍摄)、《南京!南京!》(2009年)、《拉贝日记》(2009年,中德合资拍摄)、《金陵十三钗》(2011年)等。这些讲述“南京大屠杀”故事的影片都以呈现日军的残暴和中国人的被屠杀为情节主部,这种中国人民的创伤体验没有转化为抵抗侵略者的革命动员,反而被组织到一种民族悲情中。这也成为导演陆川认为中国关于“南京大屠杀”只有控诉式的书写,没有中国人的抵抗的缘由。①对于电影《南京!南京!》的解读,可以参见笔者发表在《电影艺术》上的文章《后冷战时代的抗战书写与角川视角》,2009年第4期。
第二种是国共联合抗日的故事。新时期以来,关于抗日战争的叙述再次成为国军与共军“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叙述空间。在面对日本作为一种外在的民族敌人的意义上,国军不仅被恢复了正面抗战的“历史地位”,而且国共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也在中国人民族身份的同一的意义上获得整合,这使得抗日战争变成一种中国人抵抗外辱的国族之战。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抗战影片中,国民党、国军形象开始呈现一种正面的积极抗战的形象,比如《西安事变》(1981年)、《血战台儿庄》(1986年)、《铁血昆仑关》(1994年)、《七七事变》(1995年)等。直到《南京!南京!》(2009年)、《金陵十三钗》(2011年)等国产大片中,直接把抵抗日军的国民党士兵书写为中国军人的代表。近些年,在大众文化领域,除了发掘那些被冷战历史所遗忘的抗战老兵外,更有名的民国军人是1942年作为英美同盟军的中国远征军,这些承担国际责任的抗战老兵被命名为国家英雄。正如在一本“献给为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而战的中国军人和盟军军人”的书《国家记忆》中,作者从美国国家档案馆中找寻到当时美国随军摄影师拍摄的赴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的身影。在序言中作者深情地写道,以前抗战历史都是“认贼作父”,“直到此前多少年,做梦都想不到,有那么多父辈的影像,如此清晰,宛如眼前”〔1〕。这是一次借助美国摄影师的目光把曾经的敌人、国军重新指认为“父亲”的故事,而同名作者的另一本书直接命名为《父亲的战场: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田野调查笔记》,这种寻父之旅所实现的是把当代中国与现代中国“合并”为抽象的民族国家的过程。这种文化的民族国家化,也是当下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秩序民族国家化的曲折反映。
第三种是土匪、农民抗日的故事。随着20世纪80年代革命叙述的瓦解和现代化叙述的显影,曾经被革命动员和赋予历史主体位置的农民又变成了前现代的自我表征,这导致在抗战叙述中,曾经作为抵抗者的人民又变成了被砍头者和愚昧的庸众。如20世纪80年代的第五代电影《一个和八个》(1984年)和《红高粱》(1987年),前者讲述了一个被怀疑为叛徒的革命者在遭遇日军的过程中把一群土匪改造为抵抗的中国人的故事,被怀疑的革命者与土匪在“有良心的中国人在打鬼子”、“不打鬼子算什么中国人”的国族身份的意义上获得整合。而后者讲述了一段看不出具体时空秩序的“我爷爷”与“我奶奶”的遥远传奇。没有共产党的引领,伏击日本人成为一种在民间逻辑中的英雄复仇。也正是在这种革命者缺席的状态下,出现了一种没有经过革命动员和启蒙的农民成为抗战主体的策略,这可以从姜文的《鬼子来了》(1999年)和冯小宁的《紫日》(2001年)中看出。《鬼子来了》一开始,“我”作为游击队长半夜交给马大三两个麻袋,从而就消失不见了。对于挂甲屯的村民来说,他们不是启蒙视野下的庸众,也不是革命叙述中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主体,他们是生活在殖民地的“良民”。从这个角度来说,影片恰好处理了左翼叙述的困境,即在外在的革命者缺席的情况下,以马大三为代表的“人民”能否自发自觉地占据某种历史的主体位置。《鬼子来了》在把“日本人”还原为“鬼子”的过程中,也是马大三从前现代主体变成独自拿起斧头向日本鬼子砍去的抵抗的、革命的主体过程。与《鬼子来了》相似,冯小宁的《紫日》(2001年)以一个被俘的北方农民杨玉福的视角来讲述二战末期的故事。
第四种是外来视角下的抗战故事。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种借西方人的视角来讲述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叙述策略,如冯小宁执导的《红河谷》(1996年)、《黄河绝恋》(1999年)和叶大鹰导演的《红色恋人》(1998年)等。在这些影片中,占据主体位置的是一个“客观的”西方男人,中国则被呈现为一个女人、女八路军的形象。《红河谷》讲述的是1904年西藏人民抵抗英军侵略的故事,但是,这种抵抗的故事却放置在一个英国年轻探险家琼斯的目光中来呈现。这种西方视点的故事在《黄河绝恋》中更为明显,这部影片完全以美国飞行员的内在叙述为主。在日本这个残暴的敌人面前,影片中的“中国人”放弃了家族仇恨而成为一种抵抗的主体,只是这种土匪和八路军联合阻击日军的故事被改写为“拯救大兵瑞恩”的故事,为了把美国飞行员欧文安全送到根据地,所有的中国人都“心甘情愿地”牺牲了。《红色恋人》也以一个美国医生的回忆为视点,呈现了一段都市革命情侣的生死之恋。通过把自我的历史叙述为他者眼中的故事,革命故事获得一种言说和讲述的可能。2009年上映的《南京!南京!》则把这种外国视角转化攻占南京的日本士兵角川。与那种落后者、弱者、被砍头者的主体位置不同,中国导演可以想象性地占据一个西方化的现代主体,这也许与中国走向“大国崛起”和“复兴之路”的历史进程有关。
第五种是把抗战讲述为二战故事。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是把抗日战争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降级”为中日两个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那么,新世纪以来的抗战叙述则“升级”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战争。需要指出的是,在以欧洲为中心的二战叙述中,抗日战争一直被西方所忽视,这不只与当时国民政府的弱国地位有关,更重要的是与日本在冷战后被美国赦免、成为对抗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自由世界”的合法成员有关。这体现为战后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被彻底清算战争责任(如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就连南京大屠杀等人间惨剧也几乎不被西方社会知晓。直到冷战结束后,1997年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出版《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大屠杀》,才使得这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进入西方主流视野,也使得德国纳粹党人约翰·拉贝所留下的记录南京大屠杀的日记得以出版。1997年首先出版中文版《拉贝日记》,被作为南京大屠杀确实发生过的“权威”证词。〔2〕2014年英国历史学家拉纳·米特出版《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首次向西方世界呈现抗日战争的全景。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长期以来,在二战的“世界”视角中没有中国抗战的位置,之所以这些“被遗忘的”故事又被重新提起,与冷战终结和当下中国的崛起有关。这种西方世界有限度地对南京大屠杀、抗日战争的认识,都会引起国内社会的极大关注,因为这些来自西方的目光正好呼应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走向世界、加入英美主导的西方秩序的内在渴望。近些年,抗日战争越来越被放置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来呈现,不仅恢复国军正面抗战的形象,而且恢复国民政府作为同盟国、与英美并肩作战的位置。近年出现多部关于国军赴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题材的图书、电视剧和电视专题片,比如在电影《一九四二》(2012年)、《开罗宣言》(2015年)中把蒋介石表现为二战时期的国际领袖,参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趣的是,这种把抗战“国际化”的趋势并没有凸显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性”,不会讲述苏联援助中国抗战的故事,也难以呈现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的身影。
总之,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被书写为落后者、弱者的悲情叙述,到当下中国高调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都反映了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不同的自我想象和对未来的期许。对日本的理解,不应该陷入近代以来形成的恶魔与榜样的魔镜效应,而应该直面现代性所带来的创伤,寻找克服现代性的新路。
〔1〕章东磐.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中缅印战场影像〔M〕.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2〕戴锦华见证之维〔A〕.印痕〔C〕.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谢莲碧)
J9
A
1004-0633(2015)06-019-7
2015-09-06
张慧瑜,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电影史、当代大众文化。北京10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