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传统和小说的新奇性
王晓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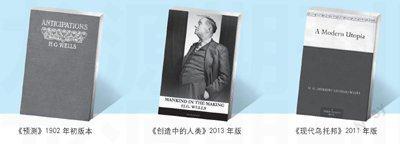
一
我们所熟悉的赫·乔·威尔斯,如帕特里克·帕林德所颂扬的“科幻传奇进化到现代科幻小说中的枢纽性人物”,是摹状星际战争、时间旅行的好手。他从创作的魔盒中源源不断地掏出地底人、月球人等形象,几乎已经左右了我们对异域生物的最初幻想。然而布莱恩·奥尔迪斯却俏皮地说道,当我们习惯这么一个威尔斯之后,另一个威尔斯马上就会跳出来。这另一个威尔斯,敛起戏剧描摹的绚烂笔墨,开始向我们输送整体性概括世界的野心。
威尔斯的此种创作,包括《预测》(Anticipations)、《创造中的人类》(Mankind in the Making)和《现代乌托邦》(A Modern Utopia)三部曲。按其自身说法,《预测》的创作是对早先想象性写作的一种偏离,是为了应对其脑中一系列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而完成此书却只能得到暂时的餍足,并未穷尽其思考。于是又有了《创造中的人类》,其中威尔斯试图“将社会组织看成是一种教育进程,而不是未来历史中的事物”。威尔斯自认该书的写作更为率直,然而也失之毛糙,因而又有了《现代乌托邦》,在此,威尔斯的野心得到最大程度的施展,他继承并修正了前作的一些细节,希图绘制出孕育于其思想的乌托邦图景。
《现代乌托邦》开篇即言明与畴昔乌托邦体式歧异之处:
一个现代空想家所设想的乌托邦,必须在一个基本方面区别于达尔文改变这个世界思索方式之前的人们所设想出来的乌有乡或乌托邦。那些乌托邦都是完美、静止的,其间事物永远处于离却骚乱的幸福的平衡……但是现代乌托邦必须是非静止、动态的,它并不处于一个恒久固定的状态,而是处在一个充满希望的阶段,并往更高的阶段攀升。
于此威尔斯给出了现代乌托邦的关键特征—“动态的”(kinetic),以区分于前人“静止的”(static)乌托邦。他批评过往的乌托邦全然枯燥乏味,“失却生命的血肉、热烈和真实,其中没有作为个体的人,而只有一般性的群体”。而恰恰是在“对个体性的坚持,以及个体生命间的必要差异”中,人们才能觉出“塑造成的身体的质感”。他进一步表示,没有恒久、确然之物,所谓的完美只不过是故意剔除了生命中的不定因素,而这不定因素才是人之为人“最神秘、深沉的质地”。此后,威尔斯借用赫拉克利特的话总结道:“人?当真有吗?没有,有的只是个体的普遍生成。”威尔斯强调乌托邦的动态特征,以及个体差异性存在的必要性,确实比只关注静态完美的早期乌托邦多了些活力和关怀。进化论洗礼下的威尔斯,相信个体凭借不断的砥砺、发展,可臻善美,从而达成整个种族的进步。
此种对个体生存发展的应许,会使现代人备感亲切。然而所谓乌托邦—莫尔创制之海外蓬莱,本便是以港湾为畛、以规约为制的群体社会,无论文本内外,个体声音、姿态都湮灭于社会规例的条分缕析之中。因而,威尔斯动态乌托邦的倡举,起于个体性的呐喊,最终仍归于集体性的运转。威尔斯在乌托邦中设置“武士”阶层,该阶层拥有较高的道德和能力,为最高领导群体。任何乌托邦成员都可申请成为“武士”阶层的精英,如此威尔斯为个体发展找到了晋升方向,听起来像是乌托邦式的成长小说。然而隐去了成长历程的成长小说,只剩一纸许可条文,一席“武士”尊位,未免令人有嚼骨食鲠之感。并且如同简·爱、汤姆·琼斯之类,迷茫几次,闯荡一番,最终能安稳地处于社会给定的位置,便宣告了成长的结束。那么,徘徊于舞台边缘,始终战战兢兢寻不到位置的狼人、吉姆爷们呢?参考现代乌托邦,也许威尔斯会把他们流放到小岛去,也许他们根本就无能来到这个世界。
这么说是因为威尔斯的现代乌托邦有着两个关键约定,很可作隐喻发挥,因而也容易招致争议。其一是惩罚。对于逾越道德法律的人,可监禁或流放,当然,待罪愆赎尽可予释放。乍一听相当公平,但只要条规名目稍改,任何人都可能成为被监禁人员。故而彼得·肯普称此流放地为“集中营岛”,暗指其恐怖色彩;其二是优生。《现代乌托邦》中说到,乌托邦“会杀死所有畸形、古怪和重病的出生婴孩”。威尔斯相信,让此种婴孩存活,只是增其不幸与痛苦而已。而乌托邦同样禁止先天疾病以及反社会人群孕育后代。因此如某些论者所言,威尔斯在《现代乌托邦》中贯彻了消极优生学,而此种消极优生学,稍加修改,即能制造出一个个体、阶级乃至种族的清洗。因而以上两点最可体现现代乌托邦集体对个体的钳制(其他如政治制度、环卫条例、经济政策等都有详尽规定,“武士”阶层则有更为精细的遵循准则),而此种钳制仍以保障个体性为出发点,故而愈加使人心悸。当威尔斯热衷于动态乌托邦的构想时,他的理想王国却已一个规章、一个制度,横梁架椽建成稳固的大厦了。当他寄望于个体的自由发展时,乌托邦的分级制度已先行筛选,留下的是有限的个体和被管制的自由。
二
应该说,在莫尔之前,乌托邦构想还只是零碎出现,不成体系。直到莫尔《乌托邦》的问世,才将先人零星的构想扭结整合为一个文本,甚而一种辐射性的思维方式。撇开莫尔针砭时政的意图不说,《乌托邦》中构建的没有压迫、剥削的理性王国,成为后世人们状写理想社会的原型。而科幻小说和乌托邦的关系向来暧昧,雷蒙·威廉斯力主科幻小说为乌托邦文学的亚类;亚当·罗伯茨则把乌托邦理想作为科幻小说四个门类之一;于此倒不如取达科·苏恩文的表述,他虽将乌托邦作为科幻小说社会政治性的亚类型,却发现了其中的矛盾意味,亦即科幻小说是在开拓至现代以后,通过回望才把乌托邦纳入自身。也就是说,科幻小说虽承继了乌托邦的血脉,但其后期扩展又超出了乌托邦的范畴。
或许可以说,《现代乌托邦》是将乌托邦传统发挥至极致的科幻小说(甚至都不像小说了,哈维·奎门称之为一种“杂交”文类)。大概只有到威尔斯手里,科学才被真正系统地纳入乌托邦体系,成为维持社群运转的第一动力。而此等科学理性的升扬,正端赖于启蒙的发生。笛卡儿将上帝列为第一动因,是权且将之悬搁,事实上也是隐隐将之排除出物质世界,但同时又高举上帝赋予的思维,为主体找到合法性,进而以主体和科学来主导物质世界。启蒙的淋漓元气注入科幻文学的创作,则体现为昂扬振奋的人物主体和凯歌猛进的科学征程淹没了昔日宗教的荣光。故而亚当·罗伯茨在为科幻小说撰史时,以科技和魔幻两个因素的消长来描摹其发展变迁,其中相互作用的仍旧是科学与神学。可惜的是,以主体发迹的启蒙,渐渐把个体交付于工具理性和逻辑推理,倒迷失了初衷。《现代乌托邦》以科学和理性作为动力,构造出的是一个整饬、划一的模型,威尔斯所憧憬的“动态”原则似乎只是主题先行,在那个模型里并不能看到鲜活的个体。
三
然而即便只是一个先行的主题,“动态”特征和个体发展也为乌托邦的描述打开了一个缺口。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假定“从莫尔的原始文本中衍生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一种致力于实现乌托邦计划;另一种是模糊而无处不在的乌托邦冲动,它以各种隐蔽的表达和实践力求浮现出来”。所谓乌托邦计划,则必是系统的,所有的乌托邦构建文本和革命实践都应划归其名下;而乌托邦冲动则更像是布洛赫阐释的白日梦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愿望。虽然弗雷德里克表示乌托邦冲动可能会指向集体,但它的早期阶段“仍然被封锁到个人经验的范围之内”。如同布洛赫发现平常生活中广告、杂志、博物馆等事物所体现出的乌托邦幻想,他所捕捉的正是零碎的个体经验。
这容易使人想起现代小说的新奇性(novelty)定义,按伊恩·瓦特的观点,现代小说正是建立在对个体经验的重视上的。古典文学或文艺复兴史诗的情节,多以过往历史传说为基础加工创造,其中更多的是模式型叙事。而现代小说则把个人日常生活(古典主义所谓低级题材)作为主要描述对象,赋予个体经验崇高感。如此,启蒙好不容易从神学那儿争取来的科学理性控制权,在一些现代小说那儿碰了壁。吊诡的是,现代小说的开创者们(比如笛福)正是在启蒙的恩典中,获得了开拓、征服的力量和乐趣,继而掉转船舵,思索起这一场启蒙所包藏的问题。
笛福笔下鲁滨孙的荒岛历险,正是脱离群体的个体经验描写。张大春赞叹笛福首度将“孤岛”和“叙事”发明成“对理性主义世界之不耐”,获得了以此叛离其当代叙述的机会。这一叛离通过个体非功利性的生存展示,恢复了工业时代业已消散的手工劳作的鲜活性。伍尔夫调侃摆在《鲁滨孙漂流记》读者面前的只有一个大陶罐。而正是这一大陶罐所代表的种种鲁滨孙亲手操持的生存活计—编制箩筐、种植小麦、制作面包等等才是小说令人殊难忘怀的美丽细节。工业发展的起步、劳动分工的明确都使得活计一肩挑的岁月一去不返,鲁滨孙劳动所得到的满足和成就感是对当时人们的一种忧伤的报偿。笛福让鲁滨孙在机器时代所作的一个回望,以个体语言的“直接性”和“具体性”(乔治·斯坦纳谓莎士比亚之语),重建了个体和世界的自然联系。
达科·苏恩文在论述科幻小说时,发现了上述现代小说的新奇性,他说这种“对人的新洞察”已成为现代小说的“战斗口号”。随即他提出科幻小说的新奇性还须更加体现整个世界的变化,使读者的经验性规范变得陌生,言下之意是要与现代小说的新奇性作个区分。但是细究起来,苏恩文将新奇性与认知性对举,令人怀疑其所谓的新奇性正是先前提出的“疏离”(dislocation),因为他同样也曾把疏离和认知对举。而疏离这一糅合什克洛夫斯基“陌生化”和布莱希特“间离”的术语,是指在一定的认知基础上,超越了作者与读者经验现实的可能性。然而,科幻小说似乎并不能完全脱离经验现实语境,事实上,科幻作品应该是以新奇性的伪装巧妙迂回地对经验现实作出品藻。尽管很多时候,这种迂回会被误解为逃避,而逃避仍不失为一种详审的视野。那么,当启蒙过后的理性社会成为一种经验现实时,现代小说强调的新奇性恰恰也是一种“疏离”,它在乌托邦传统下,开发出束缚于群体宏大叙述的个体经验,正可为揭橥理性王国潜藏之涌流提供一种视野。鉴于此,现代小说的新奇性大概也可汇入苏恩文的术语,它不以星际远航、物种差异为噱头,单只往生活情境里撷取瞬间,罗致感动,倒比乌托邦叙述多了些小说本身的自觉。
四
事实上,威尔斯《现代乌托邦》所展示的矛盾,在早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辩论中可见出渊源。车尔尼雪夫斯基狱中创作的《怎么办》中,女主角韦拉·巴夫洛夫娜所做的第四个梦基本上就是一个乌托邦幻想:
田间泛着金光,原野上开遍了鲜花,原野四周的灌木丛中百花争奇斗艳……在田间、草地、灌木和森林背后,又可以看见同样泛着金光的田亩、布满着野花的草地和灌木丛,一直到那被阳光照耀下的森林覆盖着的远山为止……
如此田园牧歌式的景象,可见出车氏对浪漫主义感伤情绪的继承,而后笔锋一转,自然的感伤氛围里耸立起理性的水晶宫:
一座庞大的建筑物,这种建筑物就连在今天最大的京城里也只有几座,或者干脆说,今天连一座也没有……已经有了一个轮廓—塞屯汉山丘上的宫殿……这些田野上布满一群一群的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还有小孩们混杂其间,到处都是人……机器几乎代替了他们的全部劳动……他们举行晚会,平常的、普通的晚会,他们天天晚上这样娱乐和跳舞……他们具有和我们同样的精神修养,同时又有着和劳动者同样强健的体格,因此他们的娱乐、他们的享受和激情当然要比我们的更富有朝气、更为强烈、更广博开阔、更使人心悦神怡了……
可见,车氏乌托邦一方面以俄国的广袤土地为基(自然风光的状写,田地,庄稼),另一方面以西方借来的启蒙武器(机器,玻璃和金属材料)构建出覆盖一切场所和设施的水晶宫殿。而水晶宫中的子民们,有“同样的精神修养”和“强健的体格”,劳动与娱乐并重,因此其享受和激情更“富有朝气、更为强烈、更广博开阔、更使人心悦神怡”。似乎在车氏眼中,西方启蒙的成果是可直接挪为己用的,而对俄国人民,车氏亦是信心满满,好似科学的准则、观念预先凿通了水道,那么技术突破和人性善美都可水到渠成而不溅染堤岸半分。于是,我们就很可理解为何男主角洛普霍夫会被塑造得如此法相庄严,天然地谙知善美,方寸不差地游刃于个人和集体利益之间。如同车氏在梦中通过阿塔斯耳忒、阿佛洛狄忒、“贞洁女皇”等形象历数女性变迁,女主角韦拉的一生也以略嫌僵化的四个梦境串联,图示了一个女性的解放过程。联想卢梭以来,皆以女性解放作为社会解放的度量标准,不妨揣测,车氏笔下的韦拉也不过是其乌托邦价值的一个展示模特。也许可以说,《怎么办》中的科学理念,业已穿透了人物塑造。无论在思想层面,还是在叙述层面,车氏都演示了乌托邦理想压倒个体经验的戏码。
面对车氏笔下的完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便故作涎皮赖脸,须知寄栖于地下斗室的疯言疯语,恰是讥刺车氏庄严宣讲的最好方式。地下人言必称“我”,升扬一个怀疑的“我”,整个地下室都喧哗着“我”的声音,这正是车氏所忽视的(韦拉也讲“我”,然而她的“我”是为了集体而列举的)。地下人的言语是即兴、片段式的,这从策略上针锋相对于车氏的整饬体系:
……但是人是如此偏爱建立体系和偏爱抽象结论,因此宁可蓄意歪曲真理,宁可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只要能够证实自己的逻辑就成。
……手段最巧妙的屠杀者,往往几乎都是最文明的大人先生……
这同时也在对人的洞察上向车氏体系发出诘难。陀氏并不相信抽象结论与体系能带来一劳永逸的效果,因为一种固化的缺乏对话的理论势必遮蔽其芜杂部分,而体系的安稳只会使人增生阻碍追索的惰性和对异质事物的敌视(然而,启蒙却只能如此,唯有一个单质化、体系化的力量才能推翻另一个单质化、体系化的力量。所谓矫枉必先过正,而后才是继续修正的过程)。因此,地下人呼吁的永远是一种变化,如之所说“也许人类活在世上追求的整个目的,仅仅在于达到目的这个不间断的过程”,最终稳固的水晶宫他并不想要。
另外,车氏笔下的“美与崇高”也成为地下人挂在嘴边的反讽话,地下人复杂的心理剖析使得车氏对洛普霍夫的刻画倍显孱弱。个中原因大概不可说是陀氏比车氏更多了几分对人性的洞察,只不过车氏也许同托尔斯泰一样,太执迷于道德和理想的完满,因而俯视众生之时不免有了盲点。陀氏恰恰从地底出发,偷听、窥视到自下而上的众生之相,因而他深知人性窳劣的成分,并不能匹配于车氏的乌托邦模式;而同时,他也不愿宗教大法官以人性窳劣之名义接管自由,完成科学乌托邦对神学王权的僭夺。他借地下人之口言明,最主要和最宝贵的东西是我们的人格和个性。这也许可说是乌托邦传统中小说新奇性的一次有力发声。
五
待科幻小说到扎米亚京手里,又给了威尔斯一个美好的回应。扎米亚京相信乌托邦并不该成为一个静态的天堂,而应该持续发展。他在《我们》中以人物讲述丰满了威尔斯搭建的钢铁框架,并且创造性地引入了威尔斯所无能发现的细节:
(叙述人在古代房子的庭院看见一位老妇人)我们因共同的血脉而相连—强壮的、伟大的血液—在我们的血管里奔涌。
我写到这里,不由得有点羞愧。不过,我保证过要在笔记里坦陈心迹:好吧,是的,我弯下腰,亲吻了老妇人柔软的、纠成一团的嘴。她用手擦擦嘴,笑了。
联众国机械化的生存里,在古代庭院的银色灌木中,扎米亚京重新发现了个体的情感震颤。甚至连“我”碍于组织而略微迟疑的小小延宕—“好吧,是的”—都被扎米亚京细腻地捕捉,像巴特说的,也许细节的想象才特别可定义乌托邦,而这可能才是小说应自觉承担起的叙述。张大春在比较《我们》和《一九八四》时,重提了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对后者的诟病。因在昆德拉看来,奥威尔是在兜售伪装成小说的政治读物,他将小说与生活无情地缩减为纯政治的方面。然而奥威尔何尝不知道政治应为生活服务的道理呢,归根结底,是他太牵心于对乌托邦政权的反思和控诉,以至于遗忘了对小说新奇性的发现。而上述《我们》中的细节,则似乎暂时地抛却了《一九八四》所念念不忘的反思和控诉。因此科幻小说着迷于乌托邦传统改造的同时,亦无时不在强化感知个体生存细节的触角,而这一个体生存细节,并不该以政治修正的名义受到过多的讹诈。
我们不应忘记,如斯质疑乌托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竟也在晚年《一个荒唐人的梦》中,做起了一个长长的乌托邦之梦。梦醒时分,那人宣称亲眼看见真理的光华四射,他要去传道,因为“人是会变得美丽、幸福的”。没错,那个醒来的荒唐人,恢复了对人性的勇气和希冀,也必将能恢复美丽的乌托邦幻想。可在恢复之前,他得去寻找一个女孩。那女孩曾拉住他的衣袖,楚楚可怜地哀求他,而现在,他伴着这一令人心碎的细节苏醒。也正是在这样的细节中,小说新奇性和乌托邦传统也都苏醒了一次。
应该说,吻老妇人和牵衣女孩的细节发现,都起到了修正乌托邦传统的作用,可是更重要的是,它们也恢复了个体生存(小说新奇性)的独立性。如前所述,笛福创作的《鲁滨孙漂流记》开启了现代小说新奇性的发现,但是最初它是作为笛福道德说教的手段而存在的,换句话说,十八世纪小说强烈的道德意图,使得小说家们一方面极力否认作品的虚构性,将之伪装为历史,另一方面,宗教、道德意图盘踞于小说之首,成为作者创作的最大目的。然而有趣的是,虽然鲁滨孙的荒岛生存细节在笛福道德意图的催逼之下龟缩一隅,但反而成为读者关注的焦点。因此,小说新奇性从笛福手里出发,希图展现个体生活的原本面貌,可是它面对的外在意义却不断扩展,从巴尔扎克到左拉到托尔斯泰,小说受到来自社会学、生理科学、政治、宗教等领域的意义索求。它虽赖于巴尔扎克获得了鲜活的众生影像,也赖于左拉获得了丰饶的细节;可是,它也成为巴尔扎克“社会书记官”的职责载体,必须接受从外而内的社会批判话语的挟持,同时,它也接受了左拉作为科学信徒的狂热,从内而外以遗传生理辖制所有细节,然后扩张延展,以此理念为指导而描画整个人际、种族、国家网络。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则延续了肇始于《鲁滨孙漂流记》的分裂—安娜支线中对个体经验精准、奥妙得令人惊叹的把握和列文支线中托尔斯泰呼之欲出的思辨意图,使得小说结构出现失衡。如此一来,新奇性变得步履蹒跚,每挪一步都牵动或内或外的意义锁链,可供真正生活呼吸的氧气越来越稀薄。那么该是狼人、吉姆爷们登场的时候了,可能会被威尔斯放逐到荒岛的边缘人,倒可能在边陲之地真诚地面对生活,新奇性也正是在边缘之地才可能卸下意义的过分累赘。虽然在乌托邦传统中,小说的新奇性重提动态个体,是对威尔斯理想的一种发展,并且上述陀氏以及扎米亚京的细节展示也成为对乌托邦社会的一种质疑,但是这种质疑并不能掏空新奇性的所有意义。犹如鲁滨孙面对陶罐时,他的眼里合该只有这一个陶罐,而不该让对理性世界的不耐过早地喧宾夺主,因而看到吻老妇人和牵衣女孩的细节时,我们也并不着急呶言太多,只因在那一刻,这一生活的细节已经足以填满我们的心肠。因而,以此为代表的小说新奇性能唤醒我们对生活的直接感,它在拒绝过多的外在意义附着的同时,不自知地修正着我们的乌托邦幻想,亦即不断地提醒我们,乌托邦世界永远不能忽视鲜活的个体生存,这应是先于所有外在意义的第一意义。如果它不自知地启发了包括乌托邦幻想在内的政治或其他领域,那是它意外的功劳,并不是它的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