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俱乐部的早餐
马慧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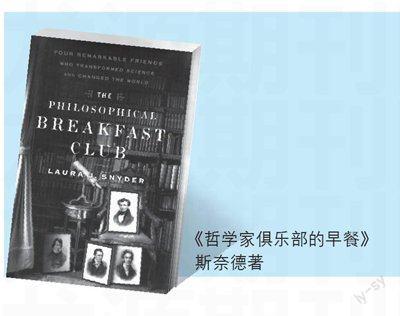

一
赫歇尔会让仆人去厨房里搬来预订好的丰盛早餐:茶、咖啡、啤酒、冷牛肉、火腿、鸡肉、凤尾鱼、鸡蛋、烤面包、松饼、烤面饼、蜂蜜,还有果酱和奶酪卷。然后这些男人就开始吃喝,大笑,交头接耳。早餐过后,惠威尔、琼斯、巴比奇和赫歇尔留下来讨论。通常是赫歇尔发起一个话题,用培根著作中的一段话做引子。
以上就是“四个哲学家的早餐”的情景,它发生在一八一二年左右的剑桥,一个个阴冷的周日早晨。那是英国工业革命的盛时,有这么四个“自然哲学家”(那时还没有科学家这名称),在剑桥里成了狐朋狗友,每周日早上聚会。这四人后来在历史上都留下了各自的痕迹,遗憾的是,他们在今天已经近于被遗忘,斯奈德(Laura Snyder)的《哲学家俱乐部的早餐》一书终于把他们拉回视野,而“那许多顿庞大的早餐”正是线索之一。四人都推崇培根的“实用科学”之论,都希望科学给生活带来实际的改变。培根的名言,除了“知识就是力量”,还有“科学家应该像蜜蜂而不是蜘蛛或蚂蚁”。因为“蚂蚁只采集不消化”,而蜘蛛呢,它的织网,一切都生自已知的东西而非外界。培根主张的是科学家勤于采集外界信息,并不断寻求实证。跟他相反的是笛卡儿,他想建造的是包罗万象的抽象之网,所以笛卡儿研究物理,不是从实验、实证入手,而是假设先行,比如上帝的存在等等。笛卡儿在欧陆影响很大,但在英国并不受重视。惠威尔等四人,都是坚定的“培根党”。
先说惠威尔(William Whewell,1794-1866)。此人家境贫寒,父亲早已准备好让他继承木匠生意,不料他学业优秀,父亲被劝说让儿子读书,只好接受“失去一个继承人”的事实。“听着惠威尔,如果你今天背出超过二十行维吉尔,我们就揍你!”这是中学里的男孩子们气急败坏地对好学生惠威尔说的话—可惠威尔偏偏还是打架能手。
惠威尔最终上了剑桥。当时的剑桥,课程内容主要是古典学和数学,并不实用,而每年的费用比他父亲全年的收入还多;而且作为剑桥人,除了社交、party还有许多花费,比如打猎、旅行等等,这个巨大开支烦扰了几代父母。剑桥是向富人子弟敞开的,但穷人也并非全无办法。惠威尔努力学习争取奖学金,又当家教,勉强收支相抵,数年之后仍为钱烦恼,买本牛顿的《自然原理》也要向父亲伸手。
很偶然地,惠威尔遇到了琼斯(Richard Jones,1790-1855)、赫歇尔(John Herschel,1792-1871)和巴比奇(Charles Babbage,1791-1871),四人的生命轨迹都发生了改变。约翰·赫歇尔是大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的独子。威廉出身贫寒,靠自己的奋斗成了科学泰斗,约翰看上去坐享其成,从小在伊顿、圣约翰这种贵族学校读过来。他年轻时极不情愿继承父业,但不知不觉地,还是成了跟父亲类似的人。不过在职业选择上,父子仍然争执不休。约翰要当律师,父亲想的是让他当神职人员,因为经济有保障,尤其难得的是,有闲暇。在那个年代,以科学为职业闻所未闻,到目前为止,牛顿都被称为“自然哲学家”。所以,“科学研究”向来是闲暇爱好,神职人员才负担得起。
巴比奇呢,同样出身富家。跟赫歇尔认识后,巴比奇也跟着一起手算天文数据,抱着沉重的草稿纸,苦不堪言。从这时候起,他就梦想发明一种辅助计算的机器。他当然不是第一个梦想计算器的人。人们为之付出的努力已经持续了千百年,从算盘到计算尺。莱布尼茨和帕斯卡,都花费了巨大的心血,尤其是莱布尼茨,自掏腰包,将数年精力贡献给一种“机械计算器”。此外,英国是个航海之国,水手时时要靠计算自己与星星的距离来推知地点。计算表格是人造的,勘误加上勘误,修订表格成为系统工程—更可怕的是,谁也不知道表格中还有没有错误,性命都赌在这些数字上。十七到十九世纪间,许多类似的机械问世,它们都是精美的机械设计成果,复杂如钟表,可惜效率不高,而且不精确,更重要的是,无法普及。巴比奇年轻时中了发明计算机的“魔症”,他还不知道这个延续二十多年的梦将怎样影响他的生活。
英法在此年间战争不断,一八一五年总算太平了。此时惠威尔已经从剑桥毕业,打算申请剑桥的院士(Fellow),此时琼斯等人都已离开,只留他一人在此苦读,四人的周日早餐不再。那个年代,院士的位子很宝贵,有了它,几乎一生不需做什么就可以拥有学者头衔和待遇,缺钱的惠威尔实在太需要它。考试共五天,每天八小时,包括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翻译、数学和玄学(metaphysics)。惠威尔一举拿下,得意地给朋友写信:“我可以在学院啤酒和学院政治中细品余生了。”
四人团中的另一人,琼斯,生活轨迹完全不同,年轻时就成了一名坎特伯雷的乡村牧师。那时,乡村牧师等级和收入区别十分清楚,而且几乎是家族垄断。琼斯收入不高,地位卑微,郁郁不乐,时间用在打牌、打猎和吃喝上。一八三○年左右,琼斯在给惠威尔的信中,说自己脑子里都是自杀的念头。此时他已经结婚,来到新教区,收入增加,环境优美,生活悠闲,似乎没什么抱怨的理由—今人可能觉得琼斯的问题就是抑郁症。惠威尔想了一个办法来帮助朋友—他认为对付精神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努力工作。他鼓动琼斯完成一项事业,这个决定最终改写了英国经济学史。
自剑桥求学的年代,政治经济学就是四人共同的兴趣,其中读法律的琼斯对政治的热情最高。法国大革命后混乱未消,隔海观望的英人日子也不好过,穷人多,暴力、犯罪、骚乱也多。琼斯和惠威尔都在读风行一时的马尔萨斯—里卡尔多辩论。他们不同意马尔萨斯的许多观点,比如惠威尔指出他们的理论和统计事实不符(惠威尔被认为是用数学描述经济学的第一人)。但他们至少在一点上同意里卡尔多:政治经济学应该成为一门培根理念中的从实证出发的科学。朋友们鼓动琼斯写一本书,把想法整理清楚。但要说服常处抑郁状态的琼斯,可不是件容易事,此人有一堆健康毛病,其一是胖得难以动弹。惠威尔一直都在劝他把每天三杯酒减为两杯。整整九年时间,惠威尔连劝带逼让他写书,尤其是,希望在里卡尔多理论深入人心之前,把书写出来。《论财富的分配和赋税的来源》(Essay on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on the Sources of Taxation)书成之后,琼斯说这是“惠威尔的养子”。
政治经济类的书太难写了。琼斯说过自己一直在博物馆和图书馆之间穿梭收集一六六八至一七七六年间的史料,观察人们如何分配收入、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关系,等等,“我只知道一个办法,就是观看,观察。”当时英国确实深受里卡尔多影响,简单地说就是假设人是趋利避害的生物,结论是,越是帮助穷人,他们越懒。结果,英国的穷人遭到愈来愈重的惩罚和歧视,其中残酷的“劳动救济所”(workhouse)就是产物之一,穷人在其中每天工作十四小时。有人说,见到救济所中的人打碎骨头做肥料,有人偷啃霉烂的骨头上的剩肉—这些骨头并不都是动物的,有一些来自墓地!
这段时间,巴比奇也发现英国的经济已经更多地依赖工业而非农业,而亚当·斯密和里卡尔多的理论是建立在农业经济上的。里卡尔多认为工业化必然导致工人失业;但巴比奇相信,工业化会带来更多的机会,因为不能由机器完成的工作还是很多的,机械化不可避免,利大于弊。琼斯和惠威尔决定改变现状,说服人们相信,“普通人自由和舒适的生活才是高产出的必要条件”。对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琼斯也不赞同,他认为人口是可以自动调节的,消费的增长必然会让人们自愿节育,而工业化会带动人的消费。琼斯的理论虽然被不少人接受,但影响力还是不及马尔萨斯和里卡尔多。
不过,综观全局,历史最终站在了里卡尔多这边。如今的经济学(包括数学模型),更接近里卡尔多而非琼斯的想法。但是,风潮也在两边不断摇摆,人们也常常发现将经济与伦理分开是错误的。至少,这四人将政治经济作为科学,把培根的归纳法用到经济学,这个贡献的重要性不可改变。
二
一八三一年,赫歇尔写了一本书,《自然哲学研究初论》(Preliminary Discourse on the Study of Natural Philosophy),推介培根的学说,讨论观察和理论的关系,提出自然哲学的终极目标是通过推理来理解世界,等等。此书影响很大,受益者包括年轻的达尔文。书出版的那个月,达尔文正在剑桥准备考试。达尔文后来回忆说正是此书激励他献身科学。此时赫歇尔新婚不久,巴比奇则正拼命学习工具制造,走访各个工厂。赫歇尔在《自然哲学研究初论》中为科学观察的大概步骤设计了一个表格,鼓励读者亲身实践,动手记录。巴比奇受此启发,设计了一种“参观工厂表格”,供人来访时提问、记录。
这几年,巴比奇好几位家人去世,包括太太。他崩溃了。多少年里,他留下自传和无数信件,但一直不提太太,因为承受不了记忆带来的悲痛。赫歇尔陪他旅行,逛遍了欧洲(此时,巴比奇接到了任命,他要成为剑桥的教授了。若干年后,他略带恨意地说,这个头衔,是国家给他的唯一荣誉)。自此,他性格大变。过去他是个多么慈爱的父亲,给孩子们设计机械玩具,还在办公室和家之间用玩具车跑来跑去送信,现在,他悲伤而暴躁。他不像惠威尔那么大大咧咧,虽然会赌气,但争论之后就烟消云散;也不像琼斯,内向地把不快留给自己。他动辄发怒,对身边关心他的人也从不克制。
其实,朋友们觉得他该满意了,因为做议员的内弟给他搞来了政府投资。很快他们就从政府那里拿到了九千镑(据说相当于现在的八十多万镑)。巴比奇雇了一位著名的巧匠,克莱门特(Joseph Clement)。此人没受过正式教育,但极有天分,能手工制造精度很高的机械部件,要的报酬也高。此刻的巴比奇不缺钱,两人的合作看上去互利互惠,前景美妙。不久,钱开始成为问题,克莱门特动辄罢工,工作过程再无宁日。此时巴比奇迁怒于皇家学会,初因是私怨,掀起的风暴却改变了学会的前景。
巴比奇在欧洲游历的时候,特别考察了巴黎,发现英国在数学方面能追赶法国,但化学等学科上则远远落后于这个出过拉瓦锡的国家。在英国,根本没有“自然哲学家”的正经职业,所有的研究都处在业余状态。虽然巴比奇对法国有些理想化,但他没有大错,法国当时是欧洲的思想中心,在法国,搞研究的人获得的支持远多于英国同行。法兰西科学院的门槛远比英国皇家学会高,皇家学会会员的资格分明早已贬值。巴比奇不仅写文章批评这些问题,还索性把矛头指向具体的人,如当时的会长和以前的功勋会长,包括班克斯(Joseph Banks),瞬间树敌无数。有人指出,虽然法兰西科学院资助一些搞研究的人,但代价不低,因为这是个受政府控制的机构,必然只能迎合政府所好,这样的系统是不会被英国人接受的。此外,赫歇尔、惠威尔和琼斯都理解巴比奇,但不愿出头攻击学会,也不愿冒政治上的风险对法国倾尽赞美。谁也没想到,巴比奇的攻击真起了作用。推选新会长的时候,赫歇尔成了众望所归的候选人之一,大家都寄希望于他。他自己有些勉强,更愿意把时间用在研究上,更何况他也不善交际。支持赫歇尔的人看上去很占上风,不过太自信了,不仅没有在公关上做到家,巴比奇还干了一件彻底搅局的事:快要选举的时候,他给许多支持者送了封信,说不去投票也可,赫歇尔必胜。此信偏偏及时送到,有人说刚备好马车,收到信就没有去。结果是,赫歇尔输掉了,119 : 111, 只差八票。
赫歇尔说他不在乎当不当会长,但失败的选举还是让他很受伤。从此他淡出了学会不说,还索性去了南非,一住数年。当然,在那里也没闲着,有了一些天文和植物学的新发现。一八三八年,他才回到英国。
对科学组织,其他几人各有想法。巴比奇想的是索性另起炉灶,组织一个新学会,跟皇家学会抗衡。费了番周折,他跟苏格兰物理学家布鲁斯特(David Brewster)创建了“英国科学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旨在具体地协助各个领域内的研究。赫歇尔上次竞选的伤口未愈,不愿靠拢任何组织,但慢慢还是参与了一些活动,对协会影响不小。惠威尔开始也不相信协会,但后来为组织工作投入了不少精力,赫歇尔怪他浪费时间,惠威尔回答,“如果有一种途径能激起人们对科学的热情,帮大家找到方向,我不会拒绝为之大声疾呼。”纠纷当然也不少,布鲁斯特自己是有地位的科学家(他发明了万花筒—当时万花筒可是科学仪器而非玩具),瞧不起英国人,可他却拿不到教职,协会主席之位也被学生夺去了,余生都为此不快。而关于科研是应该政府掏钱还是研究者掏钱,这四个人也意见不一,巴比奇虽然相当富有,但坚决主张政府出钱(后来差分机研究陷入资金困境,他仍然对自己的见解身体力行,绝不动自己腰包)。
一八三三年,著名诗人柯勒律治和惠威尔之间发生了一场小小的、却偶然地被载于史册的辩论。这发生在科学学会在剑桥的会议上,柯勒律治发问:那些从事“真正的科学”(也就是实验科学)的人,应该被称为什么?惠威尔当时是会议的秘书。谈话的具体细节,并没有清晰的记载,但历史知道惠威尔说出了“scientist”这个词。有趣的是,这个词语在几十年后才真正使用,甚至惠威尔自己都没怎么再提到它。就像时间河流里无数大大小小的事情一样,它发生了又消失,一个词语不过是河中一叶。
经过一段努力,科学协会已经是英国重要的科学力量了。惠威尔在剑桥的地位越来越高,也难免膨胀,敌人们讽刺他的态度总是“吾乃圣贤,尔等吾吠”的样子。无论如何,四人从年轻时立志改变科学世界到现在,已经二十载。他们让科学渐渐变成一种职业,呼吁政府为研究投资,大学建立实验室。不久的将来,惠威尔还提出剑桥的年轻人应该拿着科学学位毕业。
三
一八四○年,惠威尔人过中年,事业有成,想结婚了—他大概跟别的院士一样,因为不能结婚,常去妓院。想要结婚,唯一的办法是放弃这个职位,不过到哪里去找份稳定收入呢?峰回路转,他成了三一学院的院长(Master), 可以结婚了。不久,惠威尔遇到了佳人—富家女子科黛拉,皆大欢喜。
惠威尔的人生顺风顺水之时,巴比奇却在梦想的泥潭中苦苦挣扎。
他一直在构想一种计算器—差分机(Difference Engine)。话说机器和人一样,做加减法相对容易,乘除则比较难。巴比奇设计了一种差分方法,通过初始值的逐步相加,回避了乘法计算,能计算多项式。它的工艺空前复杂,部件极多,这个过程对机械制造业也有深远影响。比如,当时的机械部件没有互换性,如果别的机器需要一只新螺栓,已有的螺纹必须重钻。为他工作的克莱门特意识到这个问题,按螺钉长度确定几种螺纹,这样一来,部件不会任意制造,不断浪费—这就是机械部件标准化的开端,它在未来影响了全世界的制造业。
有趣的是,这个计算机模型中的一部分,是受了当时的一种织布机的影响。十八世纪,有个织布工人—偏巧是管风琴师的儿子,对织布机作出了改进。一般来说,管风琴因为依靠音管发音,那么选择各个音管道闭合,就需要打开/堵住这两种状态,多少年来,音管都是靠一个有孔的平面移动着打开/堵住各个管子的。此人用这个道理,把需要的花样设计成阴阳面,用滚筒带动它。它被后人再次改进,因为“太快”而影响到织布工的生计,引来很多抗议和骚乱,竟然闲置五十年。直到一八○○年,织丝工人杰卡(Joseph Jacquard)从博物馆里发现了它,又作出重要改进:板上用“有洞”/“无洞”来储存信息,有洞处杆能通过,再经几个运动环节来带动丝,无洞时杆不能通过。这样一来,花纹甚至颜色的信息,都可自动读取。当然,现在的织布机,是受计算机控制了—织布毕竟还是织布,或许它的巨大革新,期待于3D打印吧。
巴比奇把全部时间投入到差分机上。还未制成,他又有了新想法,去设计一个更抽象的分析机(Analytical Engine)。十年过去,它离成型还没有踪影。他太要完美,不断改进,以至于很难拿出什么成型的东西,也很少发表论文。早先的差分机还有人可以讨论,甚至在公众面前演示过,但对更为超前的分析机,他没有找到可以沟通的人。此外,从分析机的设计思想看,它几乎没有实用价值,更像一个思想模型—可是它没有像图灵机那样,为时代所接受。
一八五三年,惊天动地的消息传来:两个瑞典人造成了差分机!原来十几年前,一个叫舒茨(Georg Scheutz)的编辑兼印刷工在杂志上读到巴比奇的设计,就打算设计一台自己的机器。后来,他读大学的儿子加入,到一八四二年,这个机器可以计算五位数以及三次阶差—瑞典科学院已经在褒奖他们了。一八五一年,父子俩获得一小笔资助(大约相当于五百多英镑),条件是如果一八五三年底不能完成,必须退款。结果他们按期完成,在万国工业博览会上获得金奖。父子俩受到国王接见,一时风光无两。英国政府则订购了一个复制品。
这个消息对巴比奇,确实有点讽刺了,多年来,他花了政府一万七千镑,几乎一无所成。他的机器重达四吨,一万两千多个还没用到的精密零件后来都熔解报废。不过,巴比奇很有风度地表达了赞美和祝贺,舒茨松了口气,回应说“巴比奇是人类福星”。事情却又有了新的转折:舒茨的机器,后来被发现并不精确,因为设计得不像巴比奇那样可靠。父子俩最终死于潦倒,当初的辉煌是昙花一现。机械时代的设计与革新,就是如此举步维艰,动辄耗尽人的一生。后人实在难以责难这些先锋—失败何尝不是科学世界中的常态。
巴比奇呢,曾经依靠父亲供养,自己有过收入不高的教职,父亲去世后他靠遗产生活。他跟传奇女子阿达(Ada Lovelace)有过漫长的友谊—她是诗人拜伦的女儿。母亲忍受不了拜伦的债务、不忠、反复无常等等,带着一个月大的阿达离开了他。阿达自小热爱数学(一说母亲怕她的狂热想象会让她成为拜伦那样的浪漫诗人,所以特别鼓励她学数学),很崇拜巴比奇,两人惺惺相惜,长期通信。对于计算机,阿达的野心更大。巴比奇考虑的只是计算,而阿达认为它将来可以一般化地处理各种任务,包括演奏音乐—在彼时算是科幻,而现在的世界倒还真应了她的预言。她在某些方面跟巴比奇类似,比如怀才不遇,而且同样敏感。有一次,阿达指责巴比奇使用了她的论文却没有注明,巴比奇也毫无沟通技巧,两人大吵,很久之后她的怒气才慢慢平息,主动和解。她自己呢,有些风流韵事,还好赌,据说想靠建立数学模型来赢钱,可惜并不顺利,因此负债累累。三十六岁时患子宫癌,母亲竟然不许人接近她,不许她用鸦片来止痛,说疼痛能让灵魂获救。阿达在几个月的疼痛折磨后去世。
巴比奇的后半生仍然暴躁、敏感而好斗。他跟惠威尔的友谊早已破裂,而赫歇尔去世的时候,巴比奇在给他遗孀的信中,除了悼念,还酸溜溜地说道,“他灿烂夺目的名气,会给你的孩子们带来别人无法享受到的特权,无论他们做什么,都会拥有超人的地位”。这就是悲伤并嫉妒的巴比奇的最后一封信。多年来,他不时主动给政府写信解释机器的进展。他有时生气无礼,有时自怜,抱怨自己牺牲了十几年时间,竟得不到任何承认。算起来,因为差分机、分析机向政府要钱,他跟财政部的关系二十年里都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双方都烦恼不堪。彼时没有科研经费的制度,靠的只是“绅士”诚信,但一个没有规划的投资方案,时间一长,注定结局不妙。
巴比奇的晚年生活更是每况愈下。当时的伦敦有很多街头音乐家,拖着手动管风琴招摇,乐器总是走调吵人的,他们以此胁迫人给钱才离开(狄更斯对此也有记载)。巴比奇无法集中精力工作,冲他们大吼大叫,结果就是有人在他门口扔死猫,砸玻璃。别人一般就忍了,较真的巴比奇闹上了法庭,倒真迫使当局立法,让警察有权驱赶扰民者。他因此名声大作,也算一奇。
一九九一年,英国人按巴比奇的设想和当时的工艺水平造成了差分机,证明它可以运算;遗稿中许多发明思想也见了天日,原来他超出时代太多。老英雄没有遇到合适的时代,世界也错过了计算机带来的改变。或许这样的阴差阳错也是世界的主题吧。
四
十九世纪下半叶是达尔文的时代。他发表《进化论》的时候,惠威尔、巴比奇和赫歇尔已老,琼斯已去世。因为三人在科学界的地位,达尔文渴望了解他们的态度,但没敢抱太高期望。巴比奇转向进化论比较早,其余两人则有些困难。话说进化论出现在一个宗教感很强的地方,真是让人们“三观尽毁”。赫歇尔一向通达,还是受不了“随机”一词—这就是达尔文所说,生物每一代的变异是随机的,选择是由外部环境干预的—怎么可能这样呢,难道不是上帝为生命设计好路途了吗?万物没有“智能”的干预,累积如此变化的几率该多么渺小?这不仅是他的疑惑,也是很多人的想法。不过,惠威尔在给达尔文的信中说,自己虽然一时很难接受,“但是你提出了那么多事实证据,人们如果没有足够的思考和证据的话,很难反驳”。这样温和的表达已经足够让达尔文高兴了。何况,惠威尔指出进化论不能解释人类的许多现象,也是达尔文所承认的。“真理之间不可能互相矛盾”,“如果进化论是真理,如果和我们对《圣经》的解释有矛盾,也许是我们对《圣经》的理解错了”。惠威尔说。他最终承认“需要等待未来的理解”—他在公开场合不肯认同进化论,私下里却多次表示“很可能是对的”。他已经七十岁了,失去了朋友和妻子,宗教感是支撑他的力量之一,但也没有因此否认进化论。
这三人对进化论的“半信半疑”,也奠定了后世宗教与科学的矛盾/和解的动态平衡。至少,他们以当时科学泰斗的身份告诉众人:不要把《圣经》当作科学教科书;人要相信上帝,也要相信科学方法。所幸的是,达尔文去世的时候(1882年),已经不再被视为“毁灭宗教的人”,而是英国人的英雄。当然,后来的生物研究走得更远,科学家继续告诉我们,生物的神圣没有了,道德的必然性没有了,各种绝对价值观都在动摇,人类竭力维护、苦心经营的道德秩序是人类自己的游戏。人要想求真,不如自认这些都是人类社会的构建,并非世界预设。
话说这四位英国科学家,今天似乎只有巴比奇隐约留名。按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说法,科学的发展常常体现在范式的变化上。而巴比奇的计算机构思,跟后来的图灵很不同,后人另走一径,并未接过巴比奇的火炬,他是作为早期计算机史中的一部分被记住的—而“计算机史”,说来有点滑稽,因为它一直在更新,一年前的东西已算古董,史上那些笨重的“计算机”,看上去已经和你我毫无联系。各种“未完成”好比散沙一般,不成方向,科学史只好据成功来写,但那注定不是完整的历史。
而这四人的时代,是英国科学界剧烈变革的几十年。惠威尔功不可没,他对科学研究专门化的推动,是今天的科学职业、科学规范的始创,也被视为如今学术界许多问题(比如分支过细、割裂与人文的联系)的始作俑者。其实这四人一方面主张科学专门,一方面反对抛弃艺术,可惜后人难以两全。有趣的是,诗人马修·阿诺德也是在那个时期成为第一个“专业”评论家。看来,“专业化”在这个时代并非偶然。大众和学院渐行渐远似乎也是必然?世界开始为这种分裂担忧了,斯诺在《两种文化》中的呐喊只是其中之一。裂痕能愈合吗?越来越深的知识积累能被“跨界”吗?未来的未来,是轮回还是不断地告别?
参考文献:
1. The Philosophical Breakfast Club: Four Remarkable Friends Who Transformed Science and Changed the World, by Laura J. Snyder, 2012.
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by Thomas Kun, 4th Edition, 2012.
3. The Difference Engine: Chalres Babbage and the Quest to Build the First Computer, by Doron Swade, 2001.
4. Charles Babbage and His Calculating Engines, by Philip Morrison Emily Morrison, 1961.
5. Metaphors of Memory: A History of Ideas About the Mind, by Douwe Draaisma (translated by Paul Cincent), 1995.
6. 维基百科相关词条

